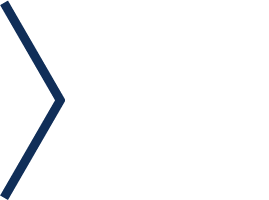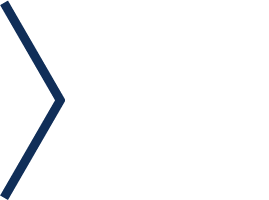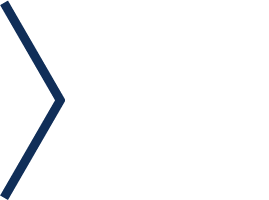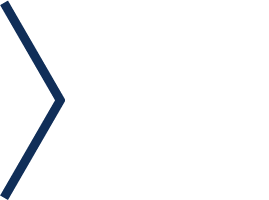摘要:宋代存在着点状模糊疆界、片状模糊疆界、带状清晰疆界和线状清晰疆界等多样疆界形态。影响疆界形态的主要因素是关系形态,疆界清晰程度与关系的对抗程度呈正比。宋朝划分疆界的主要目的是现实安全应对,核心是分隔版籍与非版籍的民和地,保护赋役来源和直辖郡县的安全,显示了宋朝对待周边关系时构建华夷秩序之外的实用主义面向。宋代疆界形态及其反映的观念有其时代特殊性,但总体上是对中国古代自有传统的承继,并不具有变革意义,也不必用“近代性”加以阐释。
宋辽通过盟约确定对等关系并划定疆界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事件,宋夏、宋金划界也是如此。学界对宋与辽、夏、金的划界活动和疆界形态均有涉及,但缺乏整体研究;一些观点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如有的学者将宋代疆界问题赋予变革的意义,认为宋辽间第一次形成了明确的“国家”关系和“国界”认知。在绘制宋代各政权疆域图时,也存在着当代立场与历史逻辑处理上的分歧,未能充分反映宋朝人对疆界的认知和逻辑。要更深入细致地认识宋代疆域问题,辨析宋代疆界在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疆界演进中是否具有变革意义,核心是厘清宋代的疆界形态和疆界意识,并对其作一整体考察。宋朝与境外政权之间,除熙宁宋辽划界、元丰宋越划界后以及南宋与金朝壤地相接外,一般都存在不同形式的中间地带,其中一种就是由非两个政权直辖诸族分布带构成的中间地带。与宋朝直接接壤的部分通常是羁縻州和熟户(熟蕃、熟蛮),宋朝对他们一般实行设砦置堡的点状控制,形成两者间点状的模糊疆界。羁縻诸族所居几乎都为山地川壑,经由山谷、河流、隘口通向宋朝直辖地区。南方诸族分布区被形象地称为溪洞,如广西湖南交界地区多个山口、通道“皆可以径至溪洞”。宋朝在主要通道上设寨扼守,置巡检“专一把截”,“分遣士卒屯诸溪谷山径间”,“择要害地筑城砦,以绝边患”,阻止蛮人进入省地。如辰州设置16砦、1400余厢禁军和600土兵控制所辖溪洞,每个砦控扼一方溪洞蛮。熙宁三年(1070)辰州为防扼溪州,于“喏溪口北岸筑一堡”,“据其要害,绝蛮人侵占省地便利”。辰州卢溪县“西有武溪水路入蛮界”,“最为冲要”之地设慢水等寨,招谕县卢溪寨就设在控扼水路进入蛮界的卢溪口。另如施州置永兴寨“控蛮夷五路溪口”;雅州卢山县设灵关镇寨,“四面险峻,控带蕃界”。陕西秦州控扼蕃人也是“于山丹峡口广吴岭上古城、大洛门城、永宁城隘路口置寨,以遏戎寇”。而澧州石洞寨“深在蛮界,不当要路,无所控扼”,被拆毁。 这些控扼的要点成为省地与蛮(蕃)地双方分界的界至。溪州蛮与省地的边界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后晋天福中,马希范与溪州蛮酋彭士愁战后定盟约,“立铜柱为界。本朝因而抚之”。宋朝与溪州蛮仍以铜柱为界,铜柱具有标识双方疆界的意义。溪州蛮进入省地的主要通道是酉水,铜柱正立于酉水下游的会溪,宋朝先后在此设会溪城和池蓬、镇溪、黔安三寨。宋太宗曾“诏辰州不得移(溪州蛮)部内马氏所铸铜柱”。张纶曾与五溪十峒蛮约盟,“刻石于境上”,所立刻石也是疆界标志。宋孝宗曾诏令湖南“省地与傜人相连,旧有界至者,宜诏湖南帅臣遣吏亲诣其处,明立封堠”。封堠和界至就是指在这些要点上树立的界标。有学者据宋孝宗令湖南“明立封堠”一条判断宋朝正州与羁縻州间边界“呈现线状,其标志物为封堠”,这一判断难以成立。宋朝与羁縻各族在冲要之地立柱、立石标示界限,但未见举行全线议疆划界。宋朝还常把山谷溪洞地形作为隔绝省地与溪洞、熟蕃的天然界限。如“蜀之边郡多与蕃界相接,深山峻岭,大林巨木,绵亘数千百里,虎狼窟宅,人迹不通”,为防止“夷人从此出没”,使沿边“八寨防托遂成虚设”,“各于其界建立封堠,谓之禁山”,与蕃部之间“非禁山林木茂密,无以保藩篱之固”。禁山成为天然屏障,禁止采伐。一处封堠就标示一片为疆界之隔的禁山,说明疆界是模糊而非线状的。判断是否侵越疆界,并无疆界线可依凭,而是以连片的禁山。宋朝直辖郡县与羁縻地区的疆界是点状控制的模糊疆界,其特点是没有举行双方会商的全线划界,而是在冲要之地设置城砦,标示界限。利用地理环境进行点状的控制或防御是惯常通例,如维克多·普莱斯考特等所指出的,沙漠、直线走势的山脉与宽阔的河流是天然的防卫屏障,“防守者可将力量集中部署在有关的通道和交汇处”。宋朝与羁縻各族的疆界正是受限于或利用了地理环境。宋朝与相邻政权间的中间地带也成为宋朝与这些政权间片状的自然模糊疆界。有学者据宋太祖“画大渡河为界”一说认为“宋与大理以大渡河为界,边界形态呈现线状,并以河流为标志物”。事实上,此说是指宋朝放弃对大渡河南越嶲诸郡的直接统治,即“弃越嶲诸郡”,作为宋朝与大理隔离地带,使大理“欲寇不能,欲臣不得”。越嶲诸族被称为“大渡河外蛮”、“黎州诸蛮”,同时臣属于宋朝和大理。宋朝也承认他们与大理的统属关系,册封代表大理来贡的卭部川蛮首领诺驱为“云南大理国主、统辖大渡河南姚嶲州界山前山后百蛮三十六鬼主、兼怀化大将军、忠顺王诺驱,可特授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旧忠顺王”。同时,这一地区诸族又有独立于宋朝和大理以外的秩序,如“邛部于诸蛮中最骄悍狡谲,招集蕃汉亡命,侵攘他种,闭其道以专利”,统辖各族,成为“大渡河南山前、后都鬼主”,或称“大渡河南邛部川山前、山后百蛮都首领”。越嶲诸族分布区并非宋朝与大理以任何形式认定的彼此疆界,但成为分隔宋朝和大理实际上自然的模糊疆界。大理国以东地区与宋朝间分布着左右江蛮、罗殿、自杞、五姓蕃等,较大渡河外诸蛮地理范围更广。该方向有“制御交趾、大理”的作用,但宋朝与大理除了南宋战马贸易外,极少从该方向展开交往。宋仁宗朝为交涉侬智高事,第一次派人出使大理国,因“南诏久与中国绝,林箐险深,界接生蛮,语皆重译,行百日乃通”。这些中间地带诸蛮没有表现为两属关系,但也成为隔绝宋朝和大理实际上自然的模糊疆界。有学者论及越南李朝历史时说:李朝自认为是“南帝”,其与“北帝”中国的“这条国界处于‘皇天’和地上的众神保护之下”。但交趾与宋朝间的线状边界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交趾从建国开始,与宋朝间就存在着双方都不直接统治的诸族,但与宋朝、大理相互认可对方对“大渡河外蛮”的统治不同,宋朝与交趾一直争夺对中间地带诸族的控制。如广源州蛮“自交阯蛮据有安南,而广源虽号邕管羁縻州,其实服役于交阯”。而当侬智高自建大历国、南天国时,交趾和宋朝都发兵攻讨。另如,恩情州“旧系省地七源州管下村峒,往年为交趾侵取,改为恩情州”,又因交趾征取过甚,来投宋朝;溪洞安平州李密“外通交趾,内结官吏”等等。此时宋朝与交趾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疆界线,对中间地带的控制在双方的博弈中不断变化,如天圣中宋朝指责交趾“不当擅赋云河洞”,到嘉祐时云河洞“乃入蛮徼数百里”,也使得双方疆界呈现片状和模糊的特点。到宋越熙宁战争,宋朝大军占据溪洞,使交趾“藩篱一空,彼何恃而窥边哉”,即其凭借侵扰宋朝的溪洞诸蛮不再具有中间地带的作用。西夏、吐蕃与宋朝之间都存在由生、熟户构成的中间地带,并无清晰界线。庆历议和后宋朝与西夏第一次商议疆界,即所谓“庆历旧例”,“以汉蕃见今住坐处当中为界”。但宋朝只承认“惟延州、保安军别定封界,自余皆如旧境”,双方亦未划定中轴线,因此到庆历六年(1046)环庆路“汉界”、“蕃界”“多方争执”,仍只是以蕃人和汉人居住区约指的中间地带为模糊疆界。宋朝与河湟吐蕃未见双方议界,而以中间的生、熟户地带为模糊疆界。元祐七年(1092)阿里骨请盟誓“汉、蕃子孙不相侵犯”,宋朝答复“汝但子孙久远,常约束蕃部,永无生事,汉家于汝蕃界自无侵占”。这只是不相侵犯的约定,没有划定“汉界”、“蕃界”的界线。澶渊之盟后北宋与辽朝在河北一带、元祐五年后北宋与西夏之间都形成了带状清晰疆界,具体表现为“两属地+中轴线”和“两不耕地+中轴线”,中轴线是区分双方疆界最为关键的清晰界线。澶渊之盟誓书承认既有实际控制边界,约定两国“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在河北“画河为界,所以限南北”,界河包括“雄州北拒马河为界”、“霸州城北界河”、“遂城北鲍河为界”、“安肃军自涧河为界”。界河不是以中流为界,而以北岸为界。两国边民皆不可入界河渔业。界河成为两国间明确的疆界线。但并非宋辽两国直辖之地直抵界河,界河两岸存在着一条两属地带,即双方边境城寨至界河之间的地带。生活在这一地带的百姓称为两属户,因“两属人户供两界差役”,又称两地供输人、两地输租民户。界河与雄州之间,即“拒马河去雄州四十余里,颇有两地输租民户”,雄州归信、容城两县就有两属户16900余。界河以北也同样分布着两属户。两属户一般只能生活于两属地。“两地供输人,旧条私出本州界,并坐徒”,“河北两地供输人辄过黄河南者,以违制论”。双方对两属户的管理和征调都遵行对等原则。宋朝“禁与两地供输人为婚姻”,同时“令两属户不得结亲北界”。“南北两界凡赈济两输户及诸科率,两界官司承例互相止约”。宋朝曾全免界河以北百姓税赋,使其“只于北界纳税,唯有差役,则两地共之”,欧阳修认为若宋朝“既不能赋役其民,即久远其地亦非中国之有。此事所系利害不轻”,坚持两国同等管理。这说明双方关系正常时两属地是双方共同管理、都不直接统辖的缓冲地带,但由于界河这一中轴线的存在,双方的疆界线是十分清晰的。宋、夏于熙宁四年局部划界,确定了双方认可的“两不耕地+中轴线”的疆界方案。熙宁以前,宋朝就在陕西单方面开掘过不少“边壕”。曹玮在环庆路“开边壕,率令深广丈五尺”,秦翰和张纶在陕西任职时也曾“规度要害,凿巨堑”,“开原州界壕至车道岘,约二十五里,以限隔戎寇”。这些“边壕”虽也被称为“界壕”,如有人称宋朝“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但属于宋朝单方开掘的军事防御线,而非双方议定的疆界线。边壕的目的和功能是“使足以限敌”。因而开壕是一种敌对行动,引起西夏的抗议,“移牒鄜延路钤辖李继昌言其事”。熙宁四年九月因宋、夏讨论绥德城外立界至。绥德城的划界方案被称为“绥州旧例”,成为元祐宋夏划界的基本方案,即“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之间量筑堡铺,十里之外并为荒闲”。西夏认可这一方案,“欲乘此明分蕃汉之限”,宋朝派官与西夏“首领相见商量”。宋朝“以界堠与西人分定疆至”,于“缘边封土掘壕,各认地方”。西夏遵守约定,主动“移绥州侧近本国自来寨棚置于近里,去绥州二十里为界”,“明立封堠”。双方都在十里荒闲地的己方一侧为界,掘壕立堠,形成宽十里的疆界地带。宋神宗本欲全面推广绥州划界方案,“遣官往诸路缘边封土掘壕”,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秦凤路、麟府路各派专官负责,计划在宋夏沿边全线掘界壕。但宋朝内部阻力甚大。范育提出此前宋夏自然疆界的“两不耕地,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指地为障,华夷异居,耕桑樵牧动不相及”,若掘封沟,“东起麟、丰,西止秦、渭,地广一千五六百里”,工程浩大,“使两边之民连岁大役”。吕大忠也认为“以两不耕种之地为界”的模糊疆界甚便,立界壕易发冲突。尽管宋神宗和王安石希望推行,但最终未能实现全面掘壕划界。熙宁四年“绥州旧例”确定了带状清晰疆界的划界方案。该方案没有对十里草地再作分割,应是在十里荒闲地两侧各自掘壕为界。元丰战争失败后,宋朝放弃消灭西夏的计划,重开疆界谈判。元祐四年议界,宋朝“欲用庆历旧例,以汉蕃见今住坐处当中为界”,而西夏“请凡画界以绥德城为法”。宋朝接受了“夏人所请,用绥州旧例”。但元祐五年划界时对“绥州旧例”作了调整,“于蕃界内存留五里,空为草地,汉界草地亦依此对留五里,为两不耕地。各不得于草地内修建堡铺”。将“绥州旧例”中十里荒闲地划出中轴线,各留五里两不耕地,形成了“两不耕地+中轴线”的清晰带状疆界。由于地形、水泉等因素影响,实际划界中并非所有沿边地段都严格执行“打量足二十里为约,不可令就地形任意出缩”的规定。西北地区水泉决定了何处生存,“彼此修筑堡铺,各于界取水泉地为便,岂可更展远近?”只能于界堠内“择稳便有水泉去处,占据地利修建,即不得分立两不耕地”。熙兰路则因地形“有难依绥州去处”,“二十里指挥,行于延安、河东与本路智固、胜如则可,行于定西城则不可”。最后只能“与夏人商议,各从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概许之”。但总体上体现了“两不耕地+中轴线”的清晰带状疆界的划界原则。宋朝与辽朝熙宁河东划界、与交趾元丰划界后,都形成了明确的线状疆界,宋金绍兴议和也划定了线状疆界。宋朝灭北汉后,在河东与辽朝直接接壤,澶渊之盟应承认了事实上的疆界。仁宗和英宗朝答复辽朝称宋人侵北界地时,或“以《河东地界图》示契丹人使”,或坚称“北来疆土,图证具存”。熙宁七年辽朝遣使来议河东地界,宋朝议界使刘忱“在枢府考核文据,未见本朝有尺寸侵虏地”,建议“坚持久来图籍疆界为据”。此“图籍”应指澶渊之盟认定的双方明确界线。但宋自取河东,特别是雍熙北伐后,大量边境居民内迁,形成大片空地,宋廷禁止百姓进入耕种,又称“禁地”。代州、岢岚、宁化、火山四州军都有“禁地”,仅“代州、宁化军有禁地万顷”。辽人不断侵入“禁地”,如“代州阳武寨旧以六蕃岭为界,康定中,北界人户聂再友、苏直等南侵岭二十余里”,宋朝节节退让,“别立石峰为界。比年又过石峰之南,寻又开堑以为限”,“天池庙本属宁化军横岭铺,庆历中,尝有北界人杜思荣侵耕冷泉谷”。可见,禁地是宋朝“自空其地,引惹北人岁岁争界”,“戎人侵耕,渐失疆界”,疆界变得模糊不清,造成边境安全隐患,宋朝因而重新开放禁地,以期“沿边地有定主,无争界之害”。但直到宋神宗朝,河东疆界争议问题仍然存在。熙宁七年辽朝派泛使萧禧提出“代北对境有侵地,请遣使分画”,双方举行了一波三折的河东议界。宋朝希望“以南北堡铺中间为两不耕地,又不可,则许以中间画界,其中间无空地,即以堡铺外为界”,但辽使“漫指分水岭为界”,最后宋朝作出重大让步,“许以辽人见开濠堑及置铺所在分水岭为界”,划清“逐处地名指定分水去处”,即李福蛮地以现开壕堑处分水岭为界;水峪内以安新铺山头分水岭为界;西陉寨地分以白草铺山头分水岭向西接古长城上分水岭为界;黄嵬山立封疆界石壕子等。分水岭为界即以山脊为界,是清晰的线状疆界,如大茂山(恒山)“以大茂山分脊为界”。分水岭和平地都“分画地界,开壕立堠”,设立“缘边界壕”。划分了线状清晰疆界。熙宁战争结束后,交趾求和议,请“画定疆界”。双方派官商议交涉。宋朝“令安抚司差人画定疆界”,交趾提出“溪峒勿恶、勿阳等州峒疆至未明”,宋朝“差职官辨正”,与交趾所差黎文盛等会商。经过七年交涉,元丰七年(1084)双方“边界已辨正”,“以庚俭、邱矩、叫岳、通旷、庚岩、顿利、多仁、勾难八隘为界”,界外六县二峒划归交趾,上电、下雷、温等18处则“从南画界,以为省地”,归入宋朝。划界后宋朝省地与交趾直辖地直接接壤,双方以一系列关隘作为线状疆界,划清界至。绍兴八年(1138)宋金议和,南宋希望以黄河旧河为界,“尽得刘豫地土”,实际结果是“以新河为界”。但仅维持一年余。绍兴十一年宋金议和划界,金朝“本拟上自襄阳,下至于海以为界”,即以江为界,最后宋朝付出巨大经济代价,得以“以淮水为界。西有唐、邓二州”,约定“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指金朝——引者注)。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指南宋——引者注)沿边州城”。次年双方交涉陕西划界,商定“于大散关西正南立为界首”,和尚原、方山原、方堂堡、秦州等都划归金朝,商州“以龙门关为界”,从而完成了双方全面划界,“自积石诸山之南左折而东,逾洮州,越盐川堡,循渭至大散关北,并山入京兆,络商州,南以唐邓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为界,而与宋为表里”。“以淮水中流为界”自然是线状疆界。唐、邓一带也有线状疆界,即“规措界壕于唐、邓间”,宋朝还对“分划唐、邓地界,并不亲至界首”的莫将和周聿各降两官。陕西疆界屡有变动,“大体以秦岭山脊为界”,陇西、成纪一带“以渭河和嘉陵江分水岭为界”。双方之间并无两属地或生熟户,而是相对清晰的疆界。
宋代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疆界形态,这种多样性反映出宋朝没有统一的疆界形态和划界原则,而主要出于错综变动的现实应对。疆界形态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背后是多样的关系形态。中国古代的华夷秩序从来都是多层次的。宋朝与境外政权间的地带根据关系形态和统辖方式,可分为直辖郡县、“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过羁縻则谓之化外”三个层次。羁縻地带包括南方羁縻州和北方受宋朝官封的蕃部,被称为“熟蛮”、“熟蕃”或“熟户”。这是中华“天下”圈层服制的现实映照。从宋朝的视角出现了省地(正州)与熟界、熟界与生界两种疆界,如湖南“内地省民居其中,外则为熟户、山徭,又有号曰峒丁,接近生界”。熟界与省界存在和区分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宋朝而言,熟户与省民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入版籍,是否承担所有赋役。如湖南路沿边“省民与徭人交结往来,以田产擅生交易。其间豪猾大姓规免税役,多以产业寄隐徭人户下。内亏国赋,外滋边隙”。可见省民承担赋役,而熟徭不承担。因此宋朝以“复其租五年”鼓励收回落入蛮人的省地,甚至由官府“代给钱偿之”,赎回省民卖给徭人之田,使其重新归入税籍。对逃入溪洞的省民“复归者,与蠲丁税三年”。而熟蛮之田在“在版籍常赋之外”,所以“不许汉人侵买夷人田地”,有“谿峒之专条”规定“山徭、洞丁田地并不许与省民交易”。但沿边州郡“利于牙契所得,而又省民得田输税,在版籍常赋之外,可以资郡帑泛用”,获得属于地方财政的税收,因而“山徭、洞丁有田者悉听其与省民交易”,省、蛮交易实际上普遍存在。除峒丁、蕃兵等兵役外,熟户承担赋税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宋政府配给峒丁、蕃兵的土地,即“峒丁等皆计口给田”,“一夫岁输租三斗,无他徭役”,负担轻于省民,故其田“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罚”;二是熟户耕种省地,如海南黎人“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赋役者名熟黎”,显然耕作省地的熟黎需承担赋役,即羁縻各族“耕作省地,岁输税米于官”;三是羁縻州(蛮地)转为正州(省地),其人地入版籍、纳赋役。如海南黎峒田土“既投降入省地,止纳丁身及量纳苗米”;梓州路罗个牟村蛮熙宁七年后成为“省地熟夷,纳二税役钱”,“既纳税赋,即是省地熟户。见在图籍,并系熟夷”;宋神宗朝开拓南北江,多州峒蛮“各以其地归版籍”,“比内地为王民”,“出租赋如汉民”;邵州徭也“籍为省民,隶邵阳县,输丁身钱米”;等等。王明珂称“赋税是(蛮夷)进入华夏之域的痛苦代价”,即可包括后两种情况。大多数成为省地的蛮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难以提供支撑建立直接统治所需的成本。对于熟地转为省地,宋朝总体上十分审慎。太宗时“溪、锦、叙、富四州蛮相率诣辰州,愿比内郡民,输租税,诏本道按山川地形以图来献。卒不许”。神宗朝经制荆湖,变羁縻州为正州,“设官屯兵,布列砦县”,“荆湖两路为之空竭”。徽宗朝改羁縻南丹州为正州观州,设官吏六十余人、厢禁军一千余人,岁费钱一万多贯、米八千多石,“州无税租户籍,皆仰给邻郡”。融州析出平州后,“糜费甚于观州”,不少州又陆续恢复为羁縻州。但在荆湖路和四川都不乏成功的事例,且变羁縻州为正州,不仅有将非版籍的民地纳入版籍的意义,也是对省熟之界的渐次消解和推移。这不仅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趋势,如王明珂所论秦汉羌人和华夏边缘的西移,姚大力指出华夏取得与周边部落的相对优势后即不断拓展生存边缘,将新认知的人群不断纳入“蛮夷”的范围。中原王朝通过移民、战争、自然融合等多种途径,不断向外推延和消解省熟之界。相对于文化上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进于夷则夷之的夷夏之变,经济上的省熟之变对宋朝政府具有更为实际的意义,其身份变换直接影响国家赋役和统治根基,因而必须划分省熟之界。宋朝对省熟的区分也十分务实,认为“不知用兵之时,所费钱粮若干,得地之后,所得租赋若干”,常是“竭中原生民之膏血,以事荒远无用之地”。中国古代一直具有用农业经济和国家赋役的眼光看待向四夷开拓的实用主义传统。汉代就有人说“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唐人亦言“用武荒外”,是“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加之宋朝对羁縻地区通过政治上朝贡和册封、经济上回赐和互市、军事上设置镇砦,建立成比较完备有效的控扼体系,且熟蛮势力分散弱小,易于控制,不构成对宋朝的严重威胁,故无必要进行双方议界,划分清晰边界。从官方管理的角度,省熟疆界形态虽是模糊的,而疆界意识是清楚的;但对于省熟交界民众而言,他们跨界互动更多关注现实经济关系,并无政治疆界意识,甚至也无清晰的华夷之辨。从沿边族群的角度,省熟之界本来也是模糊的“带状华夏边缘,而非地理上线状的、截然划分的汉与非汉的族群边界”。不仅省熟之界如此,清晰疆界也因双方民众的互动而变成“边缘地带”或“过渡地区”。如拉铁摩尔所说,“线状边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绝意义,会渐渐变得缓和中立,而这种边界也会从一条物理边界本身转为边疆地带的人群”。这是疆界意义对于官方和民间的区别。宋朝将直辖地区与非直辖地区总体上分为“汉界”和“蕃界”(“蛮界”),如“宜、融、柳等三州部内百姓及蛮界户人等”之“部内百姓”就是汉界百姓。与除境外政权外的相邻“蕃界”(“蛮界”)再分生户、熟户,西北诸蕃“有生户、熟户,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略者谓之生户”。海南岛以黎母山为中心,诸蛮环居,“内为生黎,外为熟黎”;又称“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其居山洞无征徭者为生黎”。这类无赋役、不服属的生蛮还包括莫猺、夷人、獠人等,“其名不可胜纪”。生界蛮与宋朝无政治从属关系,不承担赋役,“不授补职名,且官中亦不勾点彼族兵马”,较熟蛮对宋朝安全的威胁更大。划分生界与熟界的目的是稳定熟蛮。宋朝对熟蛮多种手段的控制体系,既消减其对宋朝安全的威胁,也使其成为隔绝省地与生蛮的安全屏障,即宋人所说“立法有溪洞之专条,行事有溪洞之体例,无非为绥边之策”。熟蛮也会侵犯省地,但因对其有约束机制,所以“与生夷反叛不同,可招纳之”。总体上宋朝能够控制和利用熟蛮,使其“藩篱内郡,障防外蛮”,所以“缘边熟户号为藩篱”,熟户蕃部“从来国家赖之以为藩蔽”。“平时省民得以安居,实赖熟户、山徭与夫峒丁相为捍蔽”,“生界有警,侵扰省地,则团结熟户、山徭与夫峒丁操戈挟矢以捍御之”。宋人甚至称溪州蛮“为辰州墙壁,障护辰州五邑,王民安居”。熟蛮成为省地与生界之间的安全保障地带。生界与熟界是宋朝根据其与本朝关系所作的区划,而非两者间相互认知的界限。如果宋朝对条件成熟的生蛮建立了间接统治,该生蛮就转化成了熟蛮,如有黎人都统领“王氏居化外”,因帮助平定黎乱有功,接受册封,从生黎转为了熟黎;甚至可能转为省民,如淳熙八年(1181)“化外黎人闻风感慕,至有愿得供田税比省民者”。如果说省熟和生熟之界尚符合“天下”秩序结构,诸“国”之间的清晰疆界则有损于华夷秩序,其出现主要是现实应对的选择和结果。清晰疆界全部出现在宋朝和与之有强烈对抗的境外政权之间,是冲突和对抗的结果,疆界的清晰程度与对抗程度成正比。且都伴随着对彼此“国”的地位的承认。宋代首先在宋辽之间形成了清晰疆界。宋初河北沿边“界河”两岸是宋辽双方实际军事控制区的交汇地带,由于宋朝“恢复”幽燕目标的存在,不可能进行双方议界,这一地带不可能成为双方共同认可的疆界地带,“界河”更不可能成为双方认可的清晰疆界线。从实际军事控制带向“界河+两属地”的清晰疆界的转变确立于“澶渊之盟”。如欧阳修《边户》诗所写:“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自从澶州盟,南北结欢娱。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边户”所居地带被双方划定为以界河为中轴线的清晰的带状疆界。这条疆界是双方打出来的。经过太平兴国四年(979)和雍熙三年(986)两次北伐及一系列军事争战,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在河北议定了“界河+两属地”的疆界形态。在河东也承认了既有疆界,但由于宋初迁徙边民,空出“禁地”,为熙宁间辽方提出议定河东疆界埋下了隐患。宋朝与西夏、交趾间的疆界都经历了从模糊向清晰的转变,伴随着宋朝对两政权从“藩镇”到“国”的政治身份认可的变化。宋夏第一次议界是庆历议和后。北宋前期将西夏视为藩镇,册封以藩镇官衔。元昊称帝后,宋朝武力解决失败,双方议和,宋朝封其主为“夏国主”,承认其“国”的地位。双方议界,即前述“庆历旧例”。熙宁四年宋朝着力于开拓河湟之时,与西夏在绥德城划界,即“绥德旧例”。宋夏元丰战争结束后,重新议界,于元祐五年形成了“中轴线+两不耕地”的清晰疆界。对交趾,宋朝从一开始也是册封藩镇官衔,以“恢复”郡县为目标,熙宁战争双方都遭受重大损失,宋朝放弃了“恢复”目标。事实上承认了交趾“国”的地位,双方正式议界,划分了清晰的疆界。南宋与金朝的划界更是在经历生死争战之后。金灭北宋后,只承认自己先后扶持的张楚和刘齐傀儡政权,“金国只纳楚使,焉知复有宋也”,“是则吾(宋)国之与金国势不两立”,意味着宋金处于战争状态。一系列战争后,宋高宗急于求和,金朝也感到难以灭宋,双方于绍兴八年议和,以河为界。但不久战争再起,到绍兴十一年和议,形成了以淮河中流为界的清晰线状疆界。羁縻各族对宋朝的威胁无外乎“时复出没,不过什百为群,夺禾稼、盗牛马而已”;而辽、西夏、交趾和金对宋朝才构成真正威胁。李纲所说“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若此其甚也”,指的就是这些政权。宋朝与这些政权的冲突和对抗使双方最终选择划界以维持和平与均衡。正如王安石所说“侵争之端,常因地界不明。欲约束边吏侵彼,亦须先明地界”。北宋清楚“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虏”。辽朝也清楚“国家大敌,惟在南方”。双方经过激烈争战,都认识到议定疆界,彼此“各守疆界”、“不得交侵”是维持均衡的最好办法。宋与西夏、交趾都把划疆界作为维持双方稳定关系的前提。为了保持与西夏的稳定关系,宋朝曾多次要求西夏“候诸路地界了日,可依前别进誓表,然后常贡岁赐并依旧例”,“约地界已定,然后付以岁赐”等。西夏却坚持“既得岁赐,始议地界”。元丰元年交趾请恢复朝贡,宋朝同时“令安抚司各差人画定疆界,毋得辄侵犯”。“强弱均而和,则彼此受其利”,辽、夏、金从宋朝获得大量岁币,而宋朝也以远少于用兵之费的岁币得到了和平。交趾从划界中得到了宋朝逐步承认,最终获得“国”的地位,意味着消除了宋朝“恢复”的威胁。如上文所述,宋朝与辽、夏、交趾、金的清晰疆界都是双方共同商议划定的,与有的政权还举行了多次划界。如宋辽澶渊之盟议界后又于熙宁年间在河东议界;宋夏之间就于庆历、熙宁、元祐、元符年间多次举行议界;宋金也于绍兴八年、绍兴十一年、绍兴三十二年、嘉定元年(1208)四次举行议界。除了商议划界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做法外,还形成了稳定的处理疆界问题的机制。一是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勘界和疆界纠纷处理机制。宋朝与辽、夏、交趾、金数次勘界都由双方派员会商划界,实地勘定。如宋辽熙宁河东勘界。辽于熙宁七年派萧禧入宋“言代北对境有侵地,请遣使同分画”,提出重新议界。宋朝“差职官与北朝职官就检视定夺”,派出刘忱为正使的议界使团,辽朝派出宰相萧素为正使的议界使团。双方反复磋商,实地勘察,如辽人提出“蔚、应、朔三州分水岭土陇为界”,但双方实地“行视无土陇”。熙宁四年讨论宋夏划界时,宋神宗提出“恐不须问彼,便可自立界至”,王安石提出“如此即不可”、“有伤大体”,表明勘界必须双方共商。元祐宋夏划界时,宋朝派遣“分画地界官,遵依朝旨,坚执商量”,“候夏国差到官,详先降指挥,同共商量分画”。元丰元年宋朝与交趾勘界,双方“各遣人画定疆界”。宋辽熙宁河东划界和宋夏元祐划界都因利益分歧,几次中断,但最后还是回到谈判桌,共同商议划定了疆界。宋夏议界时,双方因地界争议“迁延不决,舍归本国,招之不至”,最后还是“地界复议如故”,达成一致。绍兴十一年宋金议界也是双方使节往返商议,现场勘验,宋朝派周聿“充京西路分画地界官”,郑刚中“充陕西路分画地界官”,莫将“往唐、邓州分画地界”,“照南北誓书文字,仔细分画”。疆界划定后,解决疆界纠纷也有相对明确的机制。非勘界问题的一般纠纷由边境有关官员交涉解决,即“凡疆场之事,皆在边臣处画”。如辽朝侵界立寨等疆界纠纷,“不烦朝廷,只委边臣,自可了当”。熙宁七年辽使萧禧入宋提出河东疆界不明,宋神宗回答:“此细事,疆吏可了,何须遣使?待令一职官往彼计会,北朝一职官对定,如何?”说明疆界纠纷一般可由边境官员交涉解决。二是形成了疆界文案保存制度。疆界文案成为双方解决疆界问题的依据。宋辽解决疆界纠纷的根本依据是景德誓书。文彦博说若有纠纷,“以誓书为证,彼将何词以亢。纵骋诡词,难夺正论”。景德誓书约定,双方可修缮沿边城寨,但不可营造和侵边。宋仁宗朝欧阳修指出“北虏创立寨栅,已违誓书”。庆历五年“北界近筑塞于银坊城,侵汉界十里。其以誓约谕使人,令毁去之”。皇祐元年(1049)再侵据银城,“谕以誓约之意,促令毁去”。界河打渔是常出现的疆界纠纷,也依据誓书相交涉。辽朝提出“以北人渔界河为罪,岂理也哉”?宋朝回答“两朝当守誓约,涿郡有案牍可覆视”,“界河之禁,起于大国统和年,今文移尚存”。宋辽熙宁河东划界时,宋朝用澶渊之盟认可的相关文案作为依据,指出“誓书若不为凭,即代北之地止以图籍照验”,“坚持久来图籍疆界为据”。刘忱去议界前特“在枢府考核文据,未见本朝有尺寸侵虏地”。但辽朝本就是趁宋西边用兵之机敲诈,“虽图籍甚明,而诡辞不服”,宋朝只能做出让步。河东划界结束后,宋朝完整保存了划界的文图档案,将“与北人分画缘边界至,其山谷、地名、壕堠、铺舍相去远近等,并图画签贴,及与北人对答语录编进入”。宋朝与西夏的历次议界都被保存并作为“旧例”。元祐议界时宋朝最初提出依“庆历旧例”,西夏坚持用“绥州旧例”。宋朝最终同意用“绥州旧例”,而“夏人执以为据”。宋金绍兴十一年誓书所定以淮水中流和唐、邓间为界,成为隆兴和议与嘉定和议议界的依据。宋辽定界后,河北段界河就成为国界,过此河即出国境。宣和四年(1122)宋朝出兵幽燕,大军刚过界河即遇辽军来战,宋军不敢交战,“遂却军复回界河之南,滨河驻兵”,“北人隔河来问违背誓书”。双方都把界河作为国界。张叔夜被金人掳掠北迁,道中绝食,“既次白沟,驭者曰:‘过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复语。明日,卒”。由于过界河相当于出了国境,因此张叔夜悲恸而绝。宋夏划界后,“内十里筑堡铺供耕牧、外十里立封堠作空地例,以辨两国界”,“界堠内地即汉人所守,界堠外地即夏国自占”。沿疆界巡逻“人马巡绰所至,已立界堠之处为界”。宋朝与金朝也约定“务欲两国界至分明”。既有了清晰的国界,守国就不是一般意义的守边,而是守界,即“疆界既辨,则边圉不可不谨”,“我疆彼界,毋相侵犯”。如宋朝设河北界河巡检,“沿界河分番巡徼”。宋夏定界后,宋朝令沿边诸路“各据巡绰所至处,明立界至,并约束城寨兵将官,如西人不来侵犯,即不得出兵过界。尔亦当严戒缘边首领,毋得侵犯边境”。双方都各守国界。正因为视疆界为国界,所以过界即为侵犯。宋朝令宋夏沿边官员“各守疆界。如是贼马侵入汉界,仰痛行掩杀,即不得令人马擅入西界捉杀人口,引惹边事”。宋辽界河方面“禁缘边河南州军民于界河捕鱼”,同时“契丹民有渔于界河者,契丹即按其罪”。赵滋守雄州时,辽人侵入界河打渔、运盐,赵滋“戒巡兵,舟至,辄捕其人杀之,辇其舟,移文还涿州,渔者遂绝”。河东沿边官员需“定验北人有无侵越旧界,及边人有无侵北界地樵采”。辽人越过边界垒石为墙,宋即派人“移牒毁拆”,“有再垒下石墙,侵越界至,即便依前拆毁”。需要指出的是,讨论宋代“国”界问题应遵循宋代的历史逻辑,用宋人的眼光看待其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作为自称中华正统的宋朝与“蛮夷之邦”签约、划界,傅海波、葛兆光等学者均赋予其变革意义,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为坐标,赋予宋辽划界以“近代性”意义。如傅海波、崔瑞德所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认为宋辽“两国从海边到黄河拐弯处的边界被清晰地划界并由双方警惕地守卫,这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国际边界,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也代表了西方一类学者的观点。中国学者也有持类似观点者。有人认为,宋代以前历代王朝的边界仅是实际军事控制线,不具有国界的意义,而宋与辽、金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就有了国家间边界的意义”,不过“各方的控制线在法理上仍是传统的政权界限而非国家边界”;近代清朝与沙俄进行边界谈判缔约,得到西方诸国的承认,是法理上认可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天下观才转变为国家观,“近代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才最终形成”。意即以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考量,宋代是中国“天下观”下的有限变革。另一类认为宋代疆界具有中国古代自身传统发展中的变革意义。有学者反对套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和欧洲的“近代”标准,认为在此问题上“中国历史不必按照欧洲历史来裁长补短”,不同意“古代中国主要就只有‘边疆’而没有‘边界’,现代中国才有‘领土’和‘国界’”的看法,认为“从宋代开始出现的有可能走向国境清晰,认同明确,民族同一的民族国家的趋势”,“呈现出与欧洲不相同的国家建构路径”。宋代“官方组织的‘勘界’其实已经开始表明有限的‘民族/国家’在意识中逐渐形成,明确的‘边界/国境’也在事实上呈现”,“这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国境’,也有了‘国’与‘国’对等外交的意识”,“这在唐代以前的中国是几乎没有的”。宋代出现的“国境的存在和国家主权意识”,“很清楚地形成了汉族中国自我确认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还有学者认为就政治疆界划分而言并非宋辽划界方始产生,但宋代“各政权之间界至谈判、勘定等皆王朝政治地理的新因素”,而且这种新因素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政治史背景中看都是空前的。这虽未以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作为判断坐标,但也认为宋辽划界说明“当时出现了与近代民族国家相近的‘国家’意识”。对于宋代划分清晰疆界具有变革性的判断,不论是将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作为参照,还是强调中国古代自身传统中的变革,都是以“近代性”作为标准。如果将欧洲兴起的近代边界理论作为参照,表面看来宋代疆界产生程序及疆界形态无疑具有了很强的“近代性因素”。维克多·普莱斯考特将陆地边界演变或形成分为四个阶段:分配、划界、勘界和管理,“分配指的是有关领土分配的政治决定,划界涉及具体边界地点的选择,勘界是在实地标示出边界,管理是指边界的维护”。划界与勘界的区别是前者指在语言或纸面划定国界线,后者是“确定边界的最后步骤,即现场标出边界”。边界产生过程也可以分为定界(即分配)、划界、勘界三个阶段。邵沙平主编的《国际法》认为边界形成主要基于两种事实:一是由传统习惯而形成,即传统边界线;二是依条约而划定。划分边界一般还包括绘制地图和标界等阶段,为边界管理和维护提供依据,还通过条约“规定双方有维护边界标志的责任,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边界标志被损毁或移动”。关于边界标志的类型,《奥本海国际法》指出,“一般情况下可以将边界标志分为两类:一类是使用山脉、河流等自然标志的自然边界;另一类则是使用石头墙、栅栏等人为标志的人为边界”。近代“人为边界”也包括以弧线或直线确定的几何学界限或以经纬度确定的天文学界限。而陆地“自然边界”通常“沿分水岭、山脊这些明显的地貌划定,或以河流中心线或主航道中心线等为界限”。而河流划界有三种方法,即河流中间线、主航道中心线及河岸。宋与辽、夏、交趾、金的议界基本上经历了定界(即分配)、划界、勘界三个阶段,也包括勘界后的边界管理。如宋辽河东划界就经过了双方派员商议、划定疆界、实地勘验、绘制图标等过程,并按协定维护勘定的疆界。宋代的疆界形态既包括山脊、分水岭、河流等按自然地形划定的自然边界,如宋辽界河以河岸为界、宋金则以淮水中流为界,也包括树界标、建界墙、掘界壕等人为疆界。但是,宋代疆界形态和产生程序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吗?如此相似的“近代性因素”就意味着变革吗?这样的疆界特征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才出现的新产物吗?葛兆光指出,宋代“勘界”显示的中国古代开始出现的国境和民族国家意识及其至清代的演进,呈现出与欧洲不同的建构路径。这提示我们不能机械地套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将宋朝通过双方共同勘定、载之盟约或文案的“国界”仍视为非法理上的国界。陶晋生指出,宋人已经有了“多元国际系统”的两个重要观念:“一是认知中原是一个‘国’,辽朝也是一‘国’;二是认知国界的存在”,“宋人对国界的重视,足以推翻若干近人认为传统中国与外夷之间不存在‘清楚的法律和权力的界限’的看法”。宋朝与辽、夏、金、交趾的勘界就是双方议定,载之盟约的“法律和权力的界限”。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宋代勘界是否在中国“路径”中堪称一次变革呢?显然也不是。宋代疆界形态和产生程序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出现,而是前已有之。长城是一个初显的案例。作为边界,长城是一个复合的边界,“代表统一的华夏帝国的北方资源边界,也是华夏的北方族群边界”,同时也是“标识本国的政治边疆”。秦朝长城主要还是单方设定的疆界,汉代则得到匈奴等北方民族的承认。汉文帝致匈奴书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约定“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而且当时双方是对等关系,国书称“二国”、“两主”、“邻敌之国”,甚至称“独朕与单于为之父母”,互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长城成为两国共同认定的疆界。唐代与吐蕃的议界则具备了上述宋代所有的程序。唐蕃间最重要的会盟议界是建中会盟。该次议界,“二国将相受辞而会”。在建中四年(783)正月第一次会盟中,唐朝派中书侍郎张镒与吐蕃相尚结赞盟于清水,议定两国疆界,即“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并相约“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双方疆界除了黄河、大渡河等自然山川为线状疆界外,其他地区为“唐界+闲田+蕃界”的带状疆界,但唐界和蕃界是相对清晰的,这个带状疆界因而也是相对清晰的。清水之盟后,双方在议定的边界沿线树立界碑,并作为双方疆界不可侵犯的标志。如其后吐蕃宰相尚结赞曾说到“本以定界碑被牵倒,恐二国背盟相侵”。“疆场既定”后,唐朝宰相李忠臣与吐蕃相曲颊赞等在长安设坛盟誓,宣读盟文,并将“盟文藏于宗庙,副在有司,二国之成,其永保之”。建中会盟划界经过了议界、划界、勘界等程序,并载之文字。边界具有两个核心功能:区别“我者”与“他者”,即区隔的功能;保障本国安全,即防卫的功能。这也是一个政权或民族基本和本能的生存需求,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在遇到很强的对抗性外力时,就会产生更明确地区隔彼此的需要,当势均力敌的双方都具有这一愿望时,和议勘界及明确边界就自然出现。其本身并不都代表从传统到近代的变革。现代国际法界定疆界“是地图上想象的界线,分隔着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是一条划分一国领土与他国领土或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区域的界线,其作用在于确定各国之间领土范围”。维克多·普莱斯考特还指出“历史上,边界具有重要的防卫功能,外国入侵者一旦越过边界,将承担相应的后果”。古代和现代疆界都具有区隔和防卫功能。维克多·普莱斯考特等认为“中国的长城不仅旨在防范游牧民族侵扰,还旨在防止本国人外逃”,具有防卫功能。拉铁摩尔指出,“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一个固定的边疆,包括一切真正适宜中国的东西,隔绝一切不能适合中国的事物。长城就是这种信念的表现”。汉朝与匈奴约定的“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唐人说缘边关塞的功能是“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禁者也”,唐蕃会盟也有约定双方遵守划定的“汉界”与“蕃界”,“不得侵越”。这些都表明疆界具有区隔和防卫的功能。宋代也是将疆界作为区隔版籍与非版籍,以及守国的界限。从历史关系看,中国“‘有限国家’的意识大概从宋代就开始形成了”,“中国渐渐从无边无际的‘华夷’与‘天下’的想象中走出来,进入‘万国并峙’的现实世界,开始设定边界,区分你我”,也不能说是对宋朝的准确定位。事实上,宋代以前的王朝也要采用应对复杂多样的现实困境的弹性做法。当中原王朝强大,足以维持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时,便不存在与“四夷”勘定疆界的需要,自然疆界足以区隔华夷,保障安全,且无损于“华夏”尊严。如邢义田阐述长城两方面的象征意义:“从理想的一面看,修筑长城意味着中国的天子德威不足,不能于一统海内之余兼服八荒之外,成为真正的普天之下之主,象征了无奈与羞辱;从现实的一面看,它的修筑隔绝了北方草原和南方农业地带,象征着一道文明与野蛮、中国与非中国、人与禽兽、农业与游牧之间不可跨越的天限。”古人喜用“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之类不失华夏尊严的表述。宋朝对辽、西夏、交趾、金均不能取得优势而不得不承认他们为“国”,并与之勘定疆界。宋人曾一再感叹“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燕山“岂天设此限华夷”,“天限华夷”的自然疆界越来越不能发挥作用。势均力敌,甚至被动屈辱的对抗成为宋朝周边关系的常态,且强烈的外来压力如此深刻持久地影响着朝运是前所未有的,因而与辽、夏、交趾和金的全面划界成为保障安全不得不做的选择。勘定疆界成为宋朝与对抗的相邻诸国都具有的发展正常关系的需求,或者说疆界的功能是势均力敌的任何两国都希望的。陶晋生指出,中国古代政治家都了解对外族维持和平为首要,朝贡在其次,“和平既属首要,则对外政策的运用,必需具有弹性”。除了华夷秩序外,对外族的平等关系“时常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发生”。这是当理想的世界秩序不能实现时,不得不发展成的“实质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到唐代莫不如此。“传统中国固然具有一个很强的传统来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要求邻国称臣进贡,但是另一个传统也不可以忽视,那就是与邻国实际维持的对等关系”。如上文所论,划定疆界对宋朝与辽、金等国都有现实需要,都是应对现实需要的手段。如果说宋代勘界形式并非变革,那么宋代出现的“国境的存在和国家主权意识”是否在观念上代表了“很清楚地形成了汉族中国自我确认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或华夷、内外观念的变革呢?也不是。宋代的勘界反映了“理想”解说和“现实”应对的交织。对“理想”的解说需要坚守绝对理念,即华夷之辨,出于“现实”应对又需要采取弹性标准。不同形态的疆界,不论是模糊的省熟之界,还是清晰的“国”界,其功能都是区隔华夷,即“中国”与非“中国”。从地理概念而言,宋朝人所称“中国”就是直辖郡县和版籍人口。邢义田曾说“从秦一统天下,在现实的世界里,真正听命于始皇的不过是设有郡县的地方”。直辖郡县就是秦朝现实的地理“中国”。宋朝也是如此。北宋的政治话语认为辽、夏和周边诸族都不是“中国”。贾昌朝说,“西戎诸国,如沙州、唃厮啰、明珠、灭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丽、新罗等处,皆旧通中国。今为二虏隔绝,可募人往使,诱之来朝。如此,则二虏必憾于诸国矣。憾则为备,为备则势分,此中国之利也”。“二虏”指辽、夏。羁縻各族也不是“中国”。西南诸夷“唐末,王建据西川,由是不通中国”,溪州蛮“不知中国礼”,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广西诸蛮“宋兴,始通中国”等等。可见北宋人所称地理“中国”仅指其直辖郡县。南宋君臣在国内议事时也称金为夷狄。宋孝宗曾说金朝,“夷狄虽强,不可有加于中国”,而称金为“虏”、“丑虏”、“金虏”、“夷狄”等词更是常见于臣僚话语。南宋禁铜法令有“铜钱出中国界条约”,此“中国”就是指直辖郡县。从宋朝对“中国”与四夷大的区隔来说,区隔周边政权的“国”界与区隔熟蛮(蕃)的省熟之界并无本质的区别,而且不同形态疆界的功能是相同的。宋朝与华夷之辨并用的另一个解说工具是“夷夏之变”。宋人称契丹和西夏“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所为皆与中国等”,“岂可以上古之夷狄视彼也?”辽朝更是“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非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处,与中国好尚之异也”。他们已经是近于“中国”的夷狄了。南宋也用“夷夏之变”解释宋金关系。朱熹的弟子说金世宗“专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为‘小尧舜’”,朱熹回答:“他能尊行尧舜之道,要做大尧舜也由他。”就是认为金朝皇帝是行尧舜之道、近于华夏的夷狄。与这样的夷狄议界划界、对等并立无损于华夏的尊严,从而为划界作了合理解说。宋代没有统一的疆界形态和划界原则,因关系形态的不同和变化而形成多样的疆界形态,既有模糊疆界,也有清晰疆界。影响疆界形态的主要因素是关系的可控和对抗。疆界的清晰程度与对抗性呈正比。点状模糊疆界主要存在于宋朝省地与可控且能为其所用的熟蛮之间,片状模糊疆界主要存在于与对抗性不强或尚未表现出强烈对抗性的政权之间,带状清晰疆界和线状清晰疆界则是宋朝与境外政权对抗冲突的结果。对疆界形态的梳理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宋朝的疆域范围和层次。宋朝划分疆界的主要目的是现实的安全应对,其核心是区隔版籍与非版籍的民和地,保护赋役来源和“中国”即直辖郡县的安全,显示了宋朝对待周边关系时除构建华夷秩序之外的实用主义面向。从疆界的区隔和防卫功能,即划分“中国”与四夷,版籍与非版籍,保护直辖郡县安全的角度而言,省熟之界与诸“国”之界,有宋朝优势可控和均衡对抗之别,但都是此疆彼界,而无“天下之界”、“诸国之界”或羁縻之界的区别。宋代疆界的产生程序、形式及其体现的观念,总体上仍是对中国古代天下理想与现实应对、华夷之辨与夷夏之变、消解模糊疆界与发展清晰疆界等不同传统的承继和延续,只是宋朝周边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不同现象、传统和观念等在宋代同时并存,因而在具体做法有其时代的特殊性,但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变革,更不具有所谓西方历史路径意义上的“近代性”。
〔 作者黄纯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241 〕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历史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