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很多文史爱好者直到今天仍然认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成为讨论热点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叫魂》,是引领自己走入史学世界,或者彻底改变对历史学的偏见的读物。

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经由系统的翻译引进,越来越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相关研究及作者在英语世界里,通常局限于学术界和大学课堂,在当代中国却很容易成为媒体和普通读者关注的对象。
综合一些已有的研究,笔者认为美国自晚清以来对中国的研究,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和五次转折。最初的对华观察了解是在初始状态下,以晚清传教士和外交官为主要观察者的记录和分析,也有体制化的“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对传教士和一些学院派汉学家的整合。
这当中一般读者所熟知的研究,包括曾经影响鲁迅,并一直有后续争议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所著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还有卫三畏(S. W. Williams)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其成果兼具传教关怀、现实关照及美国国家利益的复杂成分,乃至一些文化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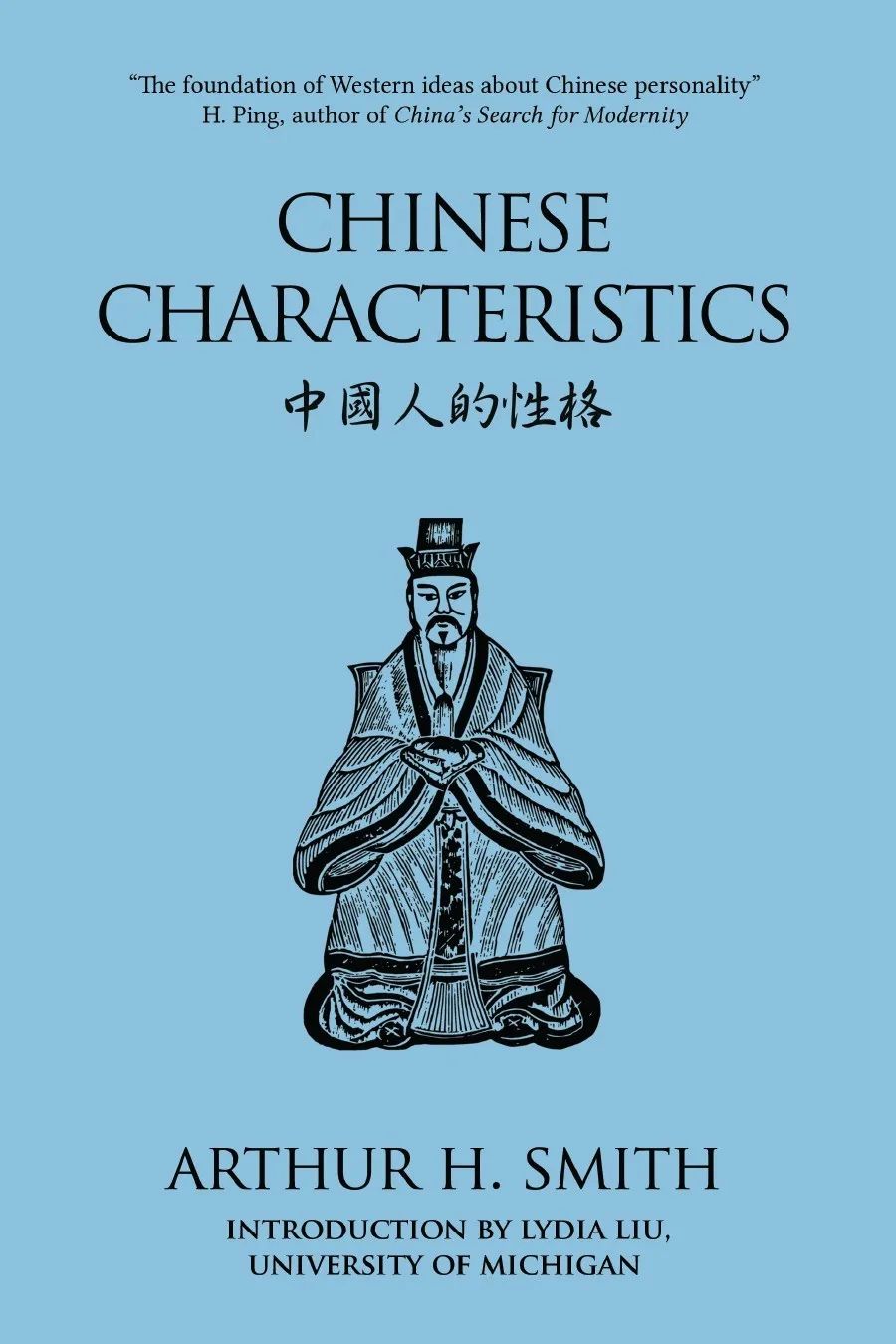
第二个阶段是在欧洲汉学影响下的美国汉学学术化和实证化阶段。其中,德国裔美国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贡献尤其巨大。笔者曾经查阅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劳费尔档案。他作为人类学家,曾经在1901年至1902年,受到美国人类学奠基人博厄斯(Franz Boas)以及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的支持和襄助前往中国考察,并搜集运回大量文物。在劳费尔的带动下,美国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也对20世纪中美文化和学术交流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美国本土汉学家,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卜德(Derk Bodde)、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等等。
第二阶段的学者更关注中国古典文化和哲学,到了第三阶段,才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将关注重点推向现代中国,把“汉学”变为以当代性和现实性为核心,强调多学科交融的区域性“中国研究”。费正清在其成名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中,不仅首次大量使用中文原始资料,还强调中国和英国的互动过程,共同创造了中西交往的新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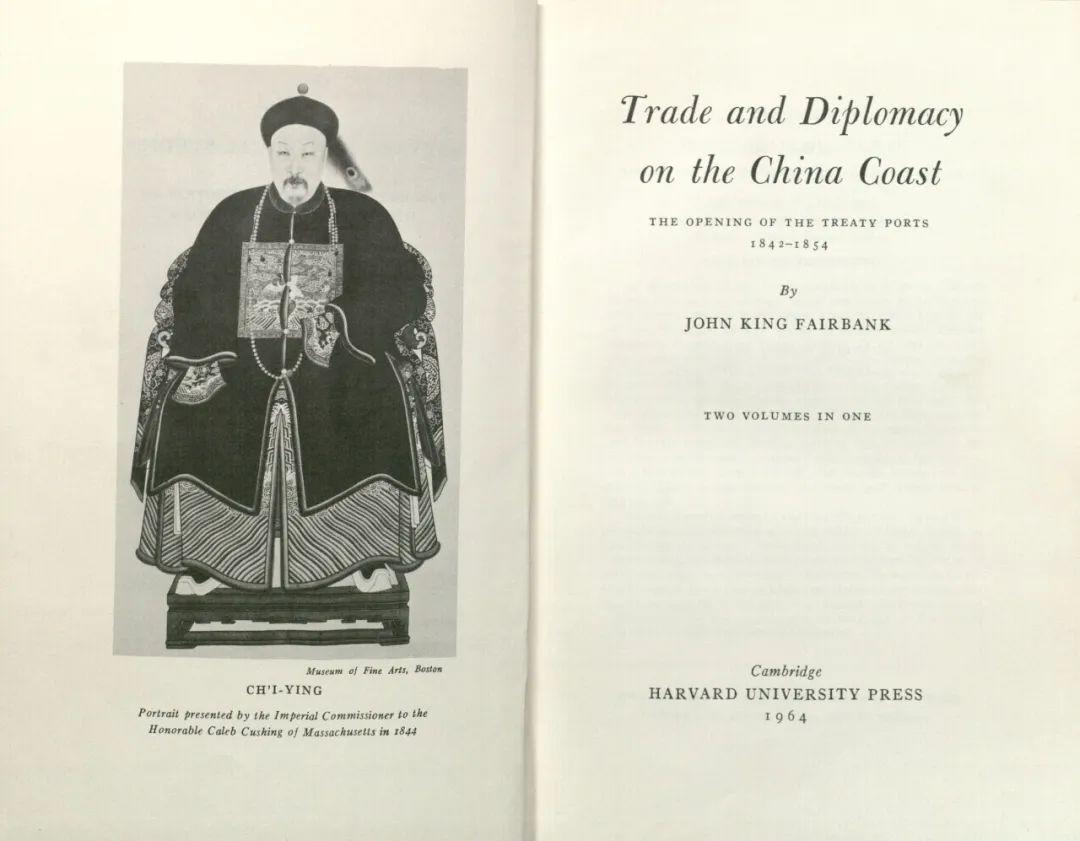
尽管后来把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看成一种过时的理论,但在本书问世的20世纪50年代,费正清确实是最早注意到晚清中国,在中西交往中的能动性和具备相应的制度弹性的学者。这是美国学界对华认知的一个重大转折。
在第四阶段,费正清的学生如柯保安(Paul Cohen)在越南战争的强烈冲击下,开始希望更深入地从中国内部看待中国,即后来正式提出的“中国中心史观”,而非以中西关系和中国必将实现西式“现代化”的框架,来看待中国历史。
在政治上,一部分激进学生和其他学者甚至认为,费正清(包括他当时的助手、刚刚过世的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所建立起来的战后以现代化为理论内核的中国学,其实是美国围堵中国战略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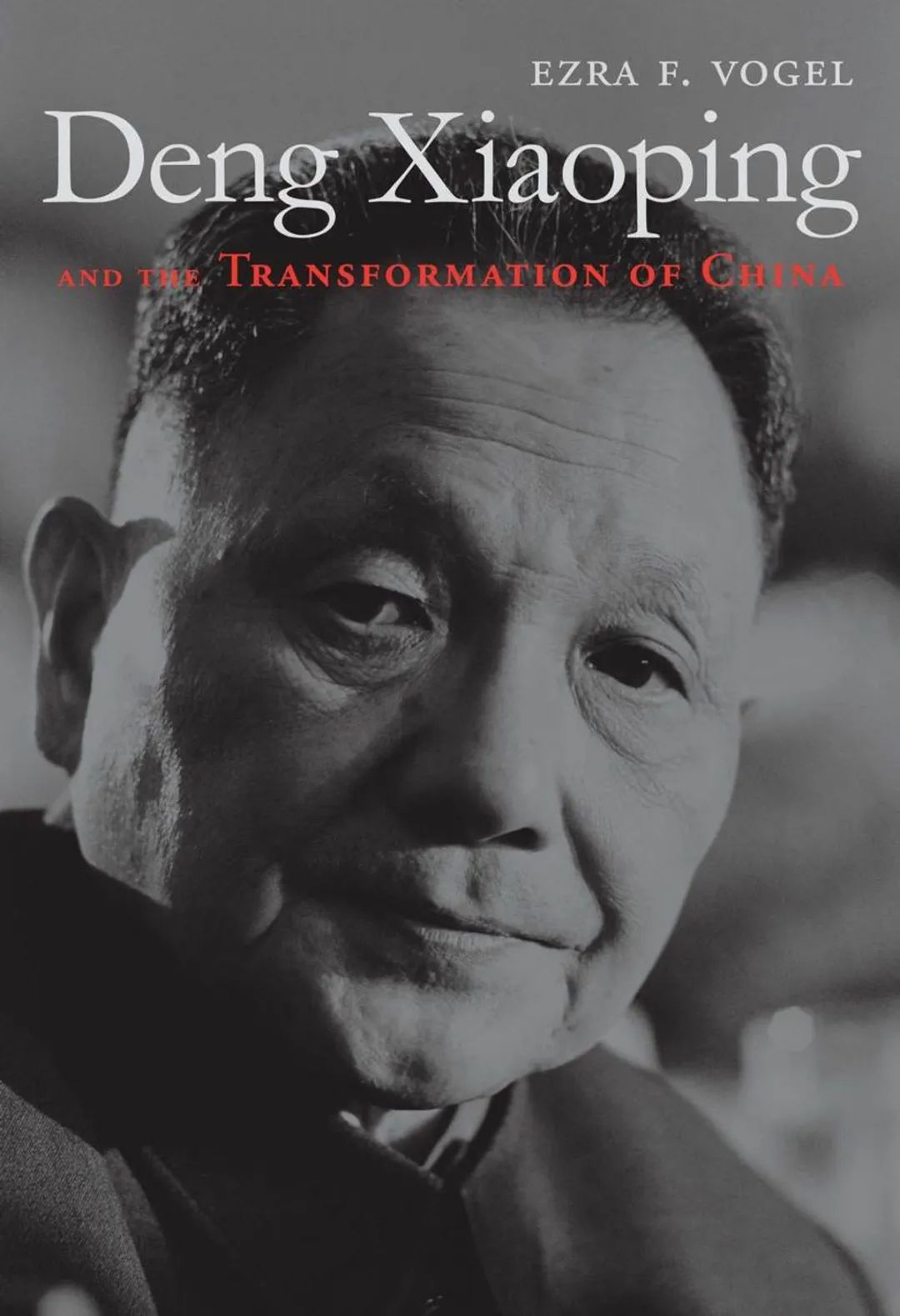
这部分年轻学者主张更为正面,和带同情地看待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实践,包括后来对当代中国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塞尔登(Mark Seldon)、毕克伟(Paul Pickowicz)和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等。周锡瑞的导师,是自认为从费正清算起的美国第三代当代中国学传人魏斐德(Fredrick Wakeman, Jr.)。在他看来,反越战期间激进的周锡瑞算第四代。
在方法上,由于受到法国年鉴派史学思潮和时间影响,这代学者也开始关注长时段变迁、地方史、下层民众等历史面向。孔飞力的《叫魂》、史景迁(Jonathan Dermot Spence)的一系列对小人物的研究,都可以归入这一路向。在一次接受访谈时,作为费正清学生的史景迁曾下意识地强调,自己和费正清的区别在于,费正清的研究更多是关注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为此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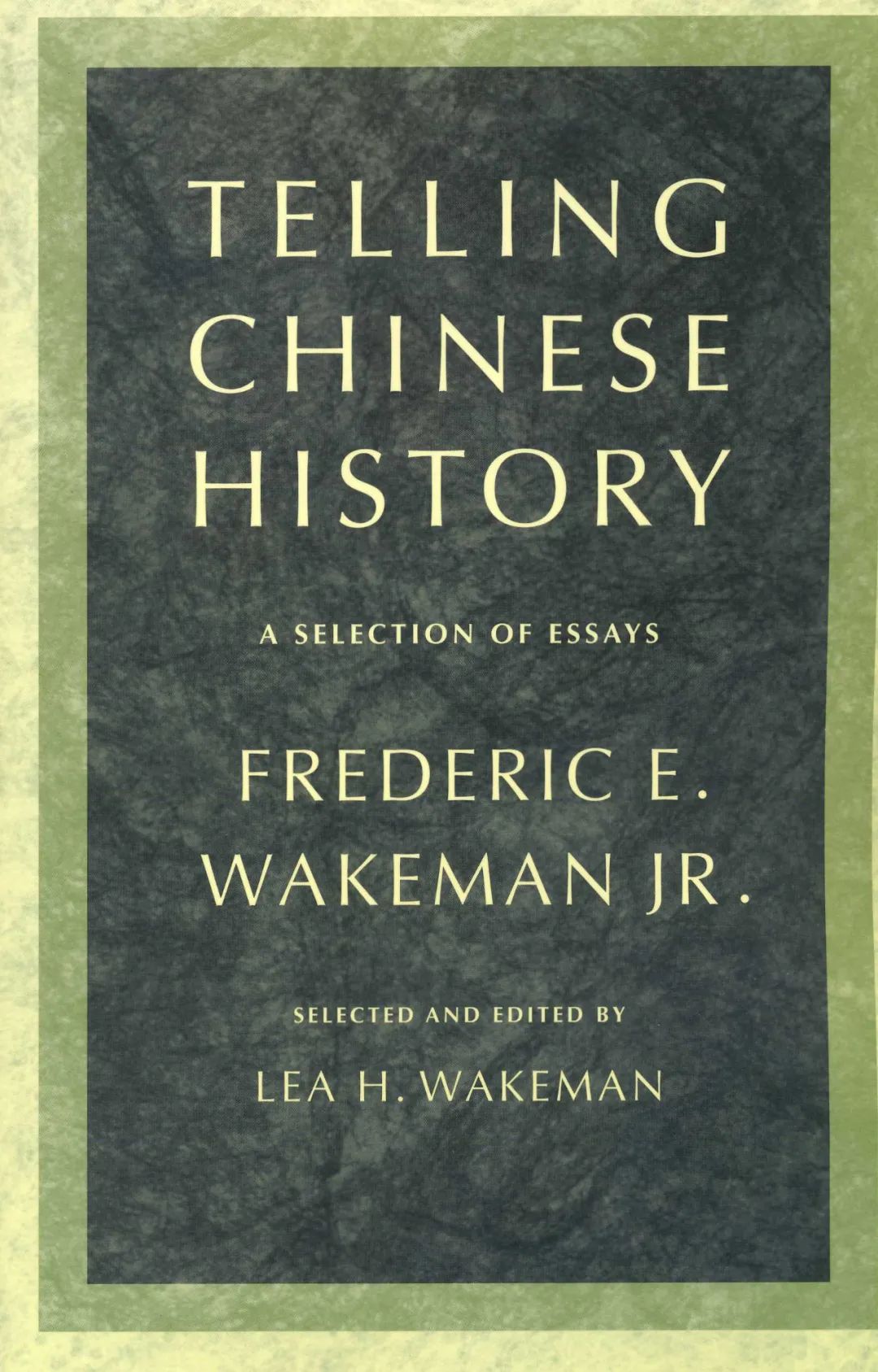
第四次重大转折是在当代社会理论的影响之下,把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公共空间理论,引入对近代中国的阐释中。在经过一系列辩论之后,魏斐德的观点显得落伍,而肯定中国存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学者,如史谦德(David Strand)、罗威廉(William Rowe)的意见占了上风,成了一种阐释近代乃至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
作为罗威廉“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这篇理论文章的中文译者,笔者认为这一视角是有价值和有生命力的,在实践中也直接影响了其学生、华裔学者王笛教授对成都街头文化的一系列研究。社会科学理论对这一代学人的影响,还包括采纳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以及黄宗智对“内卷”(involution)的移用。

第五次,也是最具争议的转向,是由史景迁的学生如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及其他清史学者发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把费正清时代以汉族官员和士大夫为核心的晚清史研究,推向清代前期及满族研究,并借此重思清代前期满族的“族性主权”问题、后期满族“汉化”问题、满洲贵族的体制创新能力,以及更宏观也更为敏感的“清朝”和“中国”的关系问题。
笔者倾向于在学术框架内讨论学术问题,姑且把这一流派(柯娇燕本人并不承认存在作为一个学派的“新清史”,也不承认自己是其中一员)及其共同的一些假设和视角的方法,看成一种反思和解构性的后现代史学立场加以研讨,并承认其长远学术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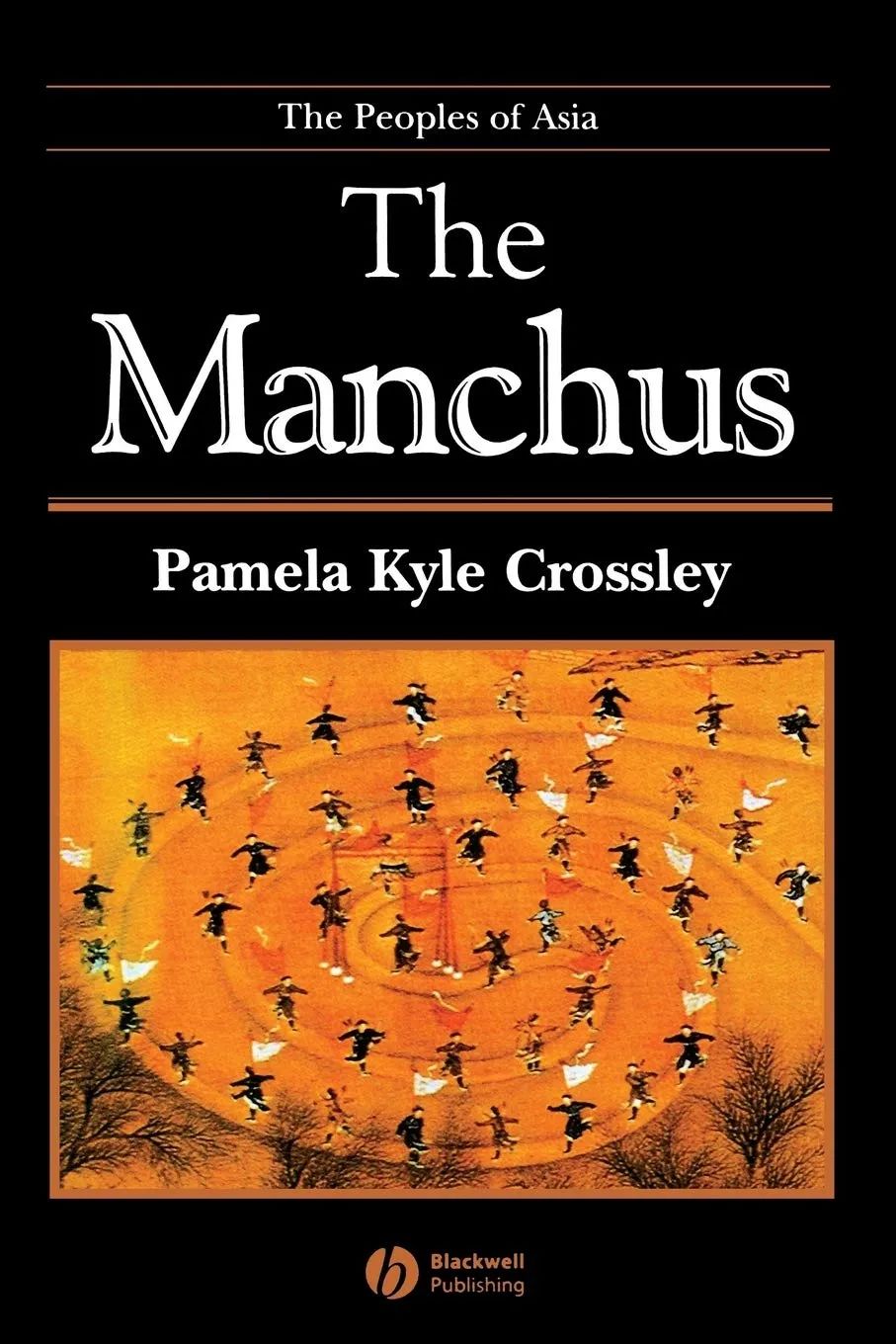
但是,由于美国的中国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现实性和政治性,一些中国国内学者和美国华裔学者,从“新清史”路径中感到某种“冷战”心态,或带有敌意的“帝国主义”对华立场,甚至认为美国学界在苏联解体后,正为“肢解中国”做理论准备。这些观点及双方持久的论辩,的确暴露了中美之间在文化立场上的分歧。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濠江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