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宏斌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1年第1辑

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本公众号分上下两期发布
摘 要:从1876年9月中英两国草签《烟台条约》,将“洋药税厘并征”提上议事日程,到1885年7月《续增专条》签订,中国和英国、印度围绕鸦片贸易展开的外交谈判持续10年之久。清廷为增加财政收入,将厘金和关税一起征收作为谈判的基础;印度政府意在实现鸦片利润最大化,反对中国提高鸦片关税和厘金,主张继续实行鸦片专卖制度;英国政府则坚持鸦片贸易,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转移国内外反对鸦片贸易的视线,并防止中国恢复鸦片输入禁令。外交谈判时断时续,鸦片贸易的巨大经济利益考验着谈判者的智慧和各国的道德底线。
关键词:晚清 鸦片贸易 英国 关税 厘金
一、“洋药税厘并征”问题之提出
二、威妥玛的解释与印度政府撤回反对意见

三、第一轮中英征收洋药税厘谈判(1879年5月至1880年1月)
四、第二轮中英征收洋药税厘谈判(1881年5—11月)
(作者王宏斌,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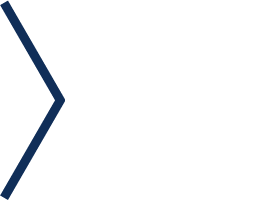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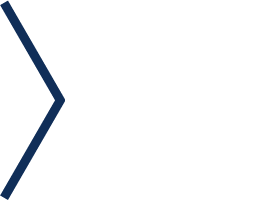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中国历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