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辽东地区是明朝经营东北的核心地带,承担着重要的边防任务。洪武初年,明军北渡进入辽东,旋即进占重镇辽阳城,明朝在辽东的边防建设由此展开。辽东的城镇建设以洪武朝为始,正统朝基本完成。边墙修筑稍晚于城镇,自正统朝开始,成化朝基本完工。明中期以后,城镇与边墙在功用上实现了结合,共同构成了辽东防御体系。在整个体系中,辽阳、广宁二城分别成为统筹辽河东、西防御的核心城镇,也是抵御蒙古、女真各部内犯的重要堡垒。随着边防需求的变化,辽东防御体系先后形成两个核心,在战略上逐渐呈现出重河西而轻河东的倾向,在战术上防御要点由边墙转向城镇。
关键词:辽东;防御体系;双核心;指挥权限
明朝完成对辽东的军事争夺后,城镇和边墙成为辽东军事防御的重要依托。目前学术界对明朝在辽东地区军事防御和辽东城镇已有所研究,[1]但仍然存在视角单一、关联不足等问题,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在嬗变的视角下对辽东防御体系不同阶段的特征加以研究,抛砖引玉,以求证于方家。
辽东地区作为明代的“九边之首”,对明朝北方安全具有决定性意义。[2]洪武四年(1371),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明,明廷随即在刘益势力范围内的得利赢城设置辽东卫。但此时明朝对辽东的控制范围仅限于沿海半岛部分地区。直到洪武五年(1372)明军夺取辽阳城后,[3]明朝在辽东的防御体系构建才逐渐开始,最初防御体系由城镇建设和卫所设置共同构成,边墙建设略晚于二者。
辽东城镇建设和卫所设置互为表里。明初辽东的卫所设置是战争具体进程的直接产物,明军的攻守进退是设置卫所的前提条件,两者息息相关。[4]军事态势直接影响城镇建设的脚步,有了城镇,卫所才有建置之依托。洪武四年,明朝“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治城池,以镇边疆”。[5]可见卫所设置与城镇建设几乎同步。关于辽东卫所设置的具体时间,学界虽有不同见解,但在洪武、永乐两朝已基本完成了对辽东卫所的设置是可以确定的,本文不再详述。洪武八年(1375),明朝在定辽都卫基础上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治所设在辽阳城,辽阳成为辽东军事、政治中心,独立担负军事、行政职责。辽东都司开始成为明朝在东北边疆实施管辖和军事防御的基础与前沿。洪武二十年(1387),纳哈出降明,辽东北部战事基本结束。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朝初步解除了女真对开原地区的威胁,辽东都司辖境范围基本确定,城镇建设开始加快。
城镇在古代军事防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可以为士兵提供军事保障外,城镇本身也是可攻可守的基地和堡垒。明朝建立之前辽东地区原有的一些城镇,经历元末战争后有些已经荒废。这些旧城、遗址被明朝一并继承。辽东地处边疆,环境恶劣,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建造新城难度极大。因此,在辽东卫城及其以上级别的城镇中,除右屯城为永乐朝徐琦、李通二人新修之外,[6]其余诸城皆为洪武朝在原有旧址、土城基础上翻修而成。在《辽东志》《全辽志》等史书中所采用的“仍旧”“因旧”等字样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时,基层堡城的建设也在洪武朝展开。堡城的规模相较于卫城、所城而言明显缩小,屯兵四百余人,[7]具体到明初而言,准确记述的史料也比较匮乏。根据《四镇三关志》的记载,洪武朝辽阳周边修有堡城6座,开原周边修有堡城9座,沈阳周边修有堡城5座,义州周边修有堡城7座。[8]
边墙是明代辽东长城的别称,明代长城依照就地取材的原则,加之明后期的修缮、加固,辽东边墙基本为砖石材料构成。依照明制,辽东边墙由“垣”“堑”“台”“空”四部分构成,除自身墙体外,其内外还配有女墙、障墙、敌台、关口等设施。与城镇不同,明代辽东边墙多为新修。学界一种观点认为:明代边墙修筑的初衷是加强实土卫所与羁縻卫所之间的军事防御。若以此为标准,辽东边墙的有效修筑时间应为正统二年(1437),[9]正统朝基本完成了辽东西部、北部的边墙修筑。
综上,洪武年间,明朝在辽东旧址基础上修筑包括辽阳在内共13座卫城,新修堡城至少27座。这些城镇自山海关向东,经广宁、海州、辽阳三城后,分别转向东北的开原、铁岭和东南的鸭绿江北岸,加上辽南沿海的金、复、盖三城,形成了对辽东全域的合围。虽然辽东都司在永乐朝已于辽河一带始筑边墙,但直到正统朝才初具规模。可见,明初辽东防御体系并不完整,最初仅由城镇体系构成,城镇体系初具雏形后边墙建设才真正开始。
在洪武朝的基础上,宣德至成化朝是辽东城镇体系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辽东城镇的发展呈现两个特点。其一,千户所城和边墙建设加快,防御体系内部联结日益紧密;其二,河西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边防的重心向西部偏移。到了成化朝,随着辽河以东边墙修筑的完成,由城镇和边墙共同构成的辽东边防体系最终形成。其后各朝虽有增减,但未见根本性变化。
(一)四级城镇体系建立
明代的千户所是卫下辖的军事机构,《明史》中称其为“守御千户所”。卫下辖千户所,千户所下辖百户所,这是辽东都司—卫所体系的基本原则。明朝于辽东设置千户所127个,但独立设置屯兵城的千户所只有10个,[10]称之为千户所城。绝大多数千户所的治所在卫城之中,如辽阳城一城即下辖千户所达二十余个。千户所城虽然数量不多,但往往设置在军事防御的要害之处,屯兵千余人,城镇级别位于卫城和堡城之间,数倍于堡城的屯兵数量可以在军情紧急时提供更有力的支援,同时保持了较强的灵活性。在10座千户所城中,除抚顺城建于洪武朝外,永乐朝建城1座,宣德朝建城6座,正统朝建城2座。千户所城的建成意味着辽东自上至下四级城镇体系的正式形成,[11]在这一体系中,镇城、卫城、所城、堡城由上至下,各司其职。与千户所城同时加速建设的还有基层堡城。堡城是为边墙后方的屯兵基地,其驻扎兵力的多少决定了它在军事支援上的辐射范围。堡城的建设反映出辽东边防模式的调整,对此下文将统一论述。
进入明中期以后,辽东城镇体系在业已形成的四级模式下继续发展,受限于史料记载的不足,目前尚且无法对正统朝以后各时期的城镇状况有一个精确的数字统计。关于明代辽东比较权威的两本志书——《辽东志》与《全辽志》均成书于嘉靖朝。《辽东志》最后一次编修的时间是嘉靖十六年(1537),《全辽志》作为《辽东志》的续修,时间为嘉靖四十四年(1565)。两书编修时间相差近三十年,几乎贯穿了嘉靖朝中后期。在史料来源方面,《辽东志》的数据主要取自弘治朝,《全辽志》在此基础上新增了弘治朝至嘉靖朝的史料,两书基本反映了明中期辽东的实况。因此,两书记载的差异可以反映这一时期辽东城镇的变化。笔者根据两书内容,将书中辽东城镇的信息总结如下表:


资料来源:(明)任洛:《辽东志》卷一《地理志》、卷二《建置志》、卷三《兵食志》,第3-7、66-76、109-113、120-145页;(明)李辅:《全辽志》卷一《图考志》、卷二《边防志》《兵政志》,第23-39、44-48、97-126、133-144页。
注:此表中凡《辽东志》和《全辽志》二书中未明确记载的内容,均以“-”标记在表。屯兵数量指的是本城及其下辖堡城中屯兵的人数。
综合上表内容可见,二十余年间辽东镇的卫城、千户所城并无增减,城内屯军数量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在《明实录》中,也未见正统朝以后辽东卫城、所城数量变化的记载。这足以说明正统朝以后辽东规模较大的城镇在分布和数量上已经固定。与此同时,辽东镇堡城数量的变化非常明显,如上文所说,这是辽东防御战略变化的表现,但并未触及整个城镇体系的根本。
(二)边墙建设加速
正如上文所说,辽东边墙虽始建于永乐朝,但仅“择一屯多有水草处,深作壕堑,开井积冰”而已。正统初期,简易边墙才开始向立体化防御体系转变。正统七年(1442),北部边墙初具规模,“起山海关抵开原,缮墙垣,深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使烽燧相接”。[21]直到成化朝之前,辽东边墙修筑的重点都围绕着山海关—广宁—辽阳—开原一线,即面向北部和西北部蒙古的防御。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当时女真对辽东东部和东南部的威胁并不大,且在明朝的控制能力之内。
成化初期,辽东东部和东南部的防御设施建设主要表现为兴建边堡和疏通河道。[22]随着一些女真部族势力的壮大,对辽东东部的威胁日益增加。成化三年(1467)九月,明朝联合李氏朝鲜,对女真李满住部发动进攻,擒杀李满住,建州女真元气大伤。以此为契机,东部边墙开始建设。成化十五年(1479),户部开始筹备修筑鸭绿江至开原边墙所需的粮食。[23]成化十七年(1481),河东边墙修筑基本完成,全长一千余里。建设完成后的边墙以开原卫镇北关为连接点,可划分为东西两段,西段西起山海关,东至镇北关。东段始修于成化五年(1469),自镇北关转向东南,至鸭绿江止。[24]此后明代还有两次对辽东边墙大规模的修筑,分别是万历朝移建宽甸六堡后对东南段边墙的东扩,以及万历三十七年(1609)时任辽东巡抚的熊廷弼在原有辽东边墙基础上进行了修整。[25]
(三)河西地位上升
辽东城镇快速发展的同时,以广宁城为核心的辽西走廊的战略位置也愈发重要。永乐初期,明成祖朱棣撤销了大宁都司,自此辽东失去北部屏障。正统朝,蒙古兀良哈三卫南下,直接威胁辽西走廊。为了抵御三卫的军事威胁,护卫京师侧翼,明朝着重加强了河西[26]一线军事防御。为了加强河西的军事统筹能力,永乐十二年(1414),明朝设置辽东总兵一职,总镇府设于河西重镇广宁城。[27]宣德十年(1435),明朝设置辽东巡抚,其治所“旧驻辽阳,后地日蹙,移驻广宁”。[28]总兵、巡抚先后驻于广宁,加之辽西一带城镇建设的加快,大大提升了河西在辽东镇的军事、政治地位。
随着河西地位的上升,其边防城镇也优先获得发展。对比史料记载可知,嘉靖朝河西共筑有卫城6座,而河东卫城的数量是4座(含辽阳城)。在千户所城的数量上,河西为7座,河东为4座。除了城镇数量差别外,对城镇修筑工作的投入差别也很大。除洪武朝外,广宁城在永乐、弘治、正德、嘉靖几朝均有扩建式修筑。而辽阳城自洪武朝“附筑土城”后,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才在史料中得见“大修辽阳城”的记载。这次大修在派驻辽东的熊廷弼的主持下进行,是时,已经距离建州女真起兵反明三年有余。基层堡城的修筑同样如此,正统朝,河西的前屯、锦州、义州、广宁等城周围新修堡城数十座,同一时期河东仅在辽阳西北一带增修了部分堡城。由于政治、军事上的倾斜,两地在城防、屯兵等方面的差距很大,对此,隆庆元年(1567)辽东巡按御史李叔和的表述一针见血:“总兵官为本镇保障,当审缓急策应。今乃坐镇河西,而以河东付之副将。虽云画地分守,然所部士马亦不足与广宁、宁前、锦义、镇武诸路相等。”[29]
基于以上记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正统朝辽东城镇体系形成后,镇城、卫城作为该体系的骨干长期稳定不变,千户所城的出现使城镇体系结构上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不断增加的堡城使得城镇体系中基层防御的划分愈加细致,各卫所防区基本固定,城、堡多建于防御要冲之地。最终,城镇体系与军事指挥系统相结合,形成了“方今沿边之守有营、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按伏、有备御以分其任;有将领以总其权,有游击以备调发,有总领以司机权,防守之道备矣”[30]的防御格局。成化朝辽河以东边墙完工后,千余里边墙与沿边城镇得以结合,辽东防御体系宣告形成。与此同时,受蒙古南下威胁的影响,河西战略地位日益上升,影响着整个防御体系的内部格局。
辽东防御体系可以划分为西、北、东三个主要的防御单元。[31]西部自山海关至广宁,长期抵御蒙古各部。北部自辽阳至铁岭一线,防御对象为女真各部,东部即传统意义的“东八站”地区,长期人烟稀少,防御相对薄弱,除边墙外仅有嘉靖四十四年徙治所于凤凰城的定辽右卫一个千户所和数十座堡城守卫。从明初收复辽东到中期巩固边防,外部军事压力始终左右着辽东防御的重心。
(一)辽河两岸“双核心”
随着辽东防御对象的变化,在辽河东、西两岸先后形成了两个防御核心——辽阳和广宁。辽阳从明初的抵御纳哈出、统辖全辽到中后期与朝鲜、女真相接,是明朝经营和维护东北边疆稳定的前沿基地。广宁临近京师,统筹河西防御,正统以来成为抵御蒙古、拱卫京师东北部的第一道屏障。加之辽东镇核心机构分驻二城,使整个防御体系围绕这两座城镇展开。
镇城辽阳城城内设有6个卫和1个自在州。洪武四年,明朝设置“辽东都卫指挥使司”,[32]洪武八年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即辽东都司,治所设于辽阳城,有明一代未有更改。除了辽东都司外,先后于辽阳城内入驻的机构还有:布政分司、太仆苑马寺、副总兵府都指挥使司等。永乐朝,辽东卫所设置的步伐加快,辽东都司权力空前扩大。与内地“州县加卫所”的管理模式不同,辽东并无直接管理民事的州县,也“不设布、按二司”,[33]对民事的管理捆绑于各个军事卫所。在此模式下,各级官员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34]军事、屯田、粮储、治安、司法、教育、民族事务都掌握在都司手中。同时,辽阳、广宁、右屯、锦州、义州、宁远、前屯、开原、铁岭、沈阳、海州、盖州、复州、金州等14城均设有察院,作为巡按御史行台。[35]简言之,辽东都司作为军事部门,同时具备独立的行政管理职能,涵盖民、政、军三大领域,辽阳城也获得快速发展,总兵设置后,依照明制,辽东副总兵常驻于辽阳。宣德朝设置辽东巡抚后,治所首先设于辽阳,后移驻广宁,在辽阳保留行台。辽阳城城镇规模在辽东首屈一指,据《辽东志》记载,辽阳共有9个城门,17个进士坊,36个举人坊。[36]作为最大的屯兵城,辽阳城屯兵6卫,兵员三万三千余名。所负责的军事防线西起东昌堡城,北至开原镇北关,东至鸭绿江西岸老边墙(万历三年后改至长甸堡)。[37]万历年间,明朝对辽阳城加以大修。万历二年(1574),朝鲜使臣赵宪出使明朝途经辽阳城时称赞:“辽城甚大,人居甚密,北望旷野,一目千里。”[38]城内设置亦如史书所载“人物富庶,室屋连接”, [39]“邑居极盛,人物骈闻,实东边一大镇也”。[40]
河西第一重镇广宁城,即辽东镇广宁分司城,是辽东镇最大的卫城。[41]城内包括广宁卫在内共有4个卫所。广宁卫“本唐显德府,金为广宁府,元改府为路”,明初“废而为卫”。[42]辽东都司独揽权力,在明初复杂形势下有利于维护辽东的稳定与发展。但客观上却为滥用职权、中饱私囊等行径创造了条件。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有效管理,[43]建文四年(1402)八月朱棣任命左都督刘贞“镇守辽东,其都司属卫军马听其节制”,[44]但刘贞只有总兵之实而无总兵之名。永乐十二年(1414),曾经参与对蒙古北征的将领刘荣被正式任命为总兵官,辽东总兵作为正式官职确立下来。[45]学界对辽东总兵设置的时间有3种观点。[46]无论如何,依照明朝规制,辽东总兵拥有包括钱粮、词讼等民事权利在内的自主行动之权。这意味着包括军事指挥权在内一些原属辽东都司的权力逐渐向总兵转移,而总兵驻地为广宁城,这直接提高了广宁城在政治上的地位。正统元年(1436),明朝始设“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一员”,[47]宣德十年正式设立辽东巡抚,将原属辽东都司和辽东总兵的权力悉数归于治下。巡抚“旧驻辽阳,后地日蹙,移驻广宁,驻山海关,后又驻宁远”。[48]通过《明史》这条记载可知,辽东巡抚设置后不久便从辽阳移驻广宁,辽阳留有行台。这次移驻对广宁城有着极大的意义,辽阳镇城的地位并未改变,但广宁城因拥有更大权力的总兵、巡抚入驻,已经不能以普通的卫城视之。为了整顿辽东军食,成化十二年(1476)以后,明廷开始派遣一名户部侍郎常驻广宁,直接参与对辽东军食的管理。[49]此举更是强化了广宁与辽阳在政治地位上的制衡。广宁城位于辽河以西,地处辽阳西北,“居西北要冲,南滨海,北限太山,医巫闾在卫西五里,虞封十有二山,此为幽州镇山者,粗恶不毛,峭拔摩空,限隔华夷之天险也”,[50]是辽东西北边防的要冲,规模仅次于辽阳城。故元势力被清除后,广宁城的4个卫所主要担负对蒙古“朵颜三卫”的防御任务,[51]驻有兵员二万二千余人,防线七百余里。[52]明初曾重新修筑广宁城,在嘉靖朝进行了续建和部分重建。万历朝时,广宁城已经“肩磨
辽东西、北、东三面所构成的面向蒙古、女真诸部的军事防线纵贯一千余里,除镇城辽阳城外,还有十余座卫城处在这条防线上。辽东城镇之间维持着一种中心与拱卫的关系,作为核心,广宁、辽阳在战略上有着很强的“辐射性”,且二城在屯兵数量、防线范围等军事指标上都远远超过其他城镇,整个辽东防御体系完全围绕二城展开。
(二)防御重心交替转移
“双核心”的防御体系形成于明中期以后,但两个核心并非同时形成,且不同时期各有侧重。洪武朝以辽阳为重点,永乐朝至万历朝逐渐向广宁转移。正如张士尊所说,总兵驻宁远的格局是针对正统时期河西蒙古族部落带来的边疆危机而进行的重心调整。因而,外部威胁的变化是防御重心交替转移的根本因素。
洪武朝明军初入辽东时,辽阳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军事攻防的核心城镇,同时基于降服纳哈出势力的考量,辽东都司驻于辽阳。明朝将辽东经略的支点设立于辽阳,辽阳遂成为当时辽东军事、政治的核心,担负着抵御故元势力、守备辽南门户等诸多职责。纳哈出归降后,辽东东部军事压力骤减。随着奴儿干都司的设立,辽东都司主要任务由作战变为经营。
与此同时,辽东西北部的蒙古势力的逐渐强大,成为辽东防御重心转移的主要原因。广宁卫地处河西,其设置初衷即为防御蒙古:“囊者胡虏近塞,兵卫未立,所以设兵守关,今虏人远遁,塞外清宁,已置大宁都司被及广宁诸卫,足以守边。”[56] “靖难之役”后,大宁都司被撤销,辽西走廊成为抵御蒙古的前线,因缺乏战略纵深,加强该地的防御能力势在必行。除了出于战略上对蒙古的警惕外,蒙古兀良哈三卫的南迁则是防御重心转移的现实因素。洪武朝“置泰宁、福余和朵颜三卫指挥使司于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57]随着明朝北部防线的整体南移,三卫随即南下。自此,蒙古诸部直接与辽东相邻,辽东成为抵御蒙古的最前线,其中又以河西最为突出,“论夷情缓急,则蓟辽为甚,昌镇次之,保镇又次之”。[58]自永乐朝至宣德初期,三卫与明朝的往来从断绝到恢复,一方面保持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依旧频频南下袭扰,明朝对三卫始终保持警惕态度。[59]正统七年(1442)十月初五,“兀良哈达贼纠合野人女真共千余人,自毡帽山入犯广宁前屯等卫界,杀虏男妇一百八十人”。[60]土木之变后,明代北部边防呈现严重的危机,边防全面内缩。[61]辽东面临的军事压力空前增加,“以故朵颜三卫并海西、建州夷人处处蜂起,辽东为之弗靖者数年”。[62]景泰朝之后,蒙古三卫“尽没辽河东西三岔河北故地,蓟、辽多事自此始”。[63]嘉靖末期,蒙古诸部动辄内犯至辽南沿海一线,掳掠甚众。嘉靖四十年(1561),辽东巡按御史李辅提出《条陈辽东八事疏》,在这一上疏中,李辅提出应当加强辽东,特别是河西一带边墙的建设,以强化其军事防御能力。万历朝以后,明廷以“东虏盗边求贡,未见款顺之心”[64]为由,继续拒绝蒙古土蛮部贡市,双方冲突升级,辽阳、沈阳、广宁、海州、盖州等地全线告急。自万历四年至万历二十七年(1599),蒙古大规模内犯达12次之多。[65]蒙古不断内犯,辽西因地理原因受害最甚,而广宁是辽东镇防御蒙古的前线军事要地,[66]为了更加有效地抵御蒙古诸部,明朝在政治和军事上持续加强对辽西的建设,辽东防御重心由辽阳一线转移至以广宁为核心的辽西一线。
在辽西抵御蒙古内犯的同时,辽东东部的女真诸部虽有所发展,但威胁程度远不及蒙古,且万历朝之前明朝对各部女真的控制效果比较理想,即便某一部族势力发展壮大,明朝也能用军事打击予以平定。成化三年(1467),明军联合李氏朝鲜大败建州女真,擒杀其首领李满住,此役令建州女真元气大伤,随后明朝“缘边自抚顺关抵鸭绿江,相其地势,创东州、马根单、清河、碱场、叆阳等五堡,后又设凤凰、镇东、镇夷三堡,广袤千余里,立烽堠,实兵马,辟灌溉,广屯田”,女真的受创加之众多边堡的防御作用,使得“东八站”一带一度出现“虏不敢深入,而百姓乐业”的局面。[67]万历三年(1575),明军再次击败建州女真,擒杀首领王杲,此举再次稳定了东部的边防形势,直到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攻陷铁岭城后,东部边防形势才发生根本性逆转。随着后金的节节胜利,辽东防御体系的重点没有来得及再次转移便迅速崩溃。
(三)防御模式由“面”向“点”转化
辽东边墙修筑完成后,整个边防体系以边墙为基础,形成了区域组合的防御模式。“以形势大略言,则锦义为西路,广宁为中路,辽阳为东路,开原为北路,酌量远近,彼此相援,边疆可拟磐石矣”。[68]辽东边墙始建之初衷亦基于此,正统二年,毕恭任定辽前卫都指挥佥事,上疏“自海州卫至沈阳中卫,宜于其间分作四处,量地远近、筑置堡、墩”,[69]明廷从之。在战略要地还加修双重甚至多道城墙,并于“大边墩台之间空缺之处,因其岸险、随其地势筑为城墙以相连缀”。[70]即将纵贯一千余里的辽东边墙划分成不同区域,各自承担一“面”的防御工作,主要城镇则居于边墙之内,起到屯兵的作用。这一模式理论上更加严密,但对边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何况辽东镇三面临敌,边防线漫长,无法处处重兵设防。加之边墙年久破损、修缮不力,防御能力严重弱化。整个体系最终转化成以城镇为要“点”的防御模式。
相较于横亘千余里的边墙,辽东城镇“以重镇为结点,以都司为框架,以卫所为网络”,[71]当遇边警时,堡城首当其冲,更高级别的所城、卫城可以对边警发生的地点第一时间进行支援。防御模式从守“面”变为守“点”,对于抵御少数民族难以预计的内犯确实更加有效。然而随着辽东周边边防局势的变化,一些城镇的地理位置日益无法满足防御、支援等需求。根据万历二年朝鲜赴明使臣许篈的记述,嘉靖四十五年(1566),蒙古大规模南下,围城沙河驿三日,而“广宁总兵官王治道领兵一万来救不及”,[72]最终“达子
城镇的作用是军事防御,城镇的选址理论上也要服从这个目的,但明代辽东不具备新修大型屯兵城的能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明朝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其一,增建堡城,将原有的防御要点划分为更多的“点”。一方面,堡城规模较小,修筑成本相对较低。增加堡城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卫城数量不足的短板。《明史》记载:“辽阳镇东二百余里旧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铎增置险山五堡,然与辽镇声援不接。”[74]另一方面,有些地区虽然是防御的要点,但自然环境不适合大量屯军,设堡城于该地也是迫于现实的选择。为抵御边患,辽东不断增修堡城,万历初期,在辽东巡抚张学颜和总兵李成梁的主持下,在东南地区移建了宽甸六堡。同一阶段,在明廷兵部的阅视中,可见新筑“城堡一百三十七座,铺城九座,关厢四座,路台、屯堡、门角、台圈、□墩、山城一千九百三十四座”[75]的记载。
其二,在一些地区增设参将、游击等权力较大的武官,或直接提升原驻官员的指挥权限,或是适时调整官员的驻地。嘉靖四十四年,明廷敕命常驻辽阳的辽东副总兵杨腾“有警哨备收敛,相机堵剿,如遇报有大警,开原、海盖二参将,沈阳、高平二游击所管兵马,悉听调度分布截杀。无事各令照常防守城池,如开原、海盖、沈阳、高平、险山等处有警,尔不必听候镇巡明文,径自提兵策应”。[76]同时,明廷因宁远一地距离广宁太远,形势孤危,特敕宁远兵备道:“春夏驻扎宁远,秋冬驻扎前屯。”[77]隆庆元年二月,辽东巡按御史李叔和上疏,以虏于“今一月之间,三犯河东”,请求“总兵宜以隆冬之时移镇辽阳,以援海州、沈阳,冰解回广宁,以防土蛮”,[78]明廷许之,后成为定例。万历八年(1580),明朝以“开原一路策援辽沈,远不济事,欲于铁岭适中添设游击一员,并兵马三千,遇警就近调援”。[79]万历十六年(1588) 五月,明朝奏准辽东总督张国彦请求,“改宁前游击为西路协守副总兵,驻扎前屯,其备御移驻中前所,听协守管辖”。[80]总之,防御模式上以“点”代替“面”,加强了边墙破败后的边防体系,也加强了防御的机动性,但这一转变也将防御压力转嫁至广大堡城。
综上,增修堡城和提升武官指挥权限都是强化辽东防御体系的尝试。随着堡城数量的扩充,这一地区的驻兵总数也随之增加,武官权限的提升让部分堡城事实上发挥了类似卫城的指挥、防御作用。当然,堡城的规模决定了它在驻兵、防御方面毕竟能力有限,无法完全替代更大规模、更高级别屯兵城的作用。所以,辽东城镇体系自身的缺陷无法通过这些手段根本解决。从结果来看,基层堡城承担了巨大的防御压力,损毁严重,辽东边患却未见有效改观。[81]
综上所述,城镇和边墙共同构成了明代辽东防御体系。城镇建设始于洪武朝明军进入辽东后,至正统朝基本形成了镇城—卫城—所城—堡城的四级体系。边墙建设晚于城镇,自正统初期开始到成化朝基本完工。自此以后,二者实现结合,整个边防体系基本形成,共同构成一个以镇城为核、卫城为锁、边墙为链的防御体系。除万历朝移建宽甸六堡外,整个体系再未发生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边墙维护和城镇发展也在同步进行。
辽东在战略位置上同时毗邻蒙古和女真两个具有军事威胁的对手,虽然明朝将蒙古视为最大威胁,但兼顾彼此是辽东边防的基础。明初故元纳哈出的威胁使河东的辽阳成为边防的核心,永乐以后辽东西北部蒙古的威胁迫使辽东防御重心西移至辽西走廊一线。在防御重心交替转移中,辽东防御体系内部形成了两大核心,分守辽河两岸。在此结构下,城镇集屯兵、御敌、指挥等功能于一身,每遇边警,各城既可以独立御敌,也可以彼此支援,其边防作用逐渐超越边墙。嘉靖朝中后期以降,辽东逐渐将防御的支点由边墙转移至城镇,堡城数量迅速增加,整体防御模式最终从防守边墙转变为防守要点。
作者简介:姜维公,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北史;张奚铭,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1] 参见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健才:《明代东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林世慧:《略论明代辽东城镇的兴衰》,《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4期;张丹卉:《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2]张丹卉:《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3]张士尊:《明初辽东二十五卫建置考释》,《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4]李新峰:《明初辽东战争进程与卫所设置拾遗》,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57-69页。
[5]《明太祖实录》卷六七,洪武四年秋七月辛亥朔条,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253-1254页。
[6](明)任洛:《辽东志》卷二《建置志》,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
[7]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第139页。
[8](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校注》卷二,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93-97页。
[9]“臣见辽东边墙,正统二年始立”。参见《明孝宗实录》卷七二,弘治六年二月辛亥条,第1351页。
[10]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第68-69页。
[11]部分学者将辽东城镇划分为五个等级,即在卫城与镇城之间划分出“路城”的概念,标准为规模“上大于卫城,可容兵二卫,约一万一千二百人”,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路城的另一个标准是“参将驻守”。参见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第55页;魏琰琰:《分统举要,纲维秩序——明辽东镇军事聚落分布及防御变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2014年,第103页。对此笔者均不赞同,首先《明史》和《明实录》中并无“路城”的明确说明,若以驻军规模为标准,五城并非全部符合。若以是否有参将驻守为标准,按照《辽东志·官师志》所载,仅有“北路参将”和“西路参将”,按照《全辽志·边防志》记载,除总兵、副总兵外,辽东“参将”数量共有7人,亦不符合。《辽东志·兵食志》中确有“五路”的划分,但为“沿边城堡墩台”的范围划分,而非对城镇的单独称谓。
[12]辽阳城所辖的7个卫,包含“自在州”。参见(明)李辅:《全辽志》卷一《图考志》,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6页。
[13]该数字中包含“游兵官军三千九员”。参见(明)任洛:《辽东志》卷三《兵食志》,第129页。
[14]三个卫所中包含安乐州。
[15]盖州城无军士驻扎,仅“瞭守官军余丁四十员名”。参见(明)李辅:《全辽志》卷二《边防志》,第129页。
[16]该数字包含旅顺城所驻明军。
[17]该数字包含盖州、复州所驻明军。
[18]屯兵数量采用的是本城及其下辖堡城中全部屯兵数量的总和。
[19]险山参将地方下辖堡城13座,分别为洒马吉堡、叆阳堡、新安堡、险山堡、宁东堡、沿江台堡、汤站堡、凤凰城堡、镇东堡、镇夷堡、草河堡、青台峪堡和甜水站堡。险山参将地方的治所为以上13座城堡中的一座,具体位置未见《辽东志》和《全辽志》的记载。
[20]镇武堡游击地方下辖城堡4座,分别为镇武堡、西兴堡、西平堡和西宁堡。镇武堡游击地方的治所为以上4座城堡中的一座,具体位置未见《辽东志》和《全辽志》的记载。
[21]《明史》卷一七七《王翱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700页。
[22](明)李辅:《全辽志》卷四《人物志》,第347-348页。
[23]《明宪宗实录》卷一九一,成化十五年六月甲辰条,第3401页。
[24]东段长城自成化五年开始修建,东南方至鸭绿江北岸险山山下一带。移建宽甸六堡后,该段长城随之新筑,此次修筑于万历四年(1576)动工,最东端达到了今宽甸县永甸乡长甸村东山,自此东南方至长佃河村与鸭绿江相接。参见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第10页。
[25]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第9-10页。
[26]明代将山海关作为辽东最西端、鸭绿江至镇北关作为辽东最东端。辽河在地理上几乎将辽东平分,因此笔者以辽河为界,称山海关至辽河为河西,辽河至鸭绿江为河东。
[27](明)李辅:《全辽志》卷一《图考志》,第30页。
[28]《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第1777页。
[29]《明穆宗实录》卷四,隆庆元年二月丁亥朔条,第102页。
[30](明)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一《镇戍通考·右边墙》,嘉靖刻本。转引自魏琰琰:《分统举要,纲维秩序——明辽东镇军事聚落分布及防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2014年,第103页。
[31]辽南沿海地区主要的威胁来自明初倭寇入侵,自永乐十四年(1416)望海埚大捷后,倭患基本远离辽东海域,沿海防御随之降至次要地位。
[32]《明太祖实录》卷六七,洪武四年秋七月辛亥条,第1253-1254页。
[33]杜洪涛:《明代辽东与山东的关系辨析——兼论地方行政的两种管理体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34]参见张士尊:《明代辽东都司与山东行省关系论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5]参见张士尊:《明代辽东都司与山东行省关系论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6](明)任洛:《辽东志》卷二《建置志》,第90-92页。
[37]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第50页。
[38](朝)权挟:《朝天日记》,[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册,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155页。
[39](朝)许封:《朝天记》,[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册,第91-92页。
[40](朝)赵翊:《皇华日记》,[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9册,第143页。
[41]关于广宁城的等级,有学者提出广宁也是镇城,即认为辽阳、广宁同为辽东镇镇城。参见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第50页;笔者认为,称辽东有两座镇城的说法可能是对《四镇三关志》《经国雄略》中将辽阳镇与广宁镇共称为辽东二镇这一记载的误解。
[42](朝)李民宬:《壬寅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5册,第25页。
[43]为加强对边疆的有效管理,明朝在辽东先后设置了三种治理体系,彼此相互制衡。参见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第112-119页。
[44]《明太宗实录》卷一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壬子条,第175页。
[45]永乐十二年九月,“命都督费瓛、刘江俱充总兵官,瓛镇守甘肃……江镇守辽东,都司属卫军马”。参见《明太宗实录》卷一五五,永乐十二年九月甲午条,第1791页。
[46]关于辽东总兵设置的时间,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一,与辽东都司设立时间相同,参见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佟东:《中国东北史》第3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584-588页;程妮娜:《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其二,以刘荣正式被任命为“总兵官”为辽东总兵设立时间,参见赵现海:《明代九边军镇体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5年,第99页。其三,以刘贞“镇守辽东”为总兵设立时间,参见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47]《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第1777页。
[48]《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第1777页。
[49]《明宪宗实录》卷一六○,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条,第2940页。
[50](朝)李民宬:《壬寅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5册,第25页。
[51]四卫分别为广宁、左卫、右卫、中卫。
[52]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第51页。
[53](朝)李弘胄:《梨川相公使行日记》,[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0册,第47页。
[54](朝)金中清:《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9册,第276页。
[55](朝)李廷龟:《庚申燕行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1册,第458-459页。
[56]《明太祖实录》卷二○八,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己未条,第3098页。
[57]《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六,洪武二十二年五月辛卯条,第2946页。
[58](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关镇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页。
[59]“辽东总兵官武进伯朱荣奏:兀良哈三卫鞋靶欲来卖马。直款谕荣曰:‘虏橘作百出,未可深信,然亦不可固拒,如实卖马,宜依永乐中例于马市内交易,勿容入城,价直须两平勿亏,交易之后即造去,勿令迟留,宜严督各卫所十分用心关防堤备,不可怠忽。’”参见《明仁宗实录》卷七上,洪熙元年二月辛丑条,第230页。
[60]《明英宗实录》卷九七,正统七年冬十月癸丑条,第1955-1956页。
[61]胡凡:《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62]潘喆:《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63](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设立三卫》,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85页。
[64]《明神宗实录》卷六三,万历五年六月丁卯条,第1405页。
[65](明)熊廷弼:《按辽疏稿》,吉林省图书馆据明万历年木刻本影印本,第602页。
[66]肖瑶:《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67](明)贺钦:《医闾先生集》卷四,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68](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校注》卷七,第470页。
[69]《明英宗实录》卷二八,正统二年三月乙卯条,第569页。
[70](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五一,江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转引自中国长城学会:《长城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71]于默颖:《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04年,第15页。
[72](朝)许封:《荷谷朝天记》,[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7册,第39页。
[73](朝)许封:《朝天记》,[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册,第87页。
[74]《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第5855页
[75]《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万历元年七月丙申条,第461-462页。
[76](明)李辅:《全辽志》卷五《艺文志上》,第396页。
[77](明)李辅:《全辽志》卷五《艺文志上》,第396页。
[78]《明穆宗实录》卷四,隆庆元年二月丁亥朔条,第102页。
[79]《明神宗实录》卷八九,万历七年七月甲子条,第1846页。
[80]《明神宗实录》卷一八九,万历十六年五月癸未条,第3727页。
[81]“大抵凌河以北,诸小城曾于丁巳之间尽为达贼所陷,闾里萧倏,人物甚少,或如新破之城,至此则城完,人众庶可倚赖,然而南近于海,或十里,或五里,北接胡地,只有线路,路边虽似掘坑,以拒胡马之来越,而囊土一投便成平地,甚危急处也”。参见(朝)赵宪:《朝天日记》,[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册,第173页。
近期,有部分网站和个人假借《史学集刊》编辑部的名义,通过虚假投稿渠道向投稿者收取所谓“审稿费”,损害了本刊及广大作者的合法权益。《史学集刊》郑重声明:
http://shxz.cbpt.cnki.net是本刊唯一官方投稿平台,本刊从未委托其他任何单位、个人和网站组稿或代收、代转稿件。请广大读者及投稿者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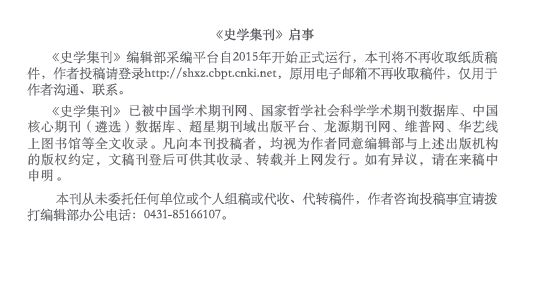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史学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