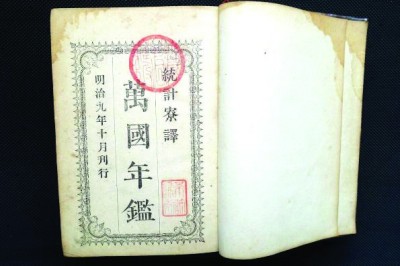《上海年鉴(1852)》,周育民 编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6月
1850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北华捷报》。1851年,北华捷报社刊印了《上海年鉴(1852)》。这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本年鉴,也是已知中国内地的第一本年鉴。《上海年鉴(1852)》内容丰富,极具史料价值,为当时外侨了解上海提供了权威的指南,它的诞生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上海年鉴(1852)》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翻译整理出版,年鉴记载了中国的风土人情、上海开埠初期的重要信息、反映早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初步认识。
《上海年鉴(1852)》为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整理研究”成果之一,中文版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周育民教授翻译。
目 录
序言
《1852年上海年鉴与商务指南》(Shanghai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是《北华捷报》社出版的第一本年鉴,也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本年鉴。
Almanac一词,根据1869年《美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起源于阿拉伯文字,意指“日记”。它不仅有日、月、年,而且标明如日出日落、日食月食等等各种天文现象的时间,但会因各地民情风俗习惯而有不同。这种编纂历书的方法传到拉丁民族,到15世纪时已有刊印。而乔治·立德菲尔得(George E. Littlefield)在《美国考古学会》(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1914年4月号会刊上发表的《论历书与年鉴》(Notes on the Calendar and the Almanac)一文中认为,在中世纪的西欧,历书的编纂权在教会,而年鉴则由民间自由编纂,当时保存最早的年鉴是1646年的,缺了封面和封底,只有8页。简而言之,在英语世界中,Almanac包含Calendar,而内容要比Calendar更加丰富。西方早期的Almanac,要比中国的皇历(黄历、时宪书)的内容要少许多。15世纪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在西方开始流行后,民间刊印历书,并利用历书发行,传播宗教、文化、习俗等知识成为可能,形成了Almanac的编纂形式。至于Almanac(年鉴)最终摆脱历书,成为一种在年度结束之后,将该年度相关资料和信息进行编纂的书籍形式,是在20世纪以后,但即使如此,当代的西方年鉴(Almanac)依然未脱19世纪时刊载大量历史文化等知识的习惯。
西方人在中国编纂的年鉴,是1832年在澳门出版的《英华历书》。以《中国丛报》社(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于1845年初发行的《英华历书》(Anglo-Chinise Calendar for the Year 1845)为例,其基本内容包括:中国干支纪年表、日月食、西方的宗教节日、中国的节气、日历(配有“历史上的今天”,主要是与西方与中国关系中的事件)以及外国在中国五个通商口岸设立的机构、商号和侨民,加上每月两页的空白记事页,共50页左右。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英华历书》基本上沿袭此体例。
但1846年初由《中国邮报》社(Office of the China Mail)发行的《1846年香港年鉴和指南》(HongKong Almanack and Directory for 1846),含有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地的月相表,介绍了香港的地理与气候,其历表中包含有历史事件、宗教节日、日出日落时间、最高最低气温和天气提示等,并附有中英条约、警务规则、机构、商号和外国居民等。因为在历表中含有大量天文气象信息,这是它可以自称Almanac的主要原因,这多少反映了当时英国人对于“年鉴”与“历书”区别的理解。
北华捷报社编纂《上海年鉴》的最初设想,显然是参照了《香港年鉴》。但是,要在上海的历表中增加大量的天文气象信息,既需要客观条件的支持,同时也需要编纂者付出艰巨的努力。从1848年初开始,天主教会在徐家汇、伦敦布道会在英租界分别设立气象观测站,对上海的气温、风向、雨量等进行观测,逐渐积累起了有关上海气候的一些基本数据,这三年的数据为年鉴提供每月天气的提示打下了基础(到1853年的《上海年鉴》中正式编入了历表)。但是,要在历表中提示每天日出日落的时间,标明月相及近地点、远地点等,需要更多的地理和天文资料作为依据,进行复杂的计算,这是编辑人员无法完成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年鉴是采用徐汇家的耶稣会传教士提供的有关苏州的经纬度进行测算的数据,因为上海与苏州纬度仅相差一度,在时间上误差仅几分钟,编辑时并未作调整。农业时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规律,无论在西方早期的年鉴还是在中国黄历编纂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而月相及近地点、远地点对于潮汐的影响,也是人类据以进行水上和夜间活动的重要信息。在科学数据上,《上海年鉴》的历表编制尚未达到《香港年鉴》的水准,但可以说是发挥了当时西方人在上海的科学资源的最大可能性了。
由于耶稣会传教士在历表编纂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上海年鉴》中的历表,充满了浓厚的天主教气息,几乎天主教中所有的节日、纪念日都分别列入了历表当中,这与《香港年鉴》的历表突出世俗性、知识性和地域相关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也多少反映了天主教会编纂历书的传统。
北华捷报社限于编辑力量,第一本年鉴的编纂最初只是参照《香港年鉴》的体例,安排了历表,月相和日、月食,口岸和管理规章,有关机构、商业和侨民,进出口关税以及扬子江航行指南等内容,不愿“平庸”的只是增加了历史年代表的内容。[1] 但实际出版时,其内容大大超出了原定范围,不得不另增“文献”(Misellany)一编,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三,以至其篇幅在当时外人在中国编纂的年鉴中首屈一指。
这个编纂方案的改动,造成了本书编辑体例的混乱。《中华帝国与他国比对编年史》上半部分、《徐光启记略》上半部分和《中国的黄历》三篇,已经编好制版,增设“文献”一编后,上两篇的续文再行编入,使得同一文章不合理的分列两编,《中国的黄历》不列入“文献”,也明显不合情理。增加“文献”一编后,原书的书名依旧,又出现了书名不涵盖内容的问题。这些问题,编辑应该清楚,之所以未能调整,估计是因为年鉴出版的时限和改版的成本均有问题。中文译本为读者便利,改正原版重要编辑失误,将《中华帝国与他国比对编年史》和《徐光启记略》正、续篇合编在一起,连同《中国的黄历》均移到“文献”编中。“文献”编中的文章没有归类编排的问题,不作处理,以略存原貌。
耶稣会士雷孝思用拉丁文撰写的《中华帝国与他国比对编年史》,在这本年鉴中,首次被译为英文发表。在这个编年史中,反映了早期耶稣会士希望根据基督宗教以耶稣诞生作为元年,建立统一的耶稣诞生前的世界编年史体系的努力,其主要目标就是将中国史纳入其中。而这需要重新架构中国历史的年代系统。耶稣会士和后来的传教士架构中国的年代系统方法,是根据“今上”年号年次,与当年西历纪年为基准,然后遂次前推,并且参用干支纪年进行校验,如果不出现阴阳历换算和年号重叠的失误或计算错误,这个方法基本上是可靠的。但在古史中,由于缺乏相应年代的干支信息,公元前的历史编年的误差也就越来越大。这个问题至今依然是中国史中尚未解决的难题,在地球上不同空间发生的历史事件,对接在同一根时间轴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份编年表在问世之后,一度成为基本参照,无论采用或是修改,也在此基础上进行。其另一个解决“中国特色”编年问题的方法是,取消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年号”编年,而以“黄帝”为第一代“皇帝”,依中国正统观念依次排列“皇帝”编号,再按朝代排列“皇帝”编号,即“中国第几代皇帝”、“某朝第几代皇帝”,这种不中不西的编年方式,在早期西方中国史的著作中普遍采用。总而言之,这份年表,其价值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信息,而在于建立世界历史统一的时间坐标的努力。
《论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对欧洲天文学的推介》和《略述中国人的科学——算术》是两篇有关中国科学发展史的重要论文。这两篇论文都是主要根据中文资料撰写的。前者回顾了从利玛窦以来一直到晚近阮元对于这段历史的评论,基本上完整地构勒了耶稣会士推介欧洲天文学成就的概貌。同时,作者艾约瑟揭露了耶稣会士格于罗马教廷的严禁,对于哥白尼、开普勒的天文学成就刻意回避而造成的一些尴尬,对于耶稣会士认为元代郭守敬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得益于经由蒙古传入的阿拉伯文化,也提出了质疑。后者是对中国古代数学成就进行集体调研后的一篇论文。作者肯定了元代以前中国人在算学方面的重要成就,进入明代,算学处于低潮期,没有任何重要著作问世,因而认为,“17世纪耶稣会士的到来,他们新近的、完善的论理在中国科学处于历史上最不利的时期取得了优势。”作者们考察了元代中国人与阿拉伯人在数学上的交流情况,但认为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中国人应该所获不多。作者对于西方的一些作者贬低中国人在算学方面能力的言词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他们列举了中国的数字符号和因归运算方法,不定数的解法(大衍术),以及向数理分析大步迈进的天元术,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早五个世纪就会运用多项式方程运算了。开方术也是由中国人独立发明的。作者甚至与当时在杭州任官的数学家戴煦有过接触,知道他已经找到了求得对数的新方法。作者认为,如果中国人以更大自由地与西方交流,将会促进双方的取长补短,也会激发他们的科学研究精神。这两篇学术论文,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很值得进行研究和评估。
《关于中国内地的通信》和《南京的旅行》是两篇游记和导游性质的文章。上海开埠初期,上海当局与英方有过外国人离开租界往返不得超过24小时的规定,严格地说,是中方规定外国人不准在上海及租界以外地方过夜。但违犯此项约定的情况不时发生。1848年“青浦教案”发生以后,中英关系高度紧张,事态平息之后,此项规定实际上无形搁置。外国侨民远足通商口岸以外的附近地区,虽然化装成中国人的样子,穿长衫马褂,戴个假辫子,但遮不住蓝眼睛、高鼻梁,不过地方官役人等大都眼开眼闭罢了。第一篇是介绍由上海到苏州的路线和景点,第二篇是介绍由苏州到南京的路线和景点,可以说是姊妹篇,留下了沿途许多村庄、城镇、河湖上的人们生活、生产、运输、交易和民情风俗的记录,有些重要的景物如南京的琉璃塔,今天已经荡然,这些文字也是它们在消逝前最后的宝贵记载之一。
《1852年上海年鉴》保留了开埠初期上海历史的许多重要信息。它所提供的《上海口岸1840-1850年气候观测均值一览表》和《气象测量记录摘要》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连续的、系统的气象统计史料。年鉴还提供了开埠以来外国侨民在上海租界的人口统计、机构行号等资料,在这些资料中,外国侨民在上海的职业、身份和地位清晰可辨。年鉴中有关上海港区的水文资料,主要是为便利外国船只进港、出口使用。其中有关上海港区的潮水表,应该是由江海关提供的,只是将时辰改为钟点而已。而《扬子江航行须知》一文,则清晰地提示了外国船只如何由嵊泗列岛进入长江口,然后进入黄浦江所须知的操作要点。它反映了嵊泗列岛作为帆船时代欧美船只前来长江流域国际航运中继站的重要地位。作为江海关理船厅的前身,上海外港区的“河泊司”是个非常奇特的机构。它是由英、法、美三国领事要求上海道台于1851年9月设立的管理外国船只停泊区的专门机构,首任“河泊司”为英国人贝利斯(Nicholas Baylies),从《五口外国居民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河泊司”有个“顺和”的行号,可见是个由外侨承办行政委托管理事务的独立民营机构,外国人在插手中国海关关税征收事务之前,早已插手港口事务了。在“文献”编中,除了有关上海地区的黄历、婚俗、灯会之外,《徐光启记略》是篇上海人物的长篇文章。有关徐光启的生平,国内已有年谱、传记等研究专著,这篇文章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记载了作者亲自考察过的一些遗迹,包括城内徐光启的故居与祠堂、徐光启晚年居住过的“双园”以及徐家汇徐家老宅的情况,并根据采访和地方志书叙述了徐家后代在上海地区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些铭文、碑刻、墓葬,上海地方史书缺载,这些英文史料多少可以弥补一些缺憾。
虽然19世纪50年代之前的上海地方志书中有不少地图刊载,但于上海县城之外,多为河道、分界等示意图,缺乏许多必要的地理标识。外国人绘制的上海地图,目前能看到的是1847年《中国丛报》所刊载的一份示意图,它虽涵盖了从上海县城、英法租界和虹口的一部分,但实在过于简略,很少研究价值。年鉴所刊载的上海地图,是当时西方人汇制的最详细的一份。北至吴淞江虹口到曹家渡一线,南至白莲泾到龙华一线,东至黄浦江陆家嘴,西至徐家汇、法华镇,包括了境内重要的河道、步道、桥梁、寺庙以及其他地理信息,而这一地区除县城和租界以外的地区,之前的地图都没有这样清晰的标识。这些地名均分别用中英文标注,也解决了中国读者阅读早期外人对于上海叙述的许多困惑。虽然,这份地图的文字说明存在许多问题,但地图本身无疑是上海史研究中最具价值的史料之一。
博学多才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医生玛高温向年鉴提供的两篇文章堪称佳作。《乌桕的用途及中国白蜡的笔记》根据中国的文献记载和考察,澄清了早期西方人关于中国白蜡园艺和制作的许多误区。这多少可以提示当今的我们,得留意些人类“照明史”的研究。他的《宁波的海盗、民变和家法》,则是宁波开埠初期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宁波地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前,相关中文史料十分缺乏,在19世纪50年代初,除了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之外,无论当地官员还是宁波士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献和笔记史料,即使后来的地方志有所记载,大多语焉不详,缺漏甚多。因此,玛高温对四五十年代之交宁波当地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记载,其史料价值也就尤为突出了。在他的笔下,广东海盗和葡萄牙人的“绿壳船”互相勾结,坑害海商,骚扰沿海;地方官瞒盰贪渎,疲于应付盗乱、盐变和教变的窘态;以及天主教煽动教民图占舟山寺庙的行径等等,都有十分细致的叙述和揭露,从一个局部展现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的中国社会动荡。他对于天主教传教方针的尖锐批评,对于我们理解后来反洋教运动的频发,也不无启示。与传教活动有关的另一篇文章,是前往琉球传教的德伯令呼吁英美国家直接出面干涉日本禁止基督教传播政策的报告。
《土耳其的鸦片吸食》,叙述了土耳其当时拉克酒的消费量提高、鸦片吸食因年轻一代的时尚变迁而止步的现象。嗜好食品的消费与社会时尚变迁、代际更替等等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一文,展现了澳洲殖民地开发初期,悉尼作为一个国际大港市兴起的早期格局。作者对于悉尼未来格局的展望,为它后来的发展所完全印证,因此,从作者流畅的文笔之下,我们更应该注意他对城市功能、城市结构、城市建筑和城市肌理的深刻思考。
《1852年上海年鉴》,涉及中今中外、天文地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方面。完成这样一部书籍的翻译工作,译者深知难以胜任。勉为其难,只是因为在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翻译成果地位偏低,既不能评奖,也无助于晋升职称,不足以激励才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肯定存在不少错误,不敢祈求原谅,唯抱“必有我师”之心,请求赐正。后任英国驻华公使的包令先生所翻译的《中国格言》,因未提供中文出处,大多未能回译,已回译部分,也无把握,只能留待读者贡献了。
附录的《1853年上海年鉴》是个残本,本无“文献”编。与1852年的比较,除了相关统计数据和规章有所变动之外,增加了各地邮费资率、美国政府方面有关贸易税收管理的文件、上海租地章程和上海口岸租地人表。被称为“上海(租界)宪法”的《上海租地章程》,中译本直接采用了英国外交部档案收藏的中文原件。
本书翻译,为上海市教委高峰高原规划资助项目,并列入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和上海图书馆计划出版项目,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得到了上述单位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在翻译过程遇到一些疑难,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无私帮助,谨此致谢!受托至今,历时三月余,虽可谓耗尽心力,然自知才疏学浅,问题不少。交稿之际,实有诚惶诚恐之感。
顾佳女士在编辑本书出版过程中付出了艰辛努力,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周育民
2019年4月
(本书英文版由北华捷报社编,上海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整理,由笔者译为中文。2019年6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以中英文合璧形式出式,一函两册,定价480元。)
[1] 见《北华捷报》1851年11月7日刊载的有关广告。
如何理解《上海年鉴(1854)》的重要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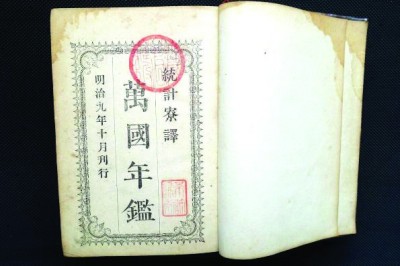
至迟在明治九年(1876)出现的日本《万国年鉴》。
20年前,建国后上海市的第一部综合性年鉴《上海年鉴》创刊,之后逐年出版,与下限为1995年的《上海通志》衔接,构成反映上海地情的资料性文献系列。论及上海城市综合年鉴的编纂历史,则更为悠久。1935年至1937年、1946年至1948年,上海市通志馆、上海市文献委员会曾编纂《上海市年鉴》6种。另外,上海华东通讯社出版有1947年《上海年鉴》。上述年鉴均收录于上海书店出版社《民国上海年鉴汇编》之中。2010年,瑞典藏书家罗闻达先生旧藏“罗氏藏书”入藏上海图书馆,罗先生过世后,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在回忆他的文章(见本刊2013年9月9日《人生不可能有常》)中提到,“罗氏藏书”中有一册1854年的《上海年鉴》,为我们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面貌提供了重要史料。这册《上海年鉴(1854)》是目前可见最早的一册《上海年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在上海图书馆的配合下重印了《上海年鉴(1854)》,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关于这本珍贵的年鉴,本刊邀请周振鹤教授来详细介绍其重要价值。
文汇报:您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简单提到过“罗氏藏书”中一册1854年《上海年鉴》的重要价值。能否为我们展开谈谈这册《上海年鉴》的重要性?
周振鹤:这本1854年《上海年鉴》是North-China Herald(《北华捷报》)出版的第三本《上海年鉴》,是相当珍贵的典籍。由《北华捷报》社出版的《上海年鉴》,据高第书目所载,有1852年到1863年(其中1859与1862两年未见)十种,这是一个系列的书,但今天已不能得其全。其中1852年与1853年相继出版的第一与第二本《上海年鉴》尚未在世界上的公共图书馆里查到。不过,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年鉴处沈思睿所提供的信息,2015年7月Alexander Historical Auctions拍卖图录上却有这两册书,两书内容的分类与1854年版相似,各有200页左右,两书品相从照片看不大理想,但其珍贵性则不待言。另外,高第书目在另一个系列中还列有 The Shanghae Almanack and Directory, for the year 1856.,出版人为 J.H.de Carvalho。
既然这一本《上海年鉴》如此珍稀,故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中国19世纪以前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新闻业,对于近代社会,尤其是开埠城市的变化,起初只能从西方人所创办的报纸中获得材料,后来进一步还可从城市年鉴中去观察。但实际上,直到最近,利用19世纪中期以来的城市年鉴来研究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论著并不多见。其实,看最先出版的城市年鉴——《香港年鉴》,所登载的内容不但可以反映当时香港一地的概貌,还可以看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通商各口的商行、外侨的简况。而对于开埠以后的上海面貌的逐年变化,连续出版的《上海年鉴》无疑是极其有用的史料。
文汇报:查《现代汉语词典》,【年鉴】条目释义为:汇集截至出版年为止(着重最近一年)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计等资料的工具书,一般逐年出版,如世界年鉴、经济年鉴。请问《上海年鉴》是否也是这个意义上的“年鉴”?
周振鹤:近代年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中国,20 世纪以前没有与之相称的连续出版物。《上海年鉴(1854)》的英文名是Shanghae Almanac for 1854,and Miscellany,此书在 19 世纪出版时,如果有人立即将其译成中文,是绝不可能用到“年鉴”一语的,因为中文“年鉴”这个词在中国要到 19、20 世纪之交才出现。
《上海年鉴(1854)》全书分为两部分,后面一部分是“文录”(Miscellany),前面的主体部分是“年鉴”,即Almanac。书名Shanghae的拼法与今天的Shanghai略有差异,前者更近上海的本地发音,出到第六本时就改为Shanghai了,不过据高第书目与2015年某拍卖行的照片看来,1852年的第一本也是用Shanghai的拼法。
《上海年鉴(1854)》一书的“年鉴”是从almanac翻译过来的。那么,almanac又是什么呢?这个词在现代的英汉词典里有“历书”与“年鉴”两个义项,所以此书到底译成“上海历书”还是“上海年鉴”呢?说来就话长一些。其实在西方,almanac本来也是一种每年行世的历书,其中载有气候预测、农民的耕作时序、潮水信息以及与日历顺序相关的表格形态的信息。所以在1822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纂的历史上第一本英汉词典中,almanac一词仅被译为“通书”(即历书),并无今天“年鉴”这个义项。以后百余年相继出版的英汉词典,均只有“历书”这个译法。但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汉辞典,如《英汉四用词典》,在“历书”的同时开始出现“年鉴”的译义,以作为第二个义项。此后一直到最近2015年商务印书馆的《新英汉词典》都是这两个译义先后并存。但也有例外,1989年梁实秋所编《袖珍远东英汉汉英辞典》中,“年鉴”已上升为第一个义项。不过梁实秋的《远东英汉大辞典》第一版对该词的释义仍是历书在前,年鉴在后,可见编者的认识是有变化的。既然英汉词典以年鉴与历书并列为 almanac 一词的译语,尤其已有词典将“年鉴”置于“历书”之前,说明编者已经注意到almanac这个词在西文世界的许多场合其实是当“年鉴”用的,而远不止是“历书”的对译。或许在马礼逊当时,他已知道这个词有年鉴这层意思的,但很可能因为当时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年鉴这种形态的出版物,所以他只能取通书这个义项。当然,在西文里,almanac的原义也的确是历书,但到后来却已发展为兼有年鉴的意义。
在西方,almanac 作为“年鉴”而不是作为“历书”的含义,可举些代表性的例子。比如 Almanach de Gotha,可译作《哥达年鉴》,是1763—1944年间(后来1998年又恢复出版)逐年出版的关于欧洲王室、贵族的资讯,与一般的历书并无关系。在美国一直到今天还有每年一册的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这样的书出版。该系列的书从1886年开始,一直到今年,连续出版 131 个年头了。这当然也是年鉴类的书,其中并无历书常有的那些基本内容。
如果论到历书的起源,在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是可以推至久远的上古年代的。中古时代以后,历书例由皇家颁行。据考证,至迟到晚唐便有印刷的历书出现。而这本 Shanghae Almanac,从内容看,里头有超出历书所包含的许多信息,所以显然译作“年鉴”合适一些。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我们尽可能地在分析 almanac 实际上包含了历书以外的内容,故应译为“年鉴”比较合适,但在实际应用上并没有非常严格的界限。照理说,本书书名既称Shanghae Almanac for 1854,and Miscellany,那么在目录页中应该并列的是 Almanac 与 Miscellany 两部分的细目。但实际上并列的却是 Kalendar(历书、日历,即 calendar)与 Miscellany 两部分。或者因为编者心目中年历是该书的核心部分,也就不在乎这里的 Kalendar 与 Almanac 似乎是等值的关系了。
文汇报:前面您提到中文“年鉴”这个词在中国要到 19、20 世纪之交才出现,能否谈谈中文“年鉴”这个词出现的大致过程?
周振鹤:虽然在《上海年鉴》的这个场合里,我们用“年鉴”来对译 almanac 一词,但在中文里,“年鉴”一语的来源英语词却是 yearbook(或作 year book),而不是 almanac。这是一个有点缠夹的问题。yearbook 这个词出现甚晚,这种出版物起先是由学校刊行的,反映该校每年最重要的事件。后来推广开来,用于登载各种机构(包括国家、城市、各行政单位)依年度变化的统计材料。这种形式的书后来也传播到东方,最先在日本出现,日本人将 yearbook 译为“年鉴”一词,成为一种每年出版的连续出版物,其中以统计数字为主。这类年鉴在 19、20 世纪得到大的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年鉴,包括统计数字以外的其他多项内容。
Year Book 这样的书在中国也早就被注意到,杨勋所著《英字指南》一书成于光绪五年(1879),在该书的第五卷《破体辑要》(“破体”一词,在今天即为简写、略称的意思。)一节中,说明 Yr. Bk.为 Year Book的简写,并将其译作“每年之书”。显见作者已经知道 Year Book 是什么形式的书,但苦于想不出一个新词来对译。但到
了 20 世纪初,该书扩充为《增广英字指南》后,第五卷中的《破体辑要》一节就将其译作“每年之书,年鉴”了。这是目前能看到的英汉词典性质的书里最早的 yearbook 与“年鉴”的对译出处。《增广英字指南》无出版日期,该书第六卷所载书信样板,最晚署“1901.4.6 ”,出书当在此后,故推测是在 1901 年以后出版。
而在实际使用中,现在已知的中文文献的最早出处是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1899.6.18)在日本横滨出版之《清议报》第十八册。该册《外论汇译》中有译自 6 月 1 日《大阪每日报》所载大隈重信在神户华商会馆的演说,其中有云:“观本年所印行《英国政治年鉴》,其变化实多。”此中之《英国政治年鉴》一语显然是译者直接取自《大阪每日报》的原文。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汉学水平较高,大量使用汉字转译当时蜂拥而来的西洋新事物新概念,或用汉语原有之旧词赋以新义(如“封建”一词),或以汉字拼写成新词(如“哲学”一语),不似昭和年代以后对外来语简单地用片假名予以音译。因此,至迟在明治九年(1876),日本就有题名《万国年鉴》的书出现。此书是日本政府机构统计寮对英国人 Frederick Martin 所编The Statesman’s Year-Book一书的翻译。有趣的是,日本所译《万国年鉴》竟然是用汉文而不是日文写的绪言,且未标出所据译的原年鉴与原作者的英文名,而写成“此书英国弗勒德力马丁氏之所著,原题曰士迭门斯伊耳伯克”,一味用汉字音译了。若复原其译音,可知此英文原版书当即 Fredrick Martin 所编著之The Statesman’s Year-Book。英文原版自 1863 年出版第一种后,一直到 2015 年仍在继续出版。日本自编的本国统计年鉴也于明治十五年开始出版,以后每年一回,依次称日本帝国第二、第三统计年鉴云云。“年鉴”一词显见是日本人的首创,到中文文献的直接借用,已经时隔二十来年了。
文汇报:以上您讨论了中文中“年鉴”一词在中文文献中出现的情况。那么中国有近代“年鉴”一类出版物出现是在什么时候?
周振鹤:中国出现与上述年鉴相似的一类出版物,据今所知,则迟自 1909 年始。这一年奉天( 今沈阳) 学务公所图书科科员谢荫昌,受奉天提学司使卢靖之嘱,于当年七月编译出版了《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此书是根据日本统计局局长伊东祐榖明治三十九年所编《世界统计年鉴》一书的“世界之部”辑译而成。“年鉴”一词见于中国书名似始于此。此后至 1911 年,卢靖又先后组织编译出版了《最新世界统计年鉴》《世界教育统计年鉴》和《欧美教育统计年鉴》三种。年鉴类书籍自此在中国流行起来。这些书名里的“年鉴”一词显然也是该书编者直接从日本搬来的。
在中国传世文献中,也可发现《崇文总目》与《宋史·艺文志》等典籍有“年鉴”一卷,此书具体内容不知,但从分类上看,该书属于术数类中的五行类书,与历书阴阳择日一类书相近,而与今天的含义完全无关。据载有《年历》一书的《通志·艺文略》阴阳类目录里,还有《选日阴阳月鉴》这样的书。既有“年鉴”还有“月鉴”,名为“月鉴”之书的全名前面还有“选日阴阳”之字样,足见年鉴是更大范围里(即一年之内)的“选日”之书了。料与古代的“日书”同属一类,先秦至西汉的日书至今出土多种,让我们看到当时人的选日思维,可惜中古世界的“月鉴”、“年鉴”这样的书如今却不见踪影了。
如果真是这样,历史倒有点诡异,西方的 almanac 从历书类扩展演化为今天的年鉴类书,而中国的“年鉴”一词,也从某一本与历书同类之书的专名诡异地变成今天年鉴类书的通称,东西殊途同归之例竟有如此之巧合?不能不令人称奇。至于当年日本学者是直接搬用中国“年鉴”此词来对译 year book,赋予其新义,或是用汉字的“年”与“鉴”拼成一个新词,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文汇报:Year Book一词除了用“年鉴”来对译,还有没有别的义项?
周振鹤:光绪二十八年(1902)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字典》中就有 yearbook 一词了,当时是译为“年报”。民国五年(1916)商务《英华新字汇》此词也译为“年报”,另译“(英法)裁判年报”。Yearbook 一词在《大英百科全书》中一直未单独立项,只是辞典有其释义而已。在最近一版(第十五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在 Legal System 词条下有一个细目 Inns of court and the year books 说明了 year book 与法院裁判的历史关系。所以早期英汉辞典有将 yearbook 译为“(裁判)年报”的,就是这个道理。
直到中华书局 1918 年《英华合解词典》始有“年报”与“年鉴”并列的译法,而“年报”仍在前。可见“年鉴”一词的使用当时还很初期。
文汇报:我们再回到《上海年鉴(1854)》的讨论。这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周振鹤:这要再回到almanac一词的“年鉴”与“历书”两重意思。Almanac既然兼有这两义,就必定与某一文化或某一地域相关连。因为不同文化与不同地方的历书内容是有差异的。历法、气候、农时不一,年中行事也就不一。所以不同的地方应该出版不同的历书(almanac),这是很正常的。在传统中国,历代政府有统一颁布的历书,在清代这样的历书称为时宪历,民间习称通书。各地出版的历书的核心内容,即日历部分都是统一的。但民间的历书除了日历部分,还要登载有关农事的其他信息,还要登载不同时日的各种适宜或不宜的行为,甚至各种生活常识。而就单个城市出版自己特别的历书或年鉴,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似不曾与闻。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种城市历书,或曰年鉴,是香港出版于 1846 年的 The Hongkong Almanack and Directory for 1846。显见这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新型著述,但是此时香港割让给英国已经数年了。
中国内地的第一本城市年鉴应该是开头提到过的上海出版于 1852 年的 Shanghai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 。该书由《北华捷报》社出版,离《北华捷报》的创刊不过一年多。这种城市年鉴应该是五口通商以后才引进到中国。
虽然西方殖民者早就到了广州,而且在1827 年以后也在广州相继创办了Canton Register等英文报纸,却未出版过广州年鉴这样一类书,恐怕原因在于当时广州实行的还是公行制度,不是近代性质的自由贸易形式,也没有正式开埠以后出现的许多洋行(这些洋行与过去旧式的十三行形式不同),更没有常住的外国侨民(开埠前西洋人必须定居于澳门,只是在贸易季节才到广州),所以没有出版供洋人阅读的年鉴的必要。而五口通商之后十来年,中国的外贸中心已从广州转移到上海,西文的广州年鉴也就没有出现的基础了。
与此同时,香港割让给英国以后,大量侨民来到该地,开设商业机构,《香港年鉴》就有出版的需求了。《香港年鉴》连续出版多少年不清楚,看高第(Henri Cordier)《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只有 1846 年与 1849 年两种,其实香港大学还藏有同名年鉴1848 年一种,由该版年鉴序言可知 1847 年也出过一册《香港年鉴》,但原书迄今未见。我们常常感叹古代文献散佚的遗憾,其实近代文献散佚也很严重,必须倍加珍惜。
文汇报:我们可以从《上海年鉴》中获得哪些具体信息?
周振鹤:对比《香港年鉴》与《上海年鉴》,可以看到,两种年鉴大概是一个模式。都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 Calendar(或拼作 Kalendar,历书),另一部分是 Directory(指南),或 Miscellany(文录)。在 Kalendar 部分,核心就是月历(monthly kalendar)及空白的备忘录(memoranda)。再加上气象记录,日月蚀预报,外侨名单、行名录(这部分内容有时也可以放在 Directory,即指南里),斤两钱币换算表之类。“文录”则内容宽泛,有与中国当时经商
环境有关的各种材料,还有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等等(就《上海年鉴》的情况而言,“文录”里的文章多是上一年在《北华捷报》上刊登过的一些文章的汇录)。应该说,出版在后的《上海年鉴》是仿照了《香港年鉴》来编辑的,但内容又有所变化,并且更加充实。
要跟中国人做生意,先就要了解中国人的作息制度,一直到今天,世界各地也都必须知道中国传统的新年——春节是在公历的什么时候,过去更是必须有此信息。西方采用的是阳历,纪年则以传说的耶稣生年为始。而中国所采用的历法是阴阳合历,纪年以皇帝在位元年为始,但西方人也注意到中国有以传说中黄帝为始的纪年。所以在华的西方人编制历书,其基本框架就是中西历的并存对照。《香港年鉴》于这一点尤为详细,将中历月日列在前,西历列在后。《上海年鉴》则以西历为主,每西历月份一页,每日一横行。中历不列月份,只列日,而在日历说明栏中注明中历每月初一是何日为始。
文汇报:所以,近代西方人最早是通过《香港年鉴》来了解中国的历法、气候、作息、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吗?
周振鹤:《香港年鉴》以前还有《英华历书》(Anglo- Chinese Kalendar)。据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说,米怜(William Milne)曾设想过编辑英文—中文—马来文历书,不过未能实现。一直到十多年后,才由马礼逊自己编辑,并由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在澳门出版了头一部《英华历书》:Anglo-Chinese Kalendar and Register,1832:with a Companion。或可简译为 “1832 年英华历书及记录,并附指南”。所以这其实也是一本带有年鉴性质的历书。18、19世纪的西方书名都很长,这本历书也不例外,基督纪元1832年,即中国六十年甲子的第二十九年(即壬辰年),该年始于1832年2月2日。两年多之后,在 1834 年5月份一期的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中已经提到,由于1832 年《英华历书》印数极少,现在已经一本也看不到了。不过只要是印本,总归还有存世的可能,所以我们很幸运,在网络时代,还是能看到该书的电子版。
第一本《英华历书》相对简单,但也有七部分内容:对历书的基本介绍,1832 年年历,公众节日(华人与穆斯林),中国的六十甲子,中国的编年体,中国王朝表,中国本朝皇帝年号列表。该历书的编排方式与《香港年鉴》《上海年鉴》不同,后两者是每月一表,将中西历一起编排。而本书是中西历分页,先是西历一页,接着是华历与回历并列另起一页。而这两种月历均详细记载中西节日内容,远比香港与上海年鉴所记节日详细。两页月历之后则是两页空白备忘页,每半月一页。显然《上海年鉴》继承这一做法,不过将两页备忘录页合为一页(《香港年鉴》则无备忘录页)。《英华历书》恐怕一直连续出到 1855 年之后。据高第书目,1834、1835 年版是在广州印的。今天还能见到的 1845 年与 1847 年版均由《中国丛报》社印刷,然前者印于香港,后者则在广州。这两本年鉴目前由电子版可看到的只是部分的内容。大概是电子版制作者以为其中的月历部分于今没有什么用处,故舍而不录。好在1845 年版的英华历书因为对页扫描的缘故,保存了 12 月份的月历,让我们知道《上海年鉴》的月历编排与之有相似之处,也知道该历书没有备忘录页的存在。由1845年《英华历书》电子版中仅见的12月份月历,可以发现《上海年鉴》月历中的中西历排日方式完全与之相同。或许编纂《上海年鉴》时也参考过《英华历书》?不过两者在12月的记事则有差异,前者所记多是英国等西方国家在华贸易传教受挫记录,后者则记的是天象、纪念日以及中国本身的事件。态度平和了许多,已向相对纯粹的商业活动靠拢。
文汇报:年鉴(历书)的编撰是否主要是为了满足西方人来中国经商的需要?
周振鹤:《上海年鉴》是商业性质的年鉴,或可称作商用年鉴。其实为了传教的需要,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在中国编辑了其他许多形形色色的almanac,不过这些almanac一般译为通书,而不是年鉴。
传教士通书按年代顺序有Anglo-Chinese Concord Almanac(《华英和合通书》),该系列通书的第一种1843年出版于香港,一直出至1865年。实际上,从第二年起即改为《华番和合通书》,1854年以后又改为《和合通书》(Concord Almanac);1861年又更名《唐番和合通书》,一直出至 1865 年。
在《香港年鉴》前后还有在宁波出版的《平安通书》(Peace Almanac),从1850年出到1853年。1851年玛高温(Daniel Macgowan)也在宁波出过一种《博物通书》(Philosophical Almanac)。1852—1861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则在上海出版了 Chinese and Foreign Concord Almanac(首期称《华洋和合通书》,次年起称《中西通书》)。其中 1859—1860 两年由伟烈亚力接办,称 Chinese Western Almanac。1856 年上海还出版过以《平安通书》为模式的《中外通书》(Chinese Foreign Almanac)。这本通书,除日历部分以外,基本上是一份基督教宣传品。1857 年在福州出版有《西洋中华通书》(European Chinese Almanac)。称作 Calendar 的则有 1850 年出版于上海的《安息日期》(Sabbath Calendar),仅一个单页。翌年香港则出版过理雅各(James Legge)编辑的只有九页的《英华通书》(Anglo-Chinese Calendar)。
文汇报:从这些年鉴或年鉴性质的书来看,西方人到中国来,最关心、最感兴趣哪些方面的信息?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又有哪些变化?
周振鹤:气候资料是西方人最注意的地理资料之一,本来这项资料就与人类生存及农工商业活动紧密相关。在古代中国,物候的观察比较发达,而气候的预测则相对后进。西方在 17 世纪上半叶陆续出现现代的观测仪器,18世纪起气象台站网逐步发展形成,开始积累气象资料。因此早在 1793 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之时就对中国的气候情况有所调查。加之中国的夏天全国高温,东南沿海溽热难当,而且灾害性天气较多,汛期明显,西洋人,尤其习惯于地中海型气候者特别难以适应,测量气温雨量气压等气象工作很受重视。1827 年第一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或译《广东记事报》)就登载了西人在广州实测的气象资料。《香港年鉴》头一页就是澳门、广州、香港三地每月的平均气温录。《上海年鉴》也有详细的气象纪录。我们常常以为中国科学的气象观测是1872年从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开始,其实要仔细追溯,恐怕得从广州的观测为起点。对于日月蚀的预报的准确更是显示西方天文学的先进性,所以无论《英华历书》《香港年鉴》与《上海年鉴》都有此项内容。气候之外,港口的潮水起落也是重要观测对象,因为与商船的出入港关系密切,因此各通商港口的潮水涨落纪录也是年鉴的内容之一。
至于外侨与洋行的名录,各国在通商口岸的外交商务机构,自然更是年鉴(历书)所不能缺少的内容。以上这些信息组成了年鉴的主要内容。然后,再附加上如 Commercial Guide, Directory、Miscellany之类内容,就组成一本扩展版的年鉴内容了。《香港年鉴》与《上海年鉴》都是这种类型的年鉴。从附加内容的变迁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城市年鉴的关心范围越来越宽泛。从与商务有关的信息,直到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关心(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时事的报道与分析,对《京报》与地方官员布告的翻译),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以及学习通商口岸方言的兴趣,这种兴趣甚至提升到对方言的科学性研究,即,不但科学地记录中国各地方言的实态,而且比较方言之间以及方言与通用语即官话之间的差异。
文汇报:现在我们要了解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还有哪些外文文献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周振鹤:上海被迫开埠以后,首先是英法两国侨民涌入,随后美国人也跟着到来,再后来,德语国家与其他欧洲国家人员接踵而至。最后日本人在19、20世纪之际也夤缘挤入。因此为着外侨,尤其是英美及法国人来沪经商、传教以及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服务的需要,出版了许多西文报纸杂志书籍,租界当局与西人管理的海关形成大量西文档案、会议记录与年刊。另有数量不少的日文文献。所有这些海量外文文献都应该得到重视,现在许多学者也正在开发利用,但距全面的利用还有相当的距离。比如这本《上海年鉴(1954)》过去就为学界所不知。穷尽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前提,所谓“动手动脚找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希望以此年鉴的重印为契机,将有关的历史资料的开发以及上海城市近代化过程的研究再往纵深推进一步。最近罗氏藏书第二批已经入藏上海图书馆,我们也期待会对上海关系史料有新的发现。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