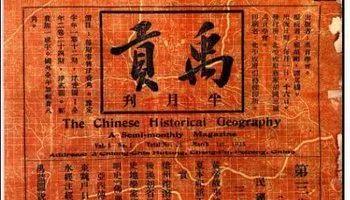作者简介:
采访者、整理者:成一农,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受访者:马修·H.埃德尼,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
翻译者:包甦,自由撰稿人。
摘要
为了促进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以及促进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国际化,成一农研究员与《地图学史》项目的负责人马修·H.埃德尼教授进行了一次对话。首先,埃德尼教授对《地图学史》前3册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评价,认为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这套丛书通过强调古地图的研究应当注重地图绘制的文化、社会等背景,拓展了地图学史研究的领域。然后,成一农研究员简要介绍了中国地图学史近20年来的发展以及研究方向的转向。作为回应,埃德尼教授认为,中国地图学史需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同时强调,中国学者今后只有通过将地图学史的研究融入人文研究,融入其对人类意义的研究,且关注对更为宏观问题的思考,才能真正走向国际化。
由J.B.哈利(J.B.Harley)和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主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地图学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丛书,是已持续30多年的《地图学史》项目的主要成果,也是迄今为止世界地图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基于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研究员主持的“《地图学史》翻译工程”于2014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地图学史》翻译工程”主要进行这套丛书前3卷的翻译工作。目前,翻译工作已基本完成,中文版即将与读者见面。为进一步了解《地图学史》项目的发展情况和学术价值,探讨未来中国学者在地图学史领域的研究方向以及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合作,借2019年8月下旬云南大学组织召开“地图学史前沿论坛暨‘《地图学史》翻译工程’国际研讨会”之际,笔者采访了《地图学史》的项目负责人马修·H.埃德尼(Matthew H.Edney)教授。
成一农(以下简称“成”):马修·H.埃德尼教授,很高兴您能接受访谈。《地图学史》的第1卷已经出版30年多,最晚的第3卷也已经出版10多年,目前您如何评价《地图学史》前3卷的学术价值?
马修·H.埃德尼(以下简称“马修”):就20世纪50至70年代人们对地图学史的兴趣而言,《地图学史》第1卷至第3卷实际将更多的内容引入到了关于古地图和地图学史的研究中。如同20世纪以前一样,在热衷地图学史的人中,有图书馆的地图保管员,他们需要为馆藏的地图做宣传;有历史学者和地理学者,他们可能对地理探索的历史、获取地球知识的历史、以及地图是如何呈现这样的知识颇感兴趣;另外,还有销售古籍和古地图的古董商、地图收藏者,他们中的一些在地图学史方面具备相当程度的学术素养,可以明确列出针对某一时期某一地区能获得的地图类型。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地图学史》前3卷的出版,至少令西方学者耳目一新。这套丛书的出版,使得历史学者、文学学者、艺术史学者,甚至社会学者和一些政治学家忽然意识到,地图是思考与交流世界知识的重要方式,是针对各种需求和目的建构起来的,因此,需要非常谨慎地对地图加以解读。
《地图学史》首当其冲的学术价值,是将地图学史置于“知识地图”之上来展现世界。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地图学史的领域逐渐扩大。如果你今天去参加国际会议,当然,你还能见到地图保管员,他们仍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成员,但古董收藏家和经销商就不再出现了,他们有了自己的圈子——国际地图收藏协会(IMCoS)。在地图学史的国际会议中,你将会发现有各种历史学背景、地理学背景的参会者。比如,2019年7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会议上,就有拉丁美洲的学者、中国学者以及少数非洲学者参加,所有这些学者都从各种不同视角对世界不同地区感兴趣,且关注于将地图作为认识这些地区以及地区历史的重要媒介。这令我身为一名地图学史研究者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轻松起来。
同时,《地图学史》开辟的领域也是跨代际的。在我开始参加国际会议之初,这一群体都是年长的白人男性,就像我现在的年纪。1997年的时候,出现了4位来自美国大学的女性,她们刚刚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分属艺术史、科学史、宗教史和历史专业。在知识层面她们并无新的创见,只是非常直接地陈述了她们所从事的研究。但她们的出现突然令其他与会者意识到,我们都老了,这才是未来,而未来正迅速降临。
如今这一领域已完全开放,我不能说《地图学史》丛书是唯一的推动因素,毕竟出于其他各种原因,地图一直享有着广泛的关注度。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哲学家借助地图思考图像的本质,试图理解图像是什么?图像如何与世界关联等问题。另外,自1966年起芝加哥举办的内本扎尔(Nebenzahl)系列讲座,有意识地尝试解决以前从未研究过的新问题。比如80年代的一个主题系列——“地图与艺术”,该系列的研究成果在1987年集结出版,题为《艺术与地图学》。又如,1972年的“地图印刷史”系列;以及君主、国王和国家重臣在委托制作地图及使用地图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且如何推动了地图学的发展等等主题。多年以来,这些系列讲座出版的图书,的确带动了对于地图的新思考。因此,《地图学史》丛书只是这一宏大进程的一部分,但却是最为醒目且最大的组成部分,真正拓展了学界的视野,使得地图学史成为一个受到认可的、有其合理性的学术领域。现在,人们已知道地图为何“很酷”,且为什么要对其加以研究了。
成:马修教授,我想向您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情况,您是否有兴趣?
马修:当然了,我对关于地图的话题都很感兴趣。
成:上个世纪,中国地图的研究者也很少,且长期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地图绘制的技术层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相对落后,如果能从传统文化中发掘一些“先进”的测绘技术,那么将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地图被认为同国家安全有关,因此地图研究也是一个受到限制的领域。进入本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历史学的开放,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地图的研究价值。但是,首先要克服的一个顽固的观念是,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地图是写实、客观和科学的。要扭转这样的观念非常困难,因为一些古地图和地图学史的研究者是地理学出身,往往会用现代地图的认知来看待古代地图。近两年,情况有所转变,研究者开始认识到地图与艺术之间,地图与文化之间,地图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要将地图放到其绘制背景和使用背景下去研究和作为史料使用。也即,地图的史料价值,远不止图面内容,更多的在于图面背后。不过,当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建立比较明确的以及得到共识的研究视角。因此,从有这样的意识到真正能落实到研究层面,还存在很多难点,同时也没有太好的研究成果可参考。所以,跟国际这方面的研究进行学术交流应该能促进我们的发展。
马修:是的。《地图学史》除了推动地图学史研究领域的发展外,还意在对相关研究领域起到推动作用。通过刚才你的介绍所了解的你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也曾经遇到过,即同样的地图被反复谈论,而没有人能谈出什么新意,无外乎是对某件作品是否是地图,地图是否好看,是否为是我们所知的著名地图这类问题。因此,J.B.哈利和戴维·伍德沃德打算做的,就是让作者们将所有能找到的信息汇总到一起,讨论就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我们所知的制图类型,哪些是我们不知道的?存在怎样的空白?这样能让学者们向前推进,而不是停留于不断重复相同的内容。因此,从务实的角度,《地图学史》是西方学界获取信息的基本资源,包括特定的地图、测量或相关概念等,同时还可回顾历史解读中存在哪些争论。中世纪的海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存最早的海图是13世纪中期的,而且相较于之后两个世纪的海图而言,是几乎完全成形的。在这之前,人们没有试图去制作海图,没有更早的不太成形的海图留存下来。于是我们会问,这些海图从何而来?谁以及为什么会产生制作海图这样的意识的?他们如何取得数据开始制作这些海图?由于证据的相对缺乏,不同的历史学者提出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如果你翻阅第1卷中托尼·坎贝尔(Tony Campbell)关于中世纪波特兰海图的章节,在前20页可以看到,从19世纪中期至今,不同的评述者如何看待这些海图是从何而来的,哪些学派制作了这些海图,并且由于许多海图都是匿名的,因此你如何判断此图出自意大利,彼图出自西班牙。因此,满篇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争论。就此而言,《地图学史》是非常实用的著作,引导现代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了解重要作品的基本信息和与之相关的文献等。
成:据您所知,《地图学史》前3卷出版以后,地图学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哪些新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马修: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地图学史》只是更为广阔的发展进程的一部分,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确可以说这套丛书以非常特殊的方式产生了影响。最能体现这点的是第1卷。2005年,在温哥华召开了一次关于中世纪和古代地图学的会议,带着戴维·伍德沃德生前的愿望,我向会议介绍了此丛书项目。理查德·塔尔博特(Richard Talbot)是会议组织者之一,他对罗马地图学进行过大量研究。在那个周末,塔尔博特不断跟我说,卷1带动了许多新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新的成果,因而它实际上已经过时了。当J.B.哈利与戴维·伍德沃德在物色讨论罗马地图学的写作人选时,他们找到了一位在罗马疆域、土地测量手册和土地管理方面有所研究的人,请其撰写关于托勒密等内容的章节。这些章节写得是不错的,但在古典学者中却引发了诸多问题。唯一流传下来的罗马地图,是一件12世纪的副本,该副本依8世纪的副本而制,而8世纪的这件又复制的是4世纪的原本,一幅长长的卷轴地图,即《波伊廷格地图》,是一幅行程图。鉴于罗马帝国拥有大量关于行程的书面记载,其中记载了你沿某条路行十里是哪座城,再行多少里是下一座城等等。塔尔博特认为,卷1的出现,让古典学者对罗马人如何理解他们的帝国有了新的认识。但也有人认为,既然《波伊廷格地图》完全是关于行程的,那么罗马人可能只会以行程的方式来理解空间,因此不会通过体现整体概念的作品来展示世界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但我们知道,希腊人有这样的总图,中世纪大型世界地图的绘制者认为他们延续的是罗马传统,只是没有罗马时期的大型世界地图传世,相反,倒是有相关的文本参考。因此,人们开始认识到,他们搜寻的档案中还蕴含有大量关于古代制图活动的证据。一旦有了这样的意识,便能有所发现。而新的发现,使得目前所了解的情况,其复杂度要远远超过迪尔克(Dilke)在撰写卷1时所掌握的。因此,卷1引发的这些争论,促使学者们以新的眼光去看待已掌握的资料,并搜寻更多的有益资料。中世纪制图学领域的研究亦如此。保罗·哈维(Paul Harvey)关于中世纪欧洲地方地图和平面图的章节,促使许多档案学者在更多有趣的地方更卖力地寻找早期的地产图。于是,在一些西班牙档案中发现的12世纪地产图,明显依照的是罗马的地产地图的样式。总之,第1卷催生了大量的工作和兴趣。
卷2第1册,我不认为它激发了人们对阿拉伯作品的兴趣,但无疑激发了对奥斯曼地图绘制的兴趣。我印象中,近期有三四本著作涉及到了奥斯曼制图学的方方面面。基于约瑟夫·E·施瓦茨贝里(Joseph E.Schwartzberg)撰写的章节,对南亚早期地图的兴趣的确也在延续。不过南亚学者中,我只知道其中一人的兴趣是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南亚现代制图学,因此不大清楚他们对早期资料的研究情况。我想,本次会议恰好表明,卷2第2册激发了对中国古代制图学越来越多的兴趣。毫无疑问的是,当前西方学者对中国、韩国、日本制图学的兴趣,比20世纪90年代以前要浓厚得多。所以,已出版的《地图学史》卷册,的确在推动新的研究领域方面颇有贡献。
而随着研究领域的成长,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产生了越来越多关于地图的信息,不仅涉及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古代时期,还包括18世纪、19世纪的。于是,我的团队在编写卷4、卷5和卷6时,需要面对的资料体量急剧增长。我们尽可能在参考书目上加以控制,但十分困难。最近刚刚出版的一本关于18世纪航海与海图的著作,非常适合卷4采用,但卷4已经定稿了,我们不能再做任何补充。这令我十分犯难,因为真的很想再加点内容。
当面临这样的问题时,我不得不考虑,不仅是前3卷,而且后3卷也需要重新思考,因为前3卷是如此成功。正如我将在本次会议开幕致辞中所说,我们最初的想法只是就中国、日本、朝鲜、南亚和东南亚的制图学做简要论述,体量不大。但新的想法不断袭来,令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仅要考虑那些老生常谈的地图,还要考虑文献记录中的其他类型的地图。因此,对待后面的几个世纪,尽管我们也想尽量面面俱到,就像针对前面的那些世纪所作的那样,但实在无能为力。所以,我们不得不将后3卷的结构体系完全颠倒过来。前3卷的结构,尤其是卷2、卷3,是按照区域严密组织的,然后在某区域内对制图学类型进行逐一论述。而从1650年直至2000年,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俄罗斯、法国、美国等国与国之间的地理制图、世界地图绘制、地图集和区域地图的绘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地图看上去都非常相似,虽然使用的是不同的文字,但都遵循着相同的投影法则、着色规律等。军用地形图也几乎全都一样。因而丛书的撰写,不得不从1650年之前的按照国别组织,转变成国际化的形式。于是在后3卷中,先讨论地图类型,然后讨论不同的区域和文化是如何对待这些地图类型的。比如,在第4卷成形时,注入了关于政治边界制图学的长篇内容,对长距离展开的详细制图学加以讨论。这一部分以启蒙时期的边界制图学作为开端,先进行了一番综述,然后分别讨论法国、德国、英国、北美的边界制图。我们希望做到的是,打破欧洲学者、西方学者已非常适应的国别语境,令他们察觉到实际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采用的边界制图方式存在很多的相似,于是人们能看到彼此的联系,从而意识到并非地图本身重要,而是发生的制图学类型具有重要性。所以,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应是,迫切需要将《地图学史》后3卷纳入一个全新的结构。尽管很多人对此并不乐见,但没有人能为我指出一种令其尽善尽美的方式。如果要做到前3卷的程度,那么后3卷的体量就会剧增,20世纪的部分会非常庞大,我们不能这么做,因而只能是重新思考按主题加以组织。
成:您刚才提到第2卷第2册对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影响,实际上这一册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之前已做过翻译,但译著出版之初,整个学界对它的评价并不是很好,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基于科学的那套古地图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地图学史的书写基础。大概在该译本出版的同期,我也在撰写我对中国古地图的认知,我觉得余定国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并不彻底,实际上中国的古地图没有什么现代科学的成分。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是完全“非科学”的,所以我那本书的名字叫做《“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以前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某些古地图有科学的成分,但他们没有去分析这些地图到底是用哪些方法、哪些数据来绘制的。我复原了一些以往被认为带有科学色彩的地图的数据,验证这些地图是用道路数据和8个方向绘制的,证明中国古人根本不在乎地图的准确性。
马修:这种情况在西方也十分类似,因为地理学者和制图师所从事的,是他们认为科学的工作,也始终希望站在科学的角度。我经常得到的批评是,你们这样的研究很好,但并不能帮助我制作更好的地图,他们完全处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中,即便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产生的地图也具有历史性和文化性。
成:接着刚才的问题,您和您的团队有没有对前3卷进行修订或增补的计划?
马修:简单的回答是,没有。理查德·塔尔博特曾经敦促过此事,问到,既然第1卷已经有些过时,那么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推出新版?但我长期以来的时间计划就是需要完成整个6卷。按照计划,最晚完成的第5卷将在2024年出版,也就是5年以后了。还需要1年时间来结清账目和归档。之后,我的生活才能回归常态。确实时间周期太长了。我从未在戴维·伍德沃德生前问过他这个问题。但他曾经提及,他可以筹集经费来出版丛书,或者建立一个中心能发布内容更新,但没有足够的经费能做到二者兼顾。所以,当理查德·塔尔博特敦促此事时,我的答复是我做不了,不过你可以做。我认为《地图学史》项目涉及的学术工作是需要两三代学者才能完成的。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个很好的项目,不知在中国的情况如何,但在西方,没有人对其做重新修订。不过,他们有足够的经费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不断在此基础上拓展相关研究。所以,这样的学术研究是需要资金投入的。如果你们想继续跟进这个项目,比如以新的角度重写中国地图学史,且出版中文版的同时译出英文版,那你们完全可以这么做,我非常欢迎。
我想再补充一件事。耶鲁大学有一位非常优秀的现代地图史学者威廉·比尔·兰金(William Bill Rankin),他绘制并研究地图,拥有一个网站www.radicalcartography.net,并写过一篇关于“国际世界地图”(International Map of the World)的很出色的文章。“国际世界地图”项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欧洲帝国项目,所有拥有海外帝国的欧洲国家(吸纳了美国)聚在一起,以1:100万的比例尺绘制一幅标准的世界地图。项目筹划是在19世纪80年代,1896年时,人们开始认可有必要这么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概在1920年,项目真的进展起来,如今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在继续。于是,兰金写了这篇文章讨论互联网带来的改变,并将“国际世界地图”项目当作他所谓的“僵尸项目”的一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官僚机构的作风,一旦为某件事设立了办公室,有了定期的预算,他们就会一直做下去,即便这件事已不再有意义。直到有人最终出来说,这样做下去毫无意义了,才能终止。“国际世界地图”项目就是这样的不断继续,它在1900年、1920年时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情况发生了改变,政治需求变化了,地图绘制也需要改变,但项目仍照旧维持,因而遭遇到了相应的困境,就像掉下来的僵尸饼干。
在某些方面,《地图学史》项目也基本上接近僵尸项目了。如果我们不对后3卷的方案作调整,它就会成为一个僵尸项目,过去的方式曾经有意义、有生命力,但现在已经行不通。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我只是想把这个项目完成。要知道,到项目完成时我就63岁了,我想在退休前用2年时间写一些我认为在当下有意义的东西。因此,我希望年轻一代的学者告诉我,他们认为哪些有意义,哪些需要去做,我不想自己始终把着这个位子。今天有许多人问我,愿不愿意主编某份刊物,或者给我某个项目等等,我的回答都是,不,我的使命结束了,让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去做。
成:我之前做过一些关于城市的研究,也翻译过相关方面的书籍。就我的理解,可能是因为语言的问题,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的研究实在了解得不太多,不知道您对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是否有一定的认识?就您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感受而言,您作何评价?
马修:我建议你们邀请的那些西方参会者中,有学者在以不同方式研究中国。他们要么是学习了中文或其他语言的西方人,要么是在西方工作的华裔,具备中文的文化知识。他们能比我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他们在学界的出现,带来的一部分影响是,为学生们打开了研究对象和思路。无论就中国地图史还是日本地图史而言,我认为他们的研究做得还不够,尽管日本的研究倒是取得了一些效果。他们研究关注的焦点,是要试着评价造访过这些地方的西方人以西方视角所做的传统叙述。比如,利玛窦来到中国,将他的世界地图献给中国皇帝,教中国人关于现代绘图的知识,令他们从欧洲知识中受益一类。而现在的研究导向是,这样的说法是一派胡言,完全是错误的。当然这中间存在互动,中西方之间有着相互关联,但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不是说要夸大其他中国人或日本人或无论谁的作用,而是要真正理解这种关系是怎样一种存在。是完全不平等?平等?还是处在两者之间?
马里奥·卡姆斯(Mario Cams,现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中文名康言)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协助中国皇帝开展的大地测量,以便在确定地球大小的基础上决定1里的长度。经过对中国文献的研究,他非常清楚地表明,这项工程是由中国皇帝召集发起的,并非耶稣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服皇帝去做的。这出自皇帝的意愿,有中国的理由去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是这位皇帝意识到,要实施这样的测量缺乏一定程度的机构能力,所以才引入外国的耶稣会士来帮助实现这项浩大工程。我知道,康言非常不喜欢人们在讨论这类问题时说,这里面存在的是西方的思考方式,摒弃了东方的方式,或者更具体的说中国方式、日本方式等等。这样一种本质论在西方社会已经不受欢迎了,因为它是错的。例如,上个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会议,康言和一位上海学者一起提交了一篇论文,他们讨论的是大约1670年由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在荷兰出版的一本中国地图集。西方对这本地图集的解释一直是,这位去到海外的耶稣会传教士得到了一些数据,对其进行了更正,投入了许多工作,回来后出版了这一精美的地图集。两位学者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地图集引言部分列出的中国的经纬度和地点,没有一个为卫匡国所用。他列出这些内容的用意,是想说明这是地图集设计的基础,但他并没有用它们,只是基本采用了现有的中国地图,略做改动,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出版。我认为关键的一点是,余定国的章节,包括加里·莱迪亚德(Gari Ledyard)关于朝鲜的以及海野一隆(Kazutaka Unno)关于日本的章节,与丛书其他部分一样,基本体现的是西方社会讲给自己的关于其他民族的故事,且这些民族的制图学是不足的。所以,我以西方的视角来看,现在要针对的是一个完全开放给借助好的证据、好的经验数据进行重新思考、重新解释的领域。什么是中国本土制图学的传统?它们如何与西方关联,或者并无关联?
成:这也是我想重写中国地图学史的原因。另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关于“被科学化”的中国地图,阐述“科学化”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有时人们没有认真思考这样做的意义,甚至没有思考过这样做的优点到底是什么,但因为“科学”被认为是好的,起码在近代中国是如此,所以很多方面都是无意识地“被科学化”的,包括地图。
马修:当第2卷的作者向出版社提交初稿以供审读时,我还是麦迪逊分校的一名学生。当时中国部分的稿件,是一位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留在明尼苏达州的中国学者撰写的,但审读者对稿件并不太满意,因为满篇讨论的都是中国制图学长久以来的科学性,非常空泛,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于是审读者回绝了这份稿子,戴维·伍德沃德他们只好另请高明。他们招募了余定国,并非出于他对地图感兴趣,可能是因为他拥有出色的语言能力。余定国是比较文学领域的教授,他的英文很棒,而且硕士读的是拉丁语和希腊语,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懂中文。我们所做的,是与余定国一起工作,为他提供地图学方面的基础,最终由他呈现相关内容,最终希望能打开了一定的研究视野。所以,你说余定国的文章受到了来自科学主义和你这两方面的批评,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余定国恰好就在这中间,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非科学的,用一句英文俚语来形容,就是“neither fish nor fowl(非驴非马,不伦不类)”。
成:在中国,这种变化大概也只是在最近10年才发生。如果在10年前,中国学者书写的地图学史也基本是这样,完全围绕科学与技术,只是最近10年大家才意识到不应如此。
马修:西方作者书写中国或日本制图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被19世纪的帝国主义观念所包裹。欧洲人有这样一种概念,每一种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是自18世纪起,从野蛮、不开化过渡到文明社会的。所以,每种文化在某个层面上可以互换。因此,地图学通史往往有这样的章节,比如第一章或其前半部分,将无论是古代的(如前巴比伦时期)、本土制图学,还是其他任何非西方地图等各种内容拼凑在一起,好像它们是对应的,而其实不是。
成:是的,中国也是在最近几年大家才意识到这样的进步史观存在问题。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中国学者对于古地图的研究其实非常多,但是,除少数以外,大部分没有在西方学术界发表、出版,甚至不被西方了解。这两年,因为年轻一代的学者外语能力的增长,情况有所改观。那么,就未来增进中外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而言,您有什么建议吗?
马修:这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语言,另一个是学术传统。我们读到的中国学者的东西不多,但我们读到过不少印度学者撰写的论著,因为印度学者会用英文写作,只不过他们的英语不同于北美或英国的英语,所以读起来经常感觉不大对劲,有所欠缺。而且,印度学者的东西似乎也达不到欧美学术研究的标准,如经常不能很好地引用文献,只是重复相同的故事,不加评判,不触碰更大的概念。因此,说到中国的学术研究,我感觉中西方之间存在较大的理解鸿沟。西方社会认为中国大学的情况与印度的有些类似,印度有的大学相当出色且能达到西方标准,但大多数达不到,于是便假设中国的大学大概也是如此情形。年轻的学者需要学习英文,当然也需要有更多的西方学者来学习中文。中国学生在学习英文、法文或德文等的同时,还需要接受相同标准的学术训练,这样,西方学者会认为中国的治学水平同他们一样严谨,研究成果也相当有质量。这不仅关乎写作的语言,也关乎表达的修辞。
另外,我认为从西方学术的角度,还意味着要懂得如何将你的研究融入更大的背景。你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之所以做这样的研究,是因为中国的地图学史是中国历史整体的重要构成。我认为J.B.哈利和戴维·伍德沃德做得很好的一点是,证明了地图不只是事实的陈述,而是社会工具,地图的产生是有原因的,地图是可被解读的文化文献。在这个意义上,将地图学史融入人文研究,融入其对人类的意义的研究,将开启对各种更大问题的思考,从而令不仅是西方学者,还包括其他的中国学者、日本或韩国学者对这样的研究感兴趣,这才是更为重要的。用英文写作,很好,但带入这样的角度用英文写作,将收获更多的交流与互动。(会议期间,马修教授主动找我,提出,通过这次会议,他认为顶尖的中国地图学史研究者的水平已经完全可以与西方这一领域优秀研究者并驾齐驱。由于这是他主动提出的认知,因此不能被看成是纯粹的恭维。)
成:我非常同意您刚刚说的这一点,我想中国的学者也开始意识到了,地图要放在相应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与这些背景形成互动。比如古代的中国人如何利用世界地图去了解世界,以及如何去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结构、秩序的理解。
马修:我知道在艺术史领域,东西方学者有着很好的互动,因为西方对中国艺术,包括雕塑、瓷器等有着由来已久的兴趣。我见过一些有中文名字的艺术史学者,他们研究的山水画就与地图绘制有一定的联系。就我的经验来看,地图学史领域这样的交流还不多,但在其他领域有着更多的交流,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地图学史研究还有待于更好地融入国际或全球环境。
成:是的,因为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真正兴起的时间非常短,大概也就是这十几年相关研究者才多起来。
马修:我刚才在读你们的会议手册以及你撰写的研究综述,我想你们已经在考虑开辟专门的收藏了。就在我出发来中国的前一天,我和纽约的一位地图、古籍经销商聊了聊,他说他曾参加过一个由纽约古籍、档案收藏者组成的旅行团前来中国。他们去过一间很大的图书馆,按理说该图书馆应该有很好的古籍收藏,但完全未做过编目,甚至图书馆不愿承认他们拥有这些资料。他跟我分析了一堆理由,但我不清楚情况是否果真如此。不过,倘若许多这样的收藏没有编目,就像西方20世纪30年代那样,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这其中会有什么呢?在西方,时至今日仍可在档案中有所发现。这些档案是编过目的,只是出于某种原因,比如在目录交接过程中遗忘了某个文件柜,而当中恰恰有不少精彩的资料。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我的一位同事在研究美国海岸测绘,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某个文件柜或地图抽屉看上去像几十年都没被动过,那么他只要把抽屉抽出来,抽屉后面就可能掉下来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就是因为抽屉太满被挤到后面而被遗忘的。这样的问题令人着迷,因为你不断地进行编目,但仍有东西尚待发现。你们的资料需要更好、更完整的编目,你们也需要能更好地访问这些资料。我很欣赏你正在做的,搭建一个数字图像的全新界面,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在欧美,即便是公众,也可获得这类数据库的访问权限。西方国家的政府档案中,某些类别的档案是比较敏感的,也不开放给研究者。但有些特定的类别,比如英国政府的,会在资料归档时明确哪些资料保密30年,哪些保密50年。所以,每年元旦,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三五十年前的信息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就大多数制图学类别,尤其是古地图而言,从档案的角度,唯一的问题是由于档案索引做得不够好,导致许多资料很难找到,你不得不翻阅大量的资料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当然,欧美的图书馆都是完全开放给公众的,大多数在19世纪便已如此,最后开放的大型图书馆,是上世纪50年代开放的锡曼卡斯(Simancas)西班牙外交档案馆。现在从马德里到锡曼卡斯有高速列车,到达那里非常方便,他们还将所有资料放到了网上,非常棒。
成: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
马修:不客气,谈论地图和《地图学史》项目是我由衷热爱的事情!
(注:为了便于阅读排版,文章中参考文献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地图史学》翻译工程”阶段性成果(14ZDB040)。
信息来源
《思想战线》,2020年第2期。
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欢迎专家学者、相关研究机构给历史地理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平台投稿,传播历史地理学的前沿动态、学术研究成果等等,惠及学林!
投稿邮箱:852565062@qq.com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历史地理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