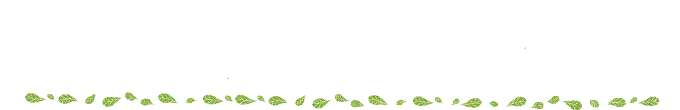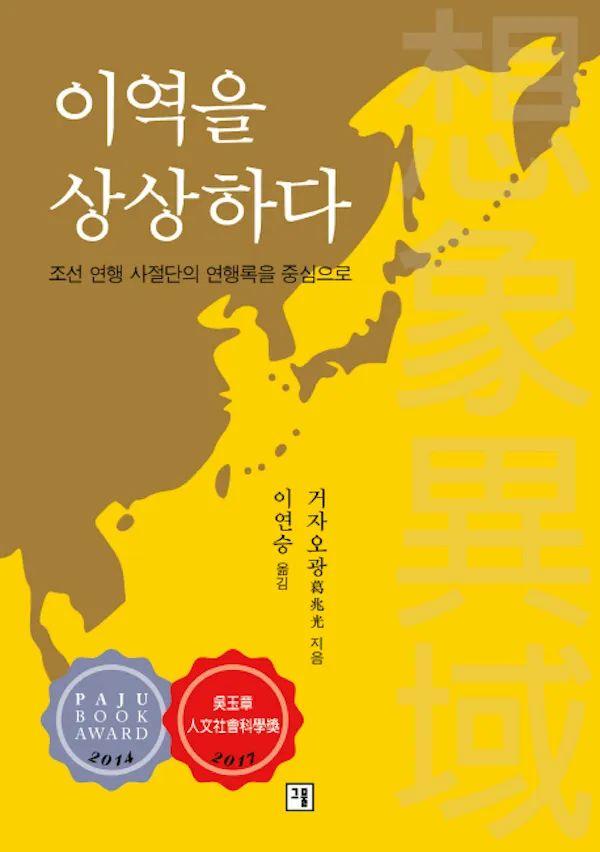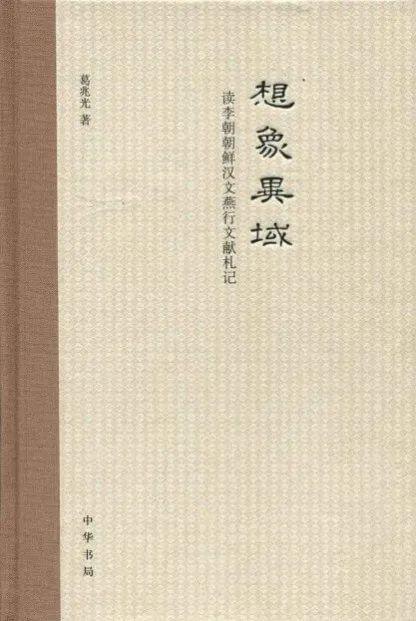来源:文汇学人
点击查看韩国西江大学史学科桂胜范教授的书评:
我们不仅要防止“中国中心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天朝立场”和“天下主义”,也要防止历史事件的分析中,过分夸大华夏文化与中华帝国的核心作用。比如,过去一旦提及儒家、汉字、佛教和律令制度,就总觉得它发源于中国,因此中国就是老师,而其他国家总是学生,难道就不能认为,它本身是东亚各国共同型塑的和共同享有的政治文化吗?
几年前,当首尔国立大学李妍承教授决定要把《想象异域》译成韩文出版的时候,我就表示,如果韩文版问世,我特别期待韩国学界的批评。所以,我在韩文版序言里特意写了一句,“(由于这)是2001年以后我阅读各种朝鲜时代的燕行录之后的成果,所以,更应当在产生燕行录的祖国韩国接受读者的检查”。说实话,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使用朝鲜王朝的史料,讨论朝鲜时代的思想,并在韩国用韩文出版,总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以及“班门弄斧”的感觉。正如我在《想象异域》最后一篇《借邻居的眼睛重新打量东亚与中国》中说的,中国学者中“能够较好通晓日文、韩文的学者还不够,只能阅读汉文燕行文献,而无法参照早期韩文、日文文献,也不能充分吸取现代日、韩研究成果”。这当然是我们的问题,也让我想起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诗可以怨》时,一开头就说的“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的汉学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蛋,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发愣”。现在,只要把这句话的“日语”改成“韩语”,就完全可以挪作我现在的感受。不过,在钱钟书先生是自谦,而我们真的是“穷光蛋”。好在钱钟书先生还补充说了一句,下雨的时候,如果没有“雨伞”,“找不到屋檐下去躲雨的时候,用棒撑着布,也还不失为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我们能用“棒撑着布”来当雨伞的方法之一,就是尽可能多读我们还算熟悉的汉文史料燕行文献,并且用我们更加熟悉的中国文献加以补充。显然,韩国学者对我们这种窘迫多少有点体谅,对我们不熟悉韩国研究论著和不能使用韩文文献也抱有宽容。这次我看到桂胜范教授这篇非常客气的书评,我就特别感受到这一点。读完这篇评论,我很感谢他的理解,也非常赞同他的一些说法。《想象异域》韩文版,书名为《想象异域:以朝鲜燕行使节团的燕行录为中心 》
首先,我非常赞同他对中国(也包括韩国)的一个批评。他指出,“中原的汉族知识人自然很熟悉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世界。既没有自我相对化的机会,甚至也不需要这样的机会,这是因为文明水准的差距原本就很悬殊”。他还点出了两个历史关节点,一个是“主客倒转”的南宋,本来可能改变这种华夷观念,但朱熹(包括宋代理学)却采取了“更加中华”的方案;还有一个是晚清,晚清虽然有“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争论,但是,“中华中心态度依然稳固”。这不仅导致了中国学界“对涉及到中国的巨量外国资料并无多少关心”,更重要的是使中国的历史研究缺乏把“中国相对化”的“外部视角”。并不只是针对中国,桂胜范教授同时也深刻反省了韩国历史研究的缺陷,指出由于殖民地的历史记忆,韩国的民族主义历史表述仍然影响巨大,他说,1980年代以前,“在殖民地经验中派生出来的反外民族主义”历史论述,总是强调“内在的发展要因”与“外部的沮害要因”。我的理解是,所谓“内在的发展要因”指的是历史研究要发掘韩国自身具有走向现代的资源,所谓“外在的沮害要因”指的是强调列强与帝国主义是阻碍韩国走向近代的背景。这让我想到中国历史学界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的某些习惯性否定,以及“没有西方因素,中国也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结论。也许,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心态和观念,可以叫“异曲同工”,也可以叫“心同理同”。我在十几年前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这个研究思路,以及后来撰写的《想象异域》这部著作,实际上就是想把历史中国对象化。“重新确立他者与自我,换句话说,就是从周边各个区域对中国的认识中,重新认知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这是我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07年成立仪式上说过的话。具体说来,它包含了三重意思,第一,重新理解中国,不仅仅依赖“西方”这个背景和尺度,而是同时要参考周边(包括日本、韩国、蒙古、缅甸、越南、印度、俄罗斯等等)的角度和立场;第二,因此要广泛发掘和使用周边各国对于“中国”的史料,不仅要发掘和使用过去曾经同为“汉字圈”的日、韩、越文献,还应当发掘和使用蒙、藏、回、缅、泰等非汉文史料;不仅要参考直接论及中国的文献,甚至还要参考表面上没有涉及中国,却有着中国因素的文献(比如日朝之间的通信使文献)。我曾经反复引述1938年胡适在瑞士苏黎世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历史学大会所作的报告,在这篇题为《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的英文论文中,他已经把“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当做一大发现。可是,我们现在做得还远远不够;第三,更重要的是,在使用这些文献观察中国的时候,尽可能从中同情地理解他们的中国观,不要因为某些价值观念的差异,把这些叙述看成是误解或偏见,其实,误解也是一种理解,偏见更呈现某种观念。其实第三点最为重要。我曾经说,过去我们对中国的自我认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自我想象”的阶段,总觉得自己是“天下帝国”,周围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蛮夷,那种极端自负的天朝主义由于中央帝国的强盛和朝贡体系的加持,始终支配着对中国自己的认识,这种传统至今犹在;第二是晚清以后由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得中国意识到天朝之外还有列强,他们甚至比我们更强(晚清有如今西方仿佛中国的“三代之治”的说法),于是西方成了中国人自我认识的一面镜子,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无论是中外比较还是东西比较,甚至历史学中的时代分期与社会阶段,基本上也是拿了一个含糊笼统的“西方”尺度打量中国。因此,我非常希望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除了西方这个尺度之外,还有我们“邻居的眼睛”,通过邻居的眼睛重新打量中国,看看这些历史上的细部差异,如何决定了后来的巨大分歧。因此,无论是日本所谓“华夷变态”的时代观也好,朝鲜所谓“小中华”的文化观也好,越南所谓“抵御北寇”的历史观也好,我们都给予尊重,并且希望从各自不同立场和不同角度,重新审视一个立体的中国。特别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当对桂胜范教授所说的问题有所反省。所以我希望通过“从周边看中国”,也就是观看者的“主客易位”,减少一些从“天朝主义”借尸还魂的“中国中心主义”。顺便说一句,韩国的白永瑞教授认为我只是单向的“从周边看中国”,似乎还是以中国为中心,所以,特意提出“双重周边”的说法。其实,白教授这一看法和我没有矛盾,我从不反对“从周边看韩国”和“从周边看日本”,每个国家的学者在观看历史的时候,都可能有一个立足点,不可能视角是全知全能的,在他在讨论某一国历史的时候,其他国家都是提供他者视角的“周边”。而我之所以强调“从周边看中国”,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当然偶尔也讨论东部亚洲),另一方面我的目的是在反省“中国中心主义”的历史方法。至于我们是否能够做到,当然还需要学界检验并给出评价。现在,桂胜范教授认为《想象异域》的“优越性在于视角的转移与资料的涉猎”,这样的称赞我不敢当,但我觉得,我们的这些意图和努力,显然得到桂胜范教授的认可,可能也和桂胜范教授的想法不谋而合。桂胜范教授的书评里,也提到他的一些不同意见,我觉得这些看法都非常珍贵。不过,我也想作出一些回应和解释。我不知道在中、韩语境中,对“裁决”和“想象”是否有些理解上的歧义。在中文语境中,“裁决”很像是一个法律词汇,就像法官根据事实作出“有罪”或“无罪”的斩钉截铁的最终判词。如果按照这个词汇的中文意思,那么,就是当年朝鲜的燕行使们,经过到大清帝国的出使经历,才对清朝政治与文化作出了自己的判决。当然,朝鲜燕行使文献中常常有对清朝政治和文化的评论,我在《想象异域》一书中也说到,他们常常使用“胡皇”、“蛮夷”、“腥膻之地”之类的词语评价清朝。不过,我总觉得燕行使们更多并不是像一个法官在冷静和客观地“裁决”,而像是带有情感和温度的“评价”。之所以说,他们不是在“裁决”,不仅仅是他们自己明白朝鲜处于弱势,并不具备抵抗天朝的能力或者裁决天朝的权力,而且他们并不完全要考察事实,然后慎密分析,最终作出判断。他们往往像一个事先抱有“华夷变态”观念的旁观者,进入大清疆域就开始评头论足。由于他们的评价带有选择性,事先埋藏在他们心底的那种怀念大明和鄙夷大清的情感,往往会引导他们的价值判断。我在《想象异域》中说的一些事例,比如关于堂子祭天、关于季文兰故事、关于胡汉衣冠等等,大概都不见得是依据事实作出的“裁决”,而是根据情感作出的“评价”,而这些评价中,并不一定需要太多的“事实”,而是包含了太多的“想象”。当然,正如我在书中说的,“在想象背后,又携带了太多的历史,隐含了太多的情感”。因此,如果说是对清朝的文明“裁决”,那么,朝鲜燕行使的这一“裁决”中也充满了太多的情感色彩,因为有情感色彩,陈述的或目睹的,未必就是事实,而对此的评价和分析,更往往带有“想象”。比如,清朝皇帝正月的祭堂子,现在都知道这是源自萨满祭天遗风,但是目睹这一事情的朝鲜使者,为什么会把它往祭祀邓将军或刘綎身上去联想?而季文兰的故事只要仔细考证,都可以明白这是康熙平定吴三桂时的事情,可是,那么多到过榛子店的朝鲜使者,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象她是明清易代中的悲惨故事?蓟州城外的男女塑像,究竟是安禄山和杨贵妃,还是裴如海、潘巧云?为什么几乎所有看过两个塑像的朝鲜使者,都把它当做安、杨,并且把这种奇怪的祭祀风气和华夷变态联系起来?正如我在书中说到的,“想象和传闻,都受到感情和观念的影响,不免有所偏向和偏见,甚至连事后的回忆,也像在哈哈镜中取像一样,会发生扭曲变形。由于朝鲜两班士人对于大清帝国的蔑视与歧视,使他们的想象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偏向于丑诋和贬斥,而传闻也总是选择着不利于清朝的话头”。其实,我一直强调燕行使文献中存在着不同的因素,即“见闻、记忆和想象”,这一点在第一章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些燕行使文献中,有真切和细致的记录(比如对清朝皇帝形象的记录,就不是中国文献中可以看到的),它们丰富了历史的细节;也有陈陈相因的转述(很多燕行使文献内容是互相沿袭的),这些转述反应了朝鲜士大夫的认知传统;也有是出于对清朝的偏见而来的想象,它们未必是事实却呈现了朝鲜对清朝的文化不认同。换句话说,“见闻”是燕行使的实录,“记忆”来自前人的叙说和文献,而“想象”则是因为层层积累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影响,对异国文明和文化的揣测。就像中国古代“邻人窃斧”故事说的那样,一旦有了“先入之见”,满眼看去都可能疑窦丛生,于是滋生出种种联想和想象。桂胜范教授说的一点儿也不错,朝鲜时代的燕行使们先有了“‘清=夷狄’这样坚固的‘华夷分辨’意识,将自己彻底武装起来,然后再踏上使行路”,所以,也正如桂胜范教授追问的,“清朝的文化与风景真的可以客观地进入他们的视野吗”?如果说,他们并不能客观,那么他们的描述中,很多就只是事先有成见(这个成见没有贬义,大概类似西方哲学所谓“前理解”,即理解和解释之前的“预设”)的想象。我和桂胜范教授都同意,朝鲜使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清即夷狄这样的绝对正答”(桂教授语),然后才进入清帝国,进行观察和记录,而且他们不可能“不做加减地﹑率直地记录下自己的感受”。那么,究竟是怀有偏见的“一厢情愿的想象”,还是先有定论的“当为的裁决”?我把它称之为“想象”,而桂胜范教授觉得应该是“裁决”。
3
最让我有些疑惑的,是桂胜范教授对朝鲜王朝与明王朝的关系的判断。桂胜范教授认为,朝鲜之所以认同明王朝,并不仅仅是万历皇帝在“壬辰之役”中援助朝鲜抗击倭寇,有“再造之恩”,朝鲜与明朝形成的“血盟关系或事大义理”,主要是因为“明朝是汉族在四百年后重新净化中原建立起来的,因此是非常特别的中华帝国(中朝)。明朝不仅仅是单纯的强大国家,更是延续周-汉-唐-宋的儒教中华文明的持担者,即中华文明国兼天子之国”。也就是说,在桂胜范教授所说的中华文明基础的“种族”、“空间”与“文明”三者之中,对朝鲜王朝来说,由于明朝既是汉族,又是中国,还是正统的儒家文明,所以,朝鲜王朝才对于明朝有这样绝对的认同。为此,他举出朝鲜王朝之前的高丽,在认同中原王朝的时候,“皇帝国(天子国)经常变换,与高丽结成宗藩关系的中原帝国一共有后梁﹑后周﹑宋﹑辽﹑金﹑元﹑明七个”。然而,在朝鲜王朝时代,由于以朱子学为国是,华夷观念非常强固,十六世纪之后,朝鲜人已经把所谓忠孝基础上的君臣-父子关系理念化,在壬辰战争爆发之前,明朝与朝鲜就已经超越单纯的君臣关系,发展成父子关系。我不知道其他韩国学者是否认同这种说法,作为中国学者,我却对此有些疑问。虽然从理论上说,这个说法也许解释得通,但是无论是古代、前近代或近代,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其实主要并不是基于义理,而是基于利害,正如现代俗话说的,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尽管朝鲜王朝与中华帝国很长时间曾经共享文化(与日本一样,也有汉字、佛教、儒家和律令制国家等共同点),但是朝鲜王朝从一开始奠基起,它对于身边这个庞大的明帝国,就抱有疑虑和警惕。所谓“事大”,虽然有对中华文明仰慕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现实(诸如安全与贸易)不得不妥协的一面。如果我们看历史文献就可以看到,明朝的天朝霸权以及巨大威胁,才是朝鲜君臣决定“事大”的关键。我要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明初。洪武二十二年(1389)李成桂废掉高丽的昌王改立恭让王,派使者来作解释,朱元璋就故意拒绝接受使臣,说“今臣子逐其父,立其子,请欲来朝,盖为彝伦大坏,君道专无”,只是表示明朝不想干预而已。到了1392年李成桂真的取代高丽建立朝鲜,朱元璋又采取要挟和蹂躏交替的方式,对李成桂建立朝鲜的合法性反复质疑和刁难,对朝鲜派来的使臣百般刁难,还威胁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你要知道大明是你的宗主国,“日头那里起,那里落,天下只是一个日头,慢不得日头”。通过软硬兼施的方法迫使朝鲜就范。而李成桂的内心其实也对明太祖相当不满,他曾经批评朱元璋“疑忌英雄及功臣,指为蓝党、胡党,皆杀之,无乃不可乎”。特别是,由于明朝在史册中以“僭位”或“篡位”记载朝鲜取代高丽,他更是相当怨怼,曾经对臣下表示,朝鲜对明朝只要虚与委蛇,来应付身边这个强大的邻国,他只是从现实角度着眼,不能不采取“事大”的姿态。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永乐时代。永乐元年(1403),朱棣曾经让礼部给朝鲜国王传话,“君臣之间,父子之际,都有一般孝顺识理的孩儿,有五逆不孝不识理的孩儿”,要挟朝鲜国王要懂得孝顺。接下来又仿效元世祖,又是强迫朝鲜太宗世子迎娶明朝皇帝之女,又是要求朝鲜给大明皇帝选秀女。而朝鲜方面呢?也未必那么“孝顺识礼”,李朝太宗看到明朝的《平安南诏》,就对永乐征讨藩属之国安南很不以为然,几年之后,更对手下官员说,“比闻皇帝北征(指征伐蒙古),是乃门庭之寇,事出不得已耳。如向者安南一举,帝之失也。自念吾东方,土嵴民贫,境连上国,诚宜尽心事大,以保一区,如不得免焉,则当积谷练兵,固守封疆”。后面两句很重要,正所谓兔死孤悲,他从安南想到朝鲜,不免对被并吞的命运相当警惕。只是采取的策略是“尽心事大,以保一区”,但如果万不得已,他也暗示朝鲜也会练兵自保。我要举的第三个例子是明代中后期。在各种“朝天录”中,其实,我们也看到朝鲜士大夫对北京有种种不满,不仅朝鲜的朝天使臣到北京受到种种刁难与勒索,明代的天使到朝鲜同样作威作福,敲诈勒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写的《天启五年天使在朝鲜》一文。坦率说,我不太相信受到这样威胁压迫,遭到如此勒索敲诈,眼看天使们作威作福的朝鲜君臣,会从心里对明朝具有君臣兼父子的真诚认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第四个例子,十七世纪也就是明清即将交替之际,朝鲜光海君对明朝和后金采取了摇摆策略。光海君李珲(1575—1641)既与明朝保持“事大”,也与后金保持良好关系,目的是避免朝鲜卷入明、金冲突之中,这种首鼠两端的策略,表明政治考虑和文化认同之间,朝鲜君臣不得不保持平衡。尽管后来“仁祖反正”,重新采取“事大亲明”的策略,但在皇太极出兵朝鲜(1637)之后,他为了保全朝鲜,也不得不采取与现实妥协的方式,这时,尽管曾有对明朝那种“君臣加父子”的联系,尽管有人抨击投降满清“禽兽不如”,但似乎“事大”的情感,还是不得不让位给保全朝鲜的理智。文化史和思想史学者可能注意到邦交中的文化理想主义,政治史和外交史学者则会更多关注政治上的现实策略。其实,桂胜范教授也提到,“单纯仅以事大义理或再造之恩,无法解释朝鲜使臣在燕行录里留下的无数贬低清朝,钦慕明朝记录的理由”。也就是说,朝鲜对明朝“事大”,一半是现实策略,一半才是文化认同。我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是,这种对明朝的文化认同,虽然从一开始也有,但真正深切地作为“事大义理”成了绝对“价值判断”,也要到壬辰之役的“再造之恩”,以及明清易代的“华变为夷”之后,才越来越浓厚地在朝鲜君臣心目中凸显出来,并且导致了朝鲜和清朝之间,“政治承认”(经由册封和朝贡,保持宗主国与附属国的身份)和“文化认同”(对于明代文化的仰慕,以及对清代文化的鄙夷)的分离。从此,朝鲜使臣出使清代北京的记录,就不再是“朝天”而是“燕行”。
4
我赞成桂胜范教授的批评,在讨论朝鲜时代的燕行使文献时,还应当注意那些并不带有“燕行”字样的文献;我也赞成桂胜范教授说的,朝鲜燕行使究竟有多少了解中国,也许对他们来说“中国即北京”,更多的中国他们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必须对燕行录加以严肃的史料批判”;我也非常赞同桂胜范教授对朝鲜燕行使和通信使的记录保持警惕,因为在他看来,“清秩序下的朝鲜是非常教条的﹑理念的国家”。不过,我也特别期待韩国学者能了解,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始终寻求在东亚史或中国史研究中,有一种自我批判的态度。对于历史上中国在东亚政治、文化和经济中的笼罩地位和巨大影响,一定要抱有怀疑、批判和分离的立场。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防止“中国中心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天朝立场”和“天下主义”,也要防止历史事件的分析中,过分夸大华夏文化与中华帝国的核心作用。比如,过去一旦提及儒家、汉字、佛教和律令制度,就总觉得它发源于中国,因此中国就是老师,而其他国家总是学生,难道就不能认为,它本身是东亚各国共同型塑的和共同享有的政治文化吗?又比如,一旦提及文化认同,就总是强调异国对中华帝国的认同和仰慕,这种单向度认同的历史见解,难道与历史上的“华夷有别”之说不是一脉相承吗?再比如,一说起朝贡体制,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难道东部亚洲海洋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中国主导的历史世界吗?正是为了改变这些在中国习以为常的历史观念,我才在《宅兹中国》和《想象异域》等书中提出以下几个想法:首先,如果说自从汉唐以来东亚确实有共享的文化圈,那么,它不仅应当强调是华夏发源的,也应当强调是东亚共同型塑的,因而这个文化圈“同中有异”,而且也应当说明,这个文化圈至少在十七世纪之后已经“渐行渐远”,这时,这个文化圈实际上在逐渐崩坏。其次,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清易代,确实在中国史、东亚史,甚至在世界史上影响很大。尽管我并不认为汉族统治下的明代文明,就比满族统治下的清代文明更高明或更正统,但在日本和朝鲜看来,确实中国已经“华夷变态”。这不仅催生了日本型华夷观念和朝鲜的小中华观念,也引来了朝鲜燕行使文献中,那些对清代中国的各种负面评价,这些负面评价,倒是让我们更深切更真实地看清了某些侧面的清代中国。再次,无论是不在册封-朝贡圈中的日本,还是在两属之间的琉球,抑或是最密切的附属国朝鲜,以及始终对北寇怀有异心的朝贡国安南,这时都逐渐出现了“政治承认”和“文化认同”的分离。也就是说,尽管各国还承认中国是大皇帝和宗主国(日本例外),但是,已经并不认为中国文化仍然正统和高明。东亚所谓“自国中心主义”,就在这样的“政治”与“文化”分离下开始滋生和膨胀,实际上,清代中国并没有真正在政治和文化上控制和调节东亚或朝贡圈的能力。最后,我也想坦率地说,尽管有人已经觉得费正清理论已经过时,但我大体还是赞同,在传统帝国到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中,确实有“(西方)冲击-(东亚)反应”的关键作用。我只是特别强调,被冲击方“各有各的反应”,而之所以有各自不同“反应”,又恰恰与“渐行渐远”,也就是十七世纪以后东亚诸国逐渐形成不同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这个分歧,导致了各国现代转型过程的差异。我不知道我的这些想法,以及作为中国学者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是否能够得到桂胜范教授以及韩国学者们的赞同。
2020年3月13日写于东京大学
“星标”我,
就不容易弄丢我!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韓國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