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区域史是理解历史发展的一把关键钥匙,是一种区别与国家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通过深入考察并比较各个区域进入国家体系的历史过程和机制,对于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区域史绝不是替代国家史,更不是国家史的地方版本,而是在超越国家的视域中将地方作为对象,以人的行为主体为出发点,始终保持对整体史的追求。2021年8月17—18日由江西师范大学组织承办的“第四届闽浙赣区域社会史研究工作坊”,围绕但不限于闽浙赣区域的诸多议题,分享区域史研究的心得、发现、可能与未来。以下四篇文章主要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厦门大学郑振满、中山大学刘志伟、北京大学赵世瑜四位教授在工作坊上的主旨发言整理而成。为尊重作者原意并还原会议的现场感,整理者据录音全文整理,仅对个别字句进行了修改。
统一模式书写背后蕴含不同的历史进程
科大卫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其实参加过很多次闽浙赣工作坊的会议,每次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共同学习,当然有时候可以跑一下田野就更高兴了。但是这两年在香港,因为新冠疫情哪里都不能去,所以田野考察也暂停了,我们以前做了很多年的项目也停顿了一阵子。我就在想这一次来开会,要交一个什么样子的报告呢?我昨天晚上准备了一个简短的ppt,但是担心网络不稳定造成麻烦,我就不演示而直接讲述。
因为这两年也没有跑过田野,我就想向大家做一点我读书的报告。什么读书的报告呢?我们原来有个项目叫作“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它跟闽浙赣也有点关系,最后应该有些最终成果。我就将之前的项目进行了整理,准备弄一本书,归纳出种种不同地方的研究,看是否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全面性的故事。事实上,在一本书中要囊括中国很多地方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每个地方情状各异,如果你不了解实地情况,读文献时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所以这一次我也感觉到太大的野心,不过,还是希望到明年可以把这本书弄出来。但是工作做到一半,我跟贺喜又接到了另一个任务,也跟闽浙赣有关系,我们要写一本书,主要讲秘密会社的秘密。我就负责其中讲到东南亚的那一章,江西、福建、广东的部分都是贺喜负责的。所以这次发言,我想还是讲整理“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这个项目的书,来谈谈区域社会史中两个不同但又有联系的层面。
一是宗族制度。似乎任何事物在发生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制度上的发明,而制度又在不同地方不断演变有不同的后果,所以说要了解一项制度,首先要了解其产生与演变的过程。讲到宗族,主要有三个部分需要处理,分别是祠堂、族谱和尝产(宗族的财产)。祠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乡村里面,为了配合王朝国家的制度,逐渐发展出家庙一类的场所。关于这方面,我出版过一本书叫做《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主要讲“大礼议”前后,在广东地区祠堂的变化。至于族谱的故事,我推荐大家去看贺喜最近出版的新书(Lineage and Community in China, 1100—1500:Genealogical Innovation in Jiangxi, Routledge, 2020)。族谱也有着漫长的历史,我们原来的族谱不是多线的,因此研究时需要分辨单线的和多线的族谱。事实上多线谱出现于宋朝,要从欧阳修的故事开始讲起,而借助多线谱我们又可以了解到宗族的另外一种模式。但是,关于尝产是怎么发展出来的,我们目前还没有解决。我相信宗族需要拿到财产,这里面是有另外一个故事要讲的,我希望在即将要写的书里可以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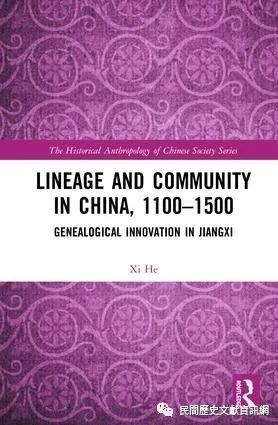
Lineage and Community in China, 1100—1500: Genealogical Innovation in Jiangxi
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有兴趣的就是要讨论国家在地方上是什么样子的,即国家跟地方社会的互动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了解国家和地方上的互动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因为不同地方与国家建立联系的时间以及所依据的机制不尽相同,还应提到文字在两者互动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在了解国家与地方互动时,我们需要对文字多加关注。我们需要辨析在地方和国家互动中,文字是否具有普遍性,又或者说在二者确立联系之后文字的普遍性才体现出来。此外,还要注意文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书籍(抄本、印刷品)以及从《四书》《五经》延续下来的教材,再想象一下《三字经》等蕴含了怎样的儒家价值,国家法令、教育政策里面又有多少是国家的政治意见,这些统统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所以说,文字是帮助我们了解两者互动的一个重要层面。
另外要关注的是神跟祖先的关系,这是我比较费力的地方,因为我基本上不懂宋史,宋以前的历史我就更不清楚了,所以我一直在辛苦的补课。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找出宋朝时每个地方具体的样子,避免将研究对象泛化,搞得整个宋代的中国都是一样的。我们还是要清楚地明白,事实上在宋朝很多地方是不拜祖先的,地方上有各种各样的神,随着时间的发展,拜神与拜祖先才逐渐结合,到某一时段才演变成祖先崇拜,这其中蕴含的问题也需要我们加以注意。
还有一点是在理解国家与地方的互动模式时,尤其是提到族产(尝产)问题,此前刘志伟先生讲过多次,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国家是利用户口登记还是田土登记来控制税收。所以在研究地方与国家互动模式时,文字、宗教和税收是三个关键因素。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我试图找出很多地方原先基本上是拜神而不是拜祖先的,进而揭示出从拜神到拜祖先的转变过程。当然,我并不是说整个中国都是一样的,我历来都是反对研究一个地方时将其视为典型,在经历一个历史过程中,肯定有很多地方采取了不一样的做法。但是,当到了某个时候,不一定是马上,也许是几百年之后,人们在用文字统筹记录时,就将这个过程当成是一样的进行书写。这就导致当我们现在去看后来者编的材料,尤其是族谱时,就感觉大家似乎都经历了同样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每个过程都是不一样的。讲到这里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看文献时,样子很像的文献背后的故事可能很不一样,看不看得出来,这是十分考验历史学者读文献的功夫。
另外要说的是,因为很多东西我还不懂,因此写这本书时异常辛苦。当然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在网上有非常多的族谱,上海图书馆有成千上万种,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有一千三百万张的一页一页的胶片记录。只要你有兴趣、有时间,慢慢去看,你可以找到很多的族谱。但这些族谱是零零散散的,你在图书馆找到的族谱和在乡村里面见到的不一样。我还非常感谢让我去跑过田野的所有朋友,因为有跑过田野的经验,在不能跑田野只能枯坐在家里通过电脑去翻阅族谱的情况下,田野的经验给予我非常大的帮助。因为跑过田野,你就懂得如何去看族谱,就会知道这些搞族谱的人背后在搞什么鬼。这些族谱为何书写,如何使用,谁写,谁读,谁保存,其中保存了什么,扔掉了什么。换句话说,你得明白流入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族谱是经过了有意筛选的“死文字”。
因为这些族谱,所以我可以去研究闽浙赣。我原先是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后来有兴趣关注华北,还有兴趣留意西南,也正是在寻找族谱的过程中,我追到了浙江,尤其是浙江的山区。在新书中我梳理了萧山湘湖盆地的情况,并与浙南山区进行对比。关于这一方面,好几个学者(例如钱杭先生)的研究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但是通过自己翻阅族谱和地方文献,我发现了湘湖地区是如何构建一个先民开发的故事,并将其作为在此地生根的宗族起源的依据,有了这个依据,他们就有入住、开发的权利,就可以把其他人排挤出去。但在山区却显示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我需要将材料翻出来,慢慢整理才搞得清楚,但是限于时间,我无法解释其中详细的差异,只能笼统的叙述一些。
这方面的研究给我启发的,其实是郭锦洲先生的《宋明间徽州社会和祭祀礼仪》一书,这原来是他的博士论文,我很幸运是他的指导老师。他试图解释明朝中叶徽州的祭祀礼仪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建立的,比如徽州的宗族,讲到汪华、方储那几个上面。其中,特别提及方储这类既是祖先又是神的人,有意思的是方腊之乱中方腊叫做方圣公,而方储也叫方圣公,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地方社会原先拜的那个神。郭先生研究的是徽州,假如他多走几步,跑到浙江这边,跑到淳安,也就是方腊出现的地方,淳安姓方的那些村子,就是方腊起义的时候军队跑进去攻打的村子。史料中清晰的记录着,那些村子要怎么样把他原来拜的方圣公改成是他们自己的祖先,并与方腊相区别,说明“那个方腊是个坏蛋,他不是我们村子的人,他都是外面的人,我们都不承认的,我们是跟着姓方的祖先这一支的”。在那一带进行观察,你会开始看到汪华,还有姓叶的宗族(有几个名字一时我说不上来),原来是拜神的,后来因为政治上的理由都改成拜祖先,改成拜祖先就跟产业有了关系,这就回到了刚才说的国家与地方互动这个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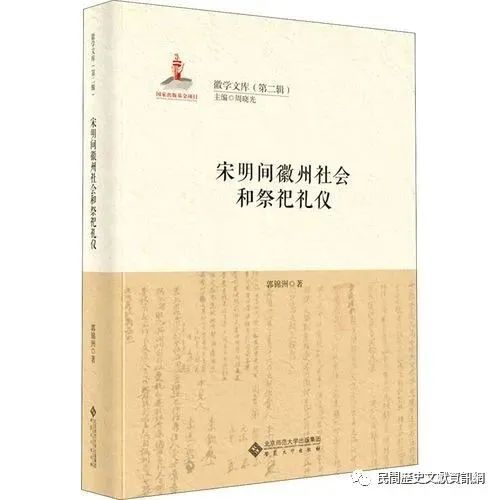
《宋明间徽州社会和祭祀礼仪》
为什么对这个地方非常有兴趣,因为这些涉及刚才说的,一部分是神跟祖先的关系,一部分是朝廷纳税登记人口还是登记土地的关系。在梳理的过程中,我要感谢许多研究宋史的学者,其中包伟民先生写的几篇文章对我了解这块区域非常重要。研究宋史的学者大多喜欢说,明清时期的制度在宋朝时就已有了雏形,但是他们较少进一步研究这些制度在宋朝哪里起的实际作用。例如南宋时期国家进行的土地登记,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实施过呢?事实上只在少许地方、短时期内登记过,而且是非常晚的时期才进行的,等真正做土地登记时,南宋快灭亡了。我对浙南山区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方腊动乱中涉及祖先与神明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南宋时期国家在这里进行了土地登记的缘故。当你拿出那一带的族谱,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土地登记与民众捐给佛寺的财产之间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生产上发生的变化,通过土地登记原先捐给佛寺的财产现在仍归民众所有,所以当佛寺没落之后,这些便成为家族的财产。神明和祖先这两个层面在财产问题上汇集,我看到后十分兴奋,在要出版的书中我花了一章去分析这个问题,我大概已经写完了。
我对江苏也很感兴趣,因为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先生曾讲到一句话“江南无宗族”,遭到大家的“围攻”。当然,我相信滨岛先生的这个提法,目的是刺激学者对此深入研究。其实他讲的内容是关键的,江南很多地方都是拜神灵的,但并不能说江南没有宗族,比如范仲淹家族及无锡的华氏宗族,很多大的宗族祠堂都在那一带。但是,江南是个非常复杂的地方,每个角落都不一样,常州和湖州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江南太大、太复杂了,要做整体研究是件很辛苦的事情,我也只是找了一个小小的地方。我找到了哪里呢?以前有一条叫泰伯渠的小河,从无锡一直流到鹅湖,中间流经梅里镇,镇里面有个泰伯庙。泰伯是一个好玩的故事,泰伯姓吴,起源于商朝,他把皇帝位置让给他兄弟,自己跑到江南隐居。过了许久,又有个姓吴叫季子的,他也把皇位让给了哥哥跑到江南来隐居。你会发现两个不同的名字背后的地点以及故事结构大体是相同的,但是你继续了解下去就会明白,这些都是到宋朝才有的。因为宋朝开始封赐地方的时候,其实封赐的是季子,不是泰伯,泰伯的故事是模仿季子的,然后把重点放在了梅里镇,后来有了泰伯庙。
泰伯庙原先是个小庙,但由于这条河流的重要性,梅里镇的地位也就日益凸显,江苏很多大的宗族都是在这样小小的圈子中发展起来的。明朝周忱在江南搞改革时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往南走就是太湖,这一带在宋元明时代就开发湖田。所以我希望看到的不只是浙江山区的故事,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群人开始修族谱,实践他们认为宗族应该有的样子,然后到了清代,因为我们都需要有祠堂,他们通通跑到惠山建祠堂。谁说江苏没有宗族?值得提到的是,郑振满讲莆田平原的宗族,你会看到它的过程和浙江山区又不一样。我已经用时太多了,就不展开具体论述了。
我只是很初步告诉大家,我的书稿打算怎么搞,开头一两章计划讲述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关注的问题等等,然后我打算讲一下浙江、江苏、西南以及山西等地。但是你不能以为我们的重点只是在地区,因为还有很多制度是很分散的,例如说军队的制度,我不是只讲卫所,军队的制度是非常影响社会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还有回族,回族不仅是一个地点,他们坚持他们有另外一个社会,这也需要明白,他们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有乡村的宗教也要弄一章,这样子加起来就有九章、十章了。我希望明年这本书可以出来,纵使不能,最少基本有个书稿,这样早日有机会可以向大家进行报告。要是这本书写完,我现在还有一本书要写,就是我的商业史。事实上,不能跑田野当然不是好事。不能跑田野,就没有很多生活的乐趣,但是也非常感谢现代网络可以找到那么多的历史材料,所以也还是生活得快快乐乐。
总之,我期待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区域进行深度研究,但这些区域不应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整个中国历史认识的一部分。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
从日常生活的文字传统解读民间文献
郑振满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闽浙赣区域史的会议,我参加过两回。以前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比较关注,确实觉得把闽浙赣三个地方联结起来考察是非常重要的。我早期做闽北研究的时候,就发现近代闽北的很多人,其实是从浙江和江西来的,福建历史上的很多大事情,似乎也离不开浙江、江西等地。我上次(第三届闽浙赣工作坊会议前夕)去闽浙交界的仙霞岭一带做田野考察,发现两边的人群实际上有非常密切的交往,他们往往就是同一个家族的人。那么,在历史上他们以什么样的形式互动,又形成了怎样的历史走向,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我今天主要想讲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读文献。我觉得区域史的研究可能要进入一个转型时期,就是从“找资料”转为“读文献”。实际上,区域史研究的最大优势就是比较接地气,所以我们在资料收集上有优势,基本上每次出去做田野调查,我们都能够发现很多新的资料。做正史的研究,用官方的资料,很难不断有新的发现,很多资料都是反复利用过了。但是我们现在也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几年收集的、出版的资料非常多,但是我们来不及精细解读。所以,到底能不能读懂新资料,以及怎么利用这些资料,可能需要大家一起来认真讨论。今天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观点: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从日常生活中,从民间社会的文字传统来理解我们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
去年底,《开放时代》杂志在昆明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研究方法论的会议,主题是“作为中国研究方法的文史哲传统”。当时我做了一个应景的报告,题目是《民间历史文献的“语法”》(后以《民间历史文献与经史传统》为题发表在《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我认为,在民间历史文献中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套话”都离不开中国本土的文史哲传统。我的讨论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民间历史文献如何使用经史传统,二是经史传统如何进入民间历史文献,三是如何从经史传统研究民间历史文献。在那次讨论中,我提出要从经史传统去解读民间文献,打通各种民间文献背后涉及的人(相关的当事人、社会群体)、事(交代事情的经过、做法)、理(引经据典的大道理、立足点)三个层次。我的报告评论人是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他认为我的解释比较自上而下,没有考虑老百姓的能动性问题。因为当时配合会议的主题,我比较强调老百姓如何“对口型”,如何把正统的意识形态、王朝国家的制度等拉到民间历史文献里面来,这个角度确实比较片面,我们还应该关注民间如何“创造”传统。实际上,我们研究中国的文史哲传统(经史传统),同样要通过解读民间文献,去看老百姓怎么理解、如何使用这个传统。在民间社会,中国的文史哲传统到现在还是活着的。只有回到民间日常生活中,我们才能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在哪里。
那么,今天我想转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怎么去看文字或者文献对普通老百姓的意义?他们为什么要去制造各种各样的民间文献?他们用这些民间文献来处理什么问题?民间文献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何在?甚至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借此机会,我想讲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民间历史文献是个非常庞杂的系统,我们要尽可能全面完整地去把家底摸清楚,去搞清楚中国各个区域现在到底还有哪些民间历史文献?当地历史上的民间文献究竟有哪些不同类型?每个区域的民间历史文献又有哪些不同特点?前些年,我跟一些年轻的朋友曾经推动过这个工作,就是在全国不同地区对现存的民间历史文献,特别是公藏机构的民间文献进行普查。我们现在对江西、福建的民间文献保存状况比较清楚,对浙江,特别是浙东南地区的民间文献也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未来应该可以出版联合目录。在区域史研究中,这可能是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对每个区域的现存民间文献开展普查,摸清家底。
最近,我跟一些学生在福建闽东地区收集契约文书,发现当地民间文献的保存状态相当完整,有很多从未见过的文献类型。当地日常生活中的大大小小事情,基本上都要靠文字来处理,包括家族内部的小额借贷,甚至一些琐碎的争议等,都必须记录在案,形成各种文字凭证。哈佛大学的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最近也带着一些学生在读“永泰文书”,有不少新的发现。他认为,在中国乡村社会,从明清以来到近现代,似乎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契约,他用的词叫“证券化”,也就是说不单单是财产、债务,包括各种社会组织、权力关系,最后都会变成一种类似于证券、股票的东西。那么,对当地的老百姓而言,使用文字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东南地区,包括福建、江西、浙江等地,现存民间历史文献比较丰富,可能有一些特别的理由,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例如,也许是这些地区的造纸业比较发达,纸张比较便宜,所以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民间文献;或者是当地历史上的产权关系不明确,所以需要留下各种文字凭证;又或者像宋怡明所说的,可能有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使各种产权形态和社会关系“证券化”了。但如果要深入探讨这一类问题,我们可能还要全面收集各种不同类型的民间历史文献,具体分析各种民间文献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
第二点,民间文献的历史源流,也就是民间文献的生产、流传和使用过程。民间历史文献经历长期的演变过程,每一时期形成的民间文献都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应该深入分析不同时代留下的民间文献,探讨各种民间文献的时代特征。比如族谱,可能早期的族谱主要是士大夫家族的,比较注重谱系、家训之类的内容。后来出现了普通民众的族谱,收录了契约、合同、族规之类的内容。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编修的族谱,我们可以发现家族文献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发生变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同样,碑刻、契约、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日用类书等等,都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征。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各种民间文献的历史源流,探讨“文字下乡”的历史过程,揭示文字传统对区域历史的影响。
我们在区域史研究的过程中,感受很深的是民间文献的“质量”似乎是不断下降。早期的民间文献,包括族谱、契约、碑刻等等,似乎书法都很讲究,文本格式也比较规范。可是越到晚近,民间文献的形式与内容越是杂乱无章,品相、文采等等也是每况愈下。这些文本形态的变化,同样反映了民间文献的时代特征。这就是说,早期的民间文献可能主要是精英阶层制作的,而后期的民间文献可能主要是普通民众制作的。那么,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开始使用文字,甚至是制作文献,对历史的发展有何影响?可能形成怎样的社会机制?反映了怎样的社会转型?这些无疑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考察民间文献的历史源流,其实就是为了探讨区域社会文化的演变趋势与转型过程。
第三点,民间文献的社会“语境”,也就是文字与权力的关系。在区域社会中,究竟是谁掌握了“文字权力”?谁在制作文献?谁在使用文献?如何使用文献?我们现在看到的民间文献是十分庞杂的,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但在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民众都会使用这些文献,通常是不同的人群掌握不同的文献。比如说科仪本,主要是仪式专家(礼生、道士、和尚等)制作和使用。普通民众一般看不懂科仪本,也不会收藏科仪本。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还是要用科仪本,因为他们需要和神、鬼、 祖先打交道。仪式专家借助于科仪本,掌握了宗教仪式活动中的“文字权力” 。
在闽浙赣地区,几乎每个家族都有族谱,但并非普通民众都会去看族谱。在一般情况下,可能主要是家族中的文化精英或领导阶层掌管族谱,因为他们需要利用族谱来管理公共事务。不过,普通民众已经被编入了族谱,他们的权利、义务、社会关系都离不开族谱。我们前不久在闽东福鼎地区考察,看到一个姓刘的家族正在编族谱,他们说每隔十年都要修一次族谱。这个家族现在大约有五六千人,每次修谱都要花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因为修谱之后都要举行大规模的祠堂“晋主”仪式。如果有人不参加修谱活动,祖先谱系没有编入族谱,他们的牌位就进不了祠堂,就不能参加家族组织。他们这次修谱扩大了“收族”的范围,编入了附近两个同姓村庄的祖先谱系。据说,这两个村庄原来没有参加修谱、晋主活动,所以这次要花大价钱。很明显,编修族谱同样是建构“文字权力” 。
民间文献的制作与使用,有时可以借助于外部的力量,不一定需要本地的文化精英。在浙南地区,有一些专门帮人家编修族谱的“专业村”,已经形成了很大规模的“文化产业”。张侃(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经带学生去考察这些村庄,发现当地世代相传的职业就是帮人家修族谱,有丰富的谱牒知识和资料积累,而且还在不断发明新的修谱技术。因此,我们考察民间文献的“社会语境”,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需要有区域文化的广阔视野。
最后,民间文献与大传统的关系,就是如何从经史传统理解民间文献的问题。所谓经史传统,包括中国自古以来的正统意识形态、历朝历代的国家制度,同时也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儒、道、释等宗教仪式传统。这些与历代典籍密切相关的经史传统,为民间文献提供了立论依据,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话语系统。那么,在民间历史文献中,究竟是如何利用这些经史传统?如何“讲套话”?如何“对口型”?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中国文化的传承机制、涉及中国历史的统一性与多元性问题。在区域史研究中,可以通过解读民间历史文献,深入探讨此类问题,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展开学术对话,不断深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认识。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对这个议题多加讨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开头提到的《民间历史文献与经史传统》。

总的说来,在民间文献与区域史研究中,不能停留于收集稀奇的资料,而是应该全面了解民间文献的不同类型、历史源流与社会语境,尤其是关注民间文献与经史传统的关系,深入探讨文字传统对区域历史的影响。
“自下而上”的区域史研究
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刘志伟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中国历史的传统范式,毫无疑问是王朝的历史。朝代更替是历史演变的主旋律,王朝的周期控制着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变化的节奏。我们最习以为常的历史叙述方式,是用王朝来标识社会生活的时间分段,例如唐代社会生活、宋代社会生活、元代社会生活等等。甚至物质形态也可以很清楚区分出不同朝代的风格变化,例如瓷器、建筑、家具的变化,都会跟着统治者的改变而有截然不同的形式风格。这种历史叙述套路已经成为学界和大众固有的不可动摇的认知方式。于是,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无论是政治史,还是社会生活史、物质文明史、精神史,都一定是随着王朝更替的节奏,呈现断裂的状态。人们习惯从王朝国家政权的更迭,去认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演变。因此,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常常呈现出与国家历史一致的阶梯式的变化。
然而,我们在区域史研究中获得的历史认识,却随着王朝更迭呈现出来历史的断裂性,就不如以王朝国家主导的历史认识那样明显。这是因为区域史研究更多是从当地民众的生活去看历史,由此获得的历史认识自然与从国家着眼去看历史有不同的观感。区域史研究与国家历史研究呈现出不同历史节奏。如果说以国家为历史主体的研究,不可能不以国家政权变动为主导,那么区域史研究则可以让我们的目光从国家政权的更迭,聚焦民众生活去观察历史。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区域史研究是否会将国家虚无化,只是关心局部地区,从而妨碍了我们去认识国家的历史进程。其实,区域史研究不仅不会妨碍我们认识国家历史,反而是我们从民众的生活去认识全社会和国家演变历史的重要途径。大家知道,施坚雅很多年前已经提出从由人们的交往形构的区域历史周期去解释中国历史结构的理论解释。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从对细碎的社会生活的微观分析获得整体的历史解释。事实上,我们多年从事区域研究的经验,也清楚表明,区域性的研究对于认识国家历史相当的重要。前几天,我一直被媒体追问,我们出版的50册《东莞明伦堂档案》(东莞市档案馆编、刘志伟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究竟有什么价值?我当时一直在想面对大众媒体要怎么讲它的价值,要大家都可以听得懂。最后我想到了一个主题,就是这些档案不但可以让我们研究明伦堂(一个在县级政权很普遍的讲学论道机构,亦为凝聚地方士人参与地方事务的场所),还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新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对明伦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窥见在一个现代国家体制中,特别是在县级层面上,如何实现地方特色与现代化转变的结合。当然,对着媒体的解说不可能深入展开。进一步来看,明伦堂最初是一个官方设立的、各地都有的机构,大家都很熟悉的组织。到了晚清,它成了士绅聚集的一个组织,演变成地方土绅主导的大规模土地控产的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的地方性政治组织。这种组织到了清末民初,很多时候是地方自治的一个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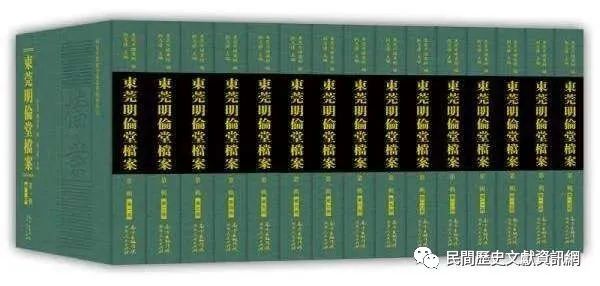
《东莞明伦堂档案》
那么,这种地方自治的基础,其实是有历史传统的,是在明清以来,特别是18,19世纪以来,各个地方发展出来的地方自治的机制上形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本来是在传统王朝国家体制中带有典型的儒家价值体系和组织形式的一种地方士绅的政治组织,到了 19世纪后期,特别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实形成了一种新型国家组织的萌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在追寻区域史研究时,可以进一步去思考的问题(可参考《东莞明伦堂及其档案小议》,收入刘志伟:《溪畔灯微一社会经济史研究杂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同时,我也很认同冯筱才教授刚才的讲话,这个工作坊没有时间的界定,我们应该把目光向下移。刚才科大卫老师说到研究的上移,我这里说应该下移,其实并不矛盾,科老师自己研究的时段就上移到宋代,下移至民国。如果我们站在向下移的角度,再来看明清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关注的地方社会的“自治化”,抑或是自治机制的发展问题,就不会仅仅局限在一个王朝秩序里,而是可以更进一步,让我们在民国时期继续关注它在各个地方的延续,以及它所展现出来的一些机制如何在新阶段进行发展。这可能是开启我们进一步去深究的新方向。
在这一点上,让我联想到萍乡学院的凌焰老师锲而不舍地找到一批赣西北的图甲文书。最近我和郑振满老师,还有一起参会的赵思渊等就去了他那里。这些资料看上去只是涉及我们很熟悉的明清时期几种主要的制度,但事实上图甲文书的背后是图甲会。图甲会跟当地宗族族谱的编撰和宗族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而族谱编纂和宗族发展的基础,又和寺庙或者庙作为一个社区的中心或是社区仪式的一个场所有关,以上这些因素都是相互联系起来的。在凌焰找到的这些赣西北的图甲文书中,我们是可以只停留在很多我们已经关心过的话题上。但是如果把这些文书,包括文书里面保存的很多的会簿、契约、土地登记表、族谱等不同的文类勾连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以后尤其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萍乡的那些被认为是传统社会中王朝国家秩序下的很多东西,其实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既有的制度设计里面,它们之间互动整合,甚至互相引发出其他制度的使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起了一套新的社会秩序。从这方面来说,我想这批文书资料对于我们了解清末以后发生的国家转型是有着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刚才科大卫教授讲到各个地方都在编族谱,你到了哪里看了其他文献才知道编族谱的那些人实际上到底在做什么,只有身处田野,跟其他文献对照,才能看懂这些民间文献。我觉得凌焰找到的这些图甲文书,确确实实是比较精彩的。你可以看到它们较为完整地包含了图甲会簿、族谱等,能让我们整体了解到他们在“搞什么”,当地社会不是血缘组织,而是会社组织。我们最近几个人过去看完后有一个共识、之所以在18世纪有了这些发展,其实跟当时地方政府推行保甲制有很大关系。但是地方社会应对的办法,不是建立一个王朝设计的保甲制,而是把保甲系统在原来寺庙祭祀仪式的基础上,通过会社的方式进行了组建。保甲的这套制度看上去是在当地落实了,但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又是一个很广泛的结盟,所以每一个参加会社的人的资格,是跟图甲里面的户籍身份联系起来的。这种户籍制度,原本是王朝社会管治基层的最基本机制,是编户齐民的办法。但是明代以后,随着图甲本身发生了异变,这种户籍可以不精确到管理具体的个人。这样的话用会社的办法,来跟图甲所给予的这种户籍身份联系起来的机制是什么?机制就是编修族谱,进入了族谱的人自然就有了编户的身份,同时也在会社里面获得了成员的资格。
在这样的一个机制发展出来的“社会”,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凌焰在萍乡的 研究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虽然这些社会现象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不同地方的表现或者说实践的方式、发生的机制、演变的过程是很不一样的。具体来说,例如我们这个工作坊讨论的闽浙赣区域,在民国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各种政治派别、政治势力、政治人物走马灯式地管治国家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其实跟他们背后的地域背景,其所经历、所身处的那个地方发展出来的一种,姑且叫作比较近代的一种国家形态是有关系的。所以闽浙赣这个区域,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构成了比较早期的关于国家建构的一些经验。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的研究就不能仅仅是基于这个地区了,我们可能要扩展到别的地区,去了解不同的政治势力背后对国家建构的不同看法。这对于加深清末民国时期地方社会组织、基层社会转型的了解,也是有很独特的意义。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走出只是在王朝历史的框架里面去讲社会,即基层社会和王朝国家的关系思路,反而更重视大家头脑里面形成的不同的国家想象,或对国家建构的一种结构性的观念,从而把我们的思路、关怀更多地引向近代国家实现的路径或者相应的机制上。
在辽东体会明清更迭
赵世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我想利用今天的这次机会,把我和刘志伟老师、郑振满老师暑期在辽东地区走马观花的一些心得分享给大家。我们这次的路线主要围绕明代女真人兴起、发展的地区,从沈阳一路向抚顺前进,再从抚顺到努尔哈赤的老家,或者他最早建都的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然后继续向着桓仁满族自治县出发,向南再向西,到达海城和营口,在快到渤海湾的地方折返,在辽阳地区考察,最后回到沈阳。
我们的路线基本上就是在通常说的明代辽东地区,也就是按照官方史书记载,明朝初年迫于野人女真部落的袭扰,努尔哈赤的先祖从松花江流域向辽河流域南迁之后,在那里生存、发展的区域。
今天的分享,要从刘老师的问题开始。在我们一路领略朝阳、萨尔浒(抚顺)、新宾、五女山城(本溪桓仁)、海城石棚等风光时,因为是夏天,到处一片葱绿,有稻田,植被也很丰茂。刘志伟老师开玩笑地问了个问题:“这么多的资源、这么好的地方,在历史上为什么他们还那么辛苦地打到我们南方去?”乍听起来,这个问题好像在开玩笑或者是有点奇怪,但是实际上在我看起来是个好问题,并不是我们可以轻易地一带而过的问题。有人会说,因为你们是在夏天的观感,到冬天就大不一样了;也有人会说,你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样子,四百年前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未必了。不过,我们认真思考后会发现,要得出一个到位的认识并不那么容易。特别重要的是,像刚才科大卫老师也提到的,如果我们不到这些地方去跑,去亲身感受,我们可能产生不了这种感受,也不会提出这种疑问。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路走走停停。首先要说的是萨尔浒,现在是个风景区,属于抚顺市东洲区,原名叫大伙房水库。里面有座山叫王杲山,至于名字的渊源,需要追溯到明清时期。在明代的建州女真史上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学清史的人都知道,这时候还不能叫满洲,因为满洲这个族名是到了皇太极 时期才定下来的,所以应该称之为女真),这三个重要人物中除了努尔哈赤之外,一个是李满住,另一个就是王杲。按明朝的年号纪年,李满住大概是在正统前后,王杲大概在嘉靖前后,努尔哈赤最高光时刻是在万历时期。为什么他们最重要?王杲在正史中提到的不多,但是在当地有很多的遗迹,也有很多的传说。传说王杲的父亲原来是五女山里边的猎户(而我们这时候还没有去五女山,也不知道我们去五 女山会跟王杲再产生联系,我们现在只是在萨尔浒这里发现了王杲)。据说当时他救了海西女真的首领,之后逐渐迁到了古勒山一带,并掌管水渡。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这里是辽东山区通往抚顺的要道,也是女真人的贡道,水渡与商业贸易有关系,所以掌管水渡有很大的权力。传说王杲之父就在这里收税,也收买皮张。抚顺在明代是一个很重要的马市所在地,是女真跟明朝人做生意的重要场所,在这里掌管水渡,控制了一个码头,实际上是掌握了非常重要的经济权力。
景区里面有个三慧寺,据说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但是后来被毁坏了,重建后就放到了现在的萨尔浒景区。佛寺很规范,但是在中轴线左侧角落的一个像洞穴那样的空间中,摆放着许多民间信仰的神像,神像前都有名牌,如黄仙、蟒仙等,应该是原先各个村子中保留的那些小庙的神灵,后来因为村里的小庙都被拆毁了,但老百姓还有这个信仰,就将这些民间神祇集中放到了一个佛寺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有一些是关内汉人社会、华北地方社会当中有的,当然有些也是东北地方社会中本身所独有的。

三慧寺
接下来继续往赫图阿拉走,因为我们到新宾的目的是去看努尔哈赤建的都城,顺路先去看了永陵。该陵据称始建于1598年,皇太极天聪八年(1634)改称兴京陵,顺治十六年(1659)才改为永陵。
永陵是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及其曾祖、祖父、父亲的陵寝,这四个庙都有满汉合璧的碑。大家可以把这个和我们在田野调查当中看到的,尤其是在华北祠堂里看到的碑,都理解成我们在华南看到的神主牌,只不过主人公是皇帝。我们看到陵墓之后,立刻就会想到新清史研究常拿满洲性和明朝汉人社会进行对比,强调清朝的独特性。现在看永陵,假设在入关以前就是这样的安排,它和汉人的宗族制度究竟差别有多大呢?猛哥帖木儿是肇祖,肇祖意即肇始之祖,也就是始迁祖。而学界的一些研究对此表示怀疑,甚至有没有曾祖福满这个人也是存疑的;高祖虽然现在也有个名字(锡宝齐篇古),但是从家庙来看谱系的记载,可能是不太确定的。可以看到,至少从皇太极开始,明代女真(满洲)人也像汉人那样追溯和拜祭祖先。
赫图阿拉现在是个大体上重建的景区,幸运的是,我们在其中一个新建的关帝庙里,发现了一口清代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铁钟,题名最前面的是镶黄旗和正黄旗的官员,后面署名的是“八旗众领催兵等”,包括“会首马金太”和其他六个旗的防御和骁骑校等人,应该是香会的会众。根据《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和《清太祖实录》中的记载,可以看到在努尔哈赤建国前就已经修了“七庙”,关帝庙就是其中之一。这不得不让人将关帝庙及其信仰与明代辽东卫所的设置及军士的信仰生活联系,所谓“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军事征服之后,寺庙就代表了礼仪秩序的确立,这一套做法应该是受到明朝人甚至更早的影响。这一带地区原来都是明朝的卫所,从永乐到宣德在奴儿干都司修建永宁寺那个时期,这些地区的女真人就了解了这个礼仪系统的重要性。所以这七庙是不是都是努尔哈赤时期新建的,还是继承了原来明代卫所的一些庙,继续用作为后金一清官方的礼仪标识,如果是,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不是“旧瓶装新酒”,是值得继续考察的。
离开赫图阿拉以后,我们到了本溪桓仁县的五女山城,看到了高句丽始祖碑,也努力攀爬到了山上。本来以为这里的故事是东汉辽东的故事,与明清历史关系不大,但实际上还是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的历史叠加在这里的痕迹。刚才提到的李满住当年就生活在五女山南麓,所以这里一直是建州女真的活动区域。前面说王杲的父亲打猎时救了李满住,传说就是在五女山中。尽管从东汉到明中叶经过了大约 1500年,这里曾经有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势力存在,但到明代女真人的时代,从最基层的社会来看,可能也不像以往理解的那样,从一种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重新开始,可能会有一种长期延续的制度传统可以继承。

离开桓仁之后,我们走了较长一段路,南下到海城。在海城的析木城镇下,有一个村叫姑嫂石村,我们立刻就想到,刘老师曾写过一篇关于姑嫂坟的文章(刘志伟:《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 收入《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传说故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似乎冥冥之中有点缘分,我们都很开心。石棚是很古老的遗存,明显是人工的,一般是建于3000年到5000年前的时代。当 时我们不知道这些石棚的性质和用处,也不知道修建者是些什么人,后来学习了台湾人类学家凌纯声先生的《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我们才知道,除了这里有石棚外,在辽宁海边也有并且数量不少。另外在温州也有与这里类似但不完全一样的石棚,人类学者称之为“石棚文化”,包括我们看到的沿海大陆架附近,像朝鲜半岛、日本等地都有这样的文化遗存。看到这个和我们的明清史关注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只是增长见闻,甚至只是“到此一游”?学术界对明清时期东南亚贸易和东北亚贸易已有研究,但落到具体的人上,好像大多数是讲南人的北上,很少讲到北人的能动行为。石棚虽然极大可能是一种上古墓祭的所在,但它们所反映的东亚沿海的文化联系是很久远的,辽东不一定只与内陆发生联系,它应该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海上联系。同时,在这个文化带中是不应该忽视北方的角色的, 只不过我们对此还不清楚。
从析木城镇的石棚下来,我们就去了八里镇的尚可喜纪念馆,也是新修的尚氏家庙的所在地。院子内外立着原来尚氏墓地的一些墓碑,房间的展览也陈列了一些墓志。尚氏后人很热情,不仅给我们讲了 很有意思的传说故事,还热情地留下我们吃饭。因为尚可喜就藩广东后在广州留下不少遗迹,特别重要的是他对海上贸易的积极态度,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我们以往以为尚可喜等人因为是毛文龙东江旧将,所以有海上贸易的传统,现在希望看看这个传统有没有更早的、更多元的渊源。
这样的想法在去了离海边很近的牛庄后,变得更强烈。这里在明初为牛庄驿,可见已经是交通要道。天命八年(1623),努尔哈赤命皇太极在这里修城驻防,可见女真人很早就认识到这里的重要性。顺治十八年开埠建港,通过大辽河至盘锦人海,说明这是一条海上贸易的通道。有传说此地之得名,是因为清初有种货船被称为“牛子”,也说明了这个地方与水运的关系,所以谈迁《北游录•纪邮下》记载:“牛庄城,周四里,守者满人,外为土著。今招募之人错马,野谷俱登,其值大减于关内,海贾所贸,一舟浮二千石,辽人利之。”同时期的王一元《辽左见闻录》也说:“辽左海禁既弛,百货云集,海艘自闽中开泽,十余日即抵牛庄,一切海货,有更贱于江浙者。”这改变了我们头脑中的印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可能是明代女真人或满洲人的海上贸易传统,或至少是他们对这个传统的接受。
大家都知道,在晚清的《北京条约》中,牛庄是最北边的开埠口岸之一,但此牛庄非彼牛庄。光绪 《海城县志》记:“营口在辽河左岸,距牛庄九十里。海禁未开时,南商浮海,由三岔河至萧姬庙河口登陆,入牛庄市场,嗣后河流淤浅不能深入,因就此为市。咸丰八年与英人订约通商,仍沿牛庄旧称,实则以营口为市场。”营口比牛庄更靠海边,咸丰八年和英国人通商时所谓的牛庄,实际上是指营口,只不过牛庄因为是更悠久、更闻名的港口,所以在条约中用牛庄之名。
虽然我们的行程又从海城向北到辽阳,再向北回到沈阳,但这个话题可以暂时在此打住。广义上的渤海湾,实际上包括山东的莱州湾、天津的渤海湾和辽东湾,我们走马观花似的跑过的,就是辽东湾的腹地,或者是辽河下游直至其入海口。这种河口冲积平原(三角洲)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学术界成果累累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所以,虽然特点不太一样,我们还是应把将这个区域的历史置于海洋和内陆接触、互动的长期过程中去认识和理解,去思考一开始提到的满洲人为何南下的问题。
我们在短暂的时间内看到的、想到的,都是一些零散的碎片。通过这些碎片,我们能不能了解历史上辽东社会的概貌?在政权的层面上,我们在五女山看到东汉时期的高句丽,在很多地方看到明代女真和清代满洲;在社会的层面上,我们看到萨满文化的石棚、辽金至明清的佛寺传统和汉人的民间结社;在人的层面上,我们看到,努尔哈赤和他建州女真的祖先已经不仅是个猎人,他们通过贸易已经对外部世界有了了解。对外部世界了解越多,走出一隅之地的动力就越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不同的碎片连缀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条区域内部发展的线索。具体来说,就是把明清之际乃至更早的辽东放到一个更多元、开放的空间中去理解,包括清兵南下在内的所谓“南下牧马”,也包括所谓“满洲性”或 “辽东性”是否等同于“内亚性”等等,以生活世界的丰富性来避免历史解释上的单一性。
(本文經整理者溫海波教授授權發佈,原載《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頁29-36。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民間歷史文獻資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