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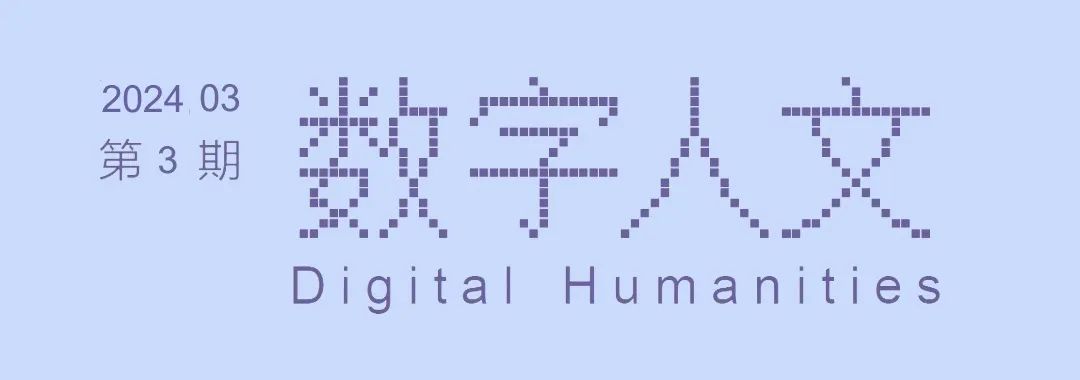
徐浩铭 /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梁 陈 /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
尚 平 / 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明初以降的实物税收模式在明代中后期难以继续支撑国家财政的运行,自16世纪以来,明政府主导了一系列由局部到整体,从改征折色到改征白银的财税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为将实物财税转化为白银货币财税,这一过程被学界视为近代国家转型。近年来,实物税收的原额与税赋折银之间存在何种联系一直为学界所探讨,但明代北方地区的税赋改革问题一直未被细探。鉴于山东兖州府地理位置及资料留存较为完备,笔者利用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使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将万历《兖州府志》中的27州县的夏税秋粮麦米及附加税的实物征收定额和当田赋改征白银之后的折算数字进行空间上的可视化展现;再利用关系网络分析软件(Gephi)将各州县田赋分派到不同仓场的情况进行分析梳理。从而引申出明代山东地区的田赋在改征白银的过程中,“变”与“不变”以及“如何变”的问题,从量化的角度管窥明代田赋改征白银前后的税额变化,以及原额对白银货币化改革的束缚情况,分析新旧税制的弹性力度。
关键词:田赋 本色 折色 折银 兖州府
近年来财政史学界在原额主义、地方财政结构、洪武型财政三个分析理论的框架之下对明代财政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1]明代“洪武型财政”[2]强调用实物作为税收的缴纳形式,国家财政运转以实物为主体。“地方财政结构”为近世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概念,明代是否存在地方财政一直备受学界争议。[3]而“原额主义”似乎成为束缚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铁链,限制了明朝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定额化的税制与难以完全征收的现状矛盾尖锐。[4]明中叶以降,政府为了摆脱“实物税收”所造成的财政税收困境,规避世界市场所带来的民间白银通货膨胀,明政府对待白银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抗拒再到接受,白银逐渐取得法定货币的地位。[5]随着“一条鞭法”“一串铃法”的推行,田赋及力役也从“实物”变为“白银”。明初的纳税政策奉行“实物至上”原则,[6]各府的州县是征收税赋的基本空间单元,各地需征税额的高低则视其空间单元内土地的优劣情况而定。[7]明代“所收税课,有本色,有折色”,[8]弘治时期会计天下夏税之数时便有本色丝、折色丝[9]之分。在古代,本色与折色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是否为既定征收的税物,“绍兴十六年(1146)诏旨折纳:绢三分折钱,七分本色;䌷八分折钱,二分本色”。[10]由此可知,“本色”即既定税项所要求的物品,折色则是其替代品。明代正税分为夏税与秋粮,“正赋有本色,有折色”。[11]在正项田赋中,“本色”为米、麦,当灾荒之年米、麦征收不足时,各地方代替米、麦进行折纳的物品称为米、麦的“折色”,[12]用米、麦之外的物品代输并且抵扣粮食额度的行为被称为“改折”或“折征”。[13]夏秋两税中本色与折色田赋的征收种类复杂且多样,两京十三省的本色、折色征收内容除本色田赋中的夏税麦及秋粮米外大多不同。除去本色、折色正项田赋外,夏秋两税中还包括农桑丝绢、丝绵折绢、马草等附加税,而附加税根据地亩来征收,作为固有税收,其征收数量极少。[14]除田赋折银外,明代赋税折银还包括盐课、上供物料、徭役的折银。[15]明初所有田赋以实物形式征收,起运、存留则是中央对各地田赋的分配手段。田赋的起运情况受限于交通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差异,因此实物税收下的财政运行模式制约了中央对全国各地田赋的直接分配。[16]从整个白银货币化改革的过程来看,改革中存在阶段性及区域性特征,改革前期和后期田赋税收纳折的阶段性层次鲜明,各地改折力度也存在差异。[17]从明代的赋税改革研究来看,1930年代以来,以梁方仲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地方与中央的赋役关系角度进行讨论,并开始引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讨论明代白银存量问题。[18]傅衣凌则全面讨论了明代国家赋役与社会转型间的关系。[19]黄仁宇则对明代的财政转型做了宏观的研究,全面论述了16世纪明代国家与财政的关系。[20]近年来,“白银货币化”概念被部分学者引用到明代财政研究中,万明、侯官响以地方区域为研究对象,引用此概念针对明代浙江、山西的田赋改革过程进行了系列讨论。[21]刘光临则利用货币经济相关理论对明代货币规模进行了重构,并得出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实则对明代的市场具有积极作用的结论。[22]赋税模式转型方面,丁亮针对明中期浙江、南直隶地区的田赋改革和社会变化进行深入探析,提出明代赋税征收模式在嘉靖中后期开始迅速转型的观点。[23]但既有的明代赋役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赋役制度演变的整体概述上。[24]相较于其他时期而言,明代财政研究缺乏对问题准确且系统的把握,这也被学界称为“世纪遗憾”。[25]随着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人文学科的数字化转型为明代赋税改革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以计算机为依托,通过数据整合及大数据综合分析,为明代田赋研究的量化分析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明中叶赋税改革过程的重构提供了更加开放的空间。

(一)兖州府田赋折银问题研究概述
从明代北方地区来看,山东的田赋对于整个明代财政而言尤为重要,根据黄仁宇对明代漕运的研究情况来看,明代所规定山东的运输税额位列北方第一。[26]同时,山东地区沟通南北直隶,地处大运河沿线腹地;明代中叶,由于黄河部分支流的河道淤积,大运河运量下降,有人建议在山东半岛的中部横向开凿一条新运河。[27]再者,山东还需向北方供应边储及马草。[28]然而目前学界对于明代山东地区的田赋研究较少,且前人并未从空间单元上,借助大数据综合分析的方法,对北方晋豫鲁地区的田赋折银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以往的研究认为,山东地区的田赋改折白银进程并不顺利,推行改革措施的执行者并非政策本身的支持者。在田赋改革初期,各地推行改革的力度及改革内容并不统一,改革初期所推行的措施也较为保守,“一条鞭法”与“三等九则法”并行的现象不在少数。[29]申斌认为明代白银货币化改革中,地方获得部分自主财权并可以进行“通融分派”,[30]岩井茂树也认为明代赋税受制于“原额”的束缚,但随着财政赤字的增加,地方财政的灵活性也随之提高。[31]而笔者在之前针对明代山东地区的研究中也得出过田赋改折白银的过程中存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差异,且改革本身存在弹性调节机制的观点。明代各地税额自永乐之后基本固定,并为定额,在田赋改折白银前,部分区域出现的些许定额的改变都在百石之内。[32]
区域性的田赋折银问题研究是否能对明代中后期的赋税改革有所回应?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前文曾提到大部分学者都是以一个“府”或“布政司”作为研究区域,以府作为空间研究单位,可以深入分析小区域内部的细微改变;以布政司为空间研究单位,则碍于各府州县的资料完整性并不统一,因此研究的深入程度难以保证。侯官响以万历时期的苏州为个案,对苏州府的田赋折银情况进行过细微考察。[33]丁亮则将与兖州府毗邻的东昌府作为研究空间,对明代东昌府的均徭役结构进行了实态分析。[34]关于明代田赋折银问题研究,学界的大部分学者都以江南富庶之地作为研究空间,但对于北方地区和大运河沿线区域的田赋折银问题探析却有所忽略。明代山东完整性的田赋资料在全国性的财政史书《万历会计录》中有所缺失,但幸运的是山东地区明代的方志资料留存较为完备。关于具体研究区域的选择,笔者初定为济南府;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可知,济南府在隆庆五年(1571)至万历二十四年(1596)这一段时间内,共领4州26县。[35]但通过嘉靖十二年(1533)《山东通志》及隆庆五年《山东经会录》中关于山东布政司各府田赋总数的记载,以及地方志资料留存的完整性来看,现世留存关于明代的济南府志及县志资料有所缺失,而兖州府则拥有较为完备的明代方志史料。目前关于兖州府境内所有州县田赋的完整记录,见于隆庆五年《山东经会录》[36]、万历元年(1573)《兖州府志》[37]、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38],但济南府的完整田赋记载仅能通过《山东经会录》一书获知。[39]
笔者依据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及万历二十五年(1597)《汶上县志》中的秋粮米白银起运额得知,自万历改革后白银的起运税额并非恒定。[40]通过“三部资料”[41]的记载可知兖州府下辖27州县的本色夏税麦、秋粮米及秋粮马草的起运目的地有所不同,起运仓场的分配税额也有所差异。兖州府27州县的田赋及附加税在征收之后通过漕运进入全国各级仓场,其中有中央仓场与地方仓场,而田赋输送到各类仓场的定额与仓场的折价不尽相同,定额及折价差异背后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政府对于田赋改折白银政策的执行逻辑。
(二)“兖州府”田赋数据的来源及处理
依据现存资料的整理情况,嘉靖年间山东地区的地方志并未详细记录田赋折银数字及田赋起运到各级仓场的分配情况。将上述三部文献进行比对之后,可以明确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中关于田赋的记载均转录自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在万历元年《兖州府志》与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中都同时出现了曹州秋粮米的存留数量缺少了“300石”的记载,而在这两个版本的府志中,关于这300石的缺数及其用途的记载皆尽一致。
二书记载如下:“起运六千石,存留兑拨郯城县起运三百石,待该县荒田垦熟,议复实征六千三百石,实征银六千九百五十四两九钱六分。”[42]但关于万历元年《兖州府志》的田赋数字来源,笔者将其与隆庆五年《山东经会录》中对于兖州府的记载做了详细比对,可以确定的是万历元年《兖州府志》中对于田赋的记载来源于《山东经会录》。但万历元年《兖州府志》中关于州县的“土地清丈”“一条鞭例”未见于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因此笔者在研究中将三部资料联合使用。在田赋的记载内容进行数据化转录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府志中关于本色麦米的记载并无田赋实物定额及存留定额的白银纳折数字,本色麦米中可以转录为意义数据的仅有“起运”一项。夏税、秋粮的附加税中除马草有起运定额与起运折银数外,农桑、丝绵皆为实物定额及其白银纳折数字,花绒项全征本色,并无起运及存留情况的相关记载。后续文中出现的折银率指实际征银额除以实物定额。折银价为史料文献所载实际折价,明代白银的两与钱之间为十进制关系。[43]而以滋阳县中的秋粮起运项为例,“洗马林堡仓并新河口堡仓粟米九百一石四斗,每石一两二钱,共银一千八十一两六钱八分”。[44]其中粟米为901.4石,折价为每石1.2两白银,实征银为1081.68两,即901.4(粟米)×1.2(折价)=1081.68。转录情况见“兖州府本色田赋折银转录表”(表1)、“兖州府田赋附加税折银转录表”(表2)。
在转录过程中,本色田赋起运项的实物定额计量单位仅为“石”,因此该项在数据转录过程中均为整数。不同州县及不同项实物田赋的折银数字在文献中所对应的实际计量单位会在两、钱、分、厘之间浮动,且折银数字自身并未展现出某种共性规律,以作为整数之后究竟需要保留几位小数的取舍标准。
为了便于数据处理及计算,笔者通过运用“有效数字定义”[45]来界定小数点后位数的保留标准。
定义如下:设x的近似值x*=±0.x1x2…xn×10m。其中,xi是0到9之间的任一个数,但n是正整数,m是整数,若![]() 则称x*为x的具有n位有效数字的近似值,x1x2…xn准确到第n位,是x*的有效数字。
则称x*为x的具有n位有效数字的近似值,x1x2…xn准确到第n位,是x*的有效数字。
证明过程如下:曲阜县夏税小麦“实征银五百七十二两三钱八分二厘”[46](572.382两),笔者处理数字为572.38。

因此,572为572.382的有效数字。
综上所述,数据自身的有效数字可达个位,因此数据精确到个位或小数点后两位并不会造成整体分析的信度下降。

(注:实物定额单位为石且保留整数,纳折银单位为两且保留两位小数。)
表1 兖州府本色田赋折银转录表

(注:实物定额单位农桑折绢与丝绵折绢为匹、花绒为斤、马草为束,纳折银单位为两且保留两位小数。)
表2 兖州府田赋附加税折银转录表

在ArcGIS软件中利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部分(山东一)作为栅格数据的来源,再以此建立矢量数据,[47]并添加30米精度的DEM数据及3、4、5级水系网络作为底图。结合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山东兖州府在万历元年共计4州23县。4州分别为曹州、沂州、济宁州、东平州,其中曹州领曹县、定陶二县,沂州领郯城、费县二县,济宁州领嘉祥、巨野、郓城三县,东平州领汶上、东阿、平阴、阳谷、寿张五县。剩下11直辖县分别为:滋阳县、曲阜县、宁阳县、邹县、泗水县、滕县、峄县、金乡县、鱼台县、单县、城武县。[48]将文献和数据相结合,以本色田赋中夏税起运麦的实物定额、折银额,秋粮起运米的实物定额、折银额;附加税中的农桑折绢、丝绵折绢的实物定额及折银额,马草实物定额及马草折银额作为数据库的属性项,并以此在矢量数据中绘制出万历兖州府田赋空间可视化图。
(一)夏税秋粮本色田赋的可视化展现
在ArcGIS软件中利用自然间断点法将夏税麦的实物起运定额及折银起运额分为三个等级,实物起运定额的等级为低起运额(1级)850—4,100、中起运额(2级)4,100—8,500、高起运额(3级)8,500—13,500三个区间(保留整数,单位为石);再将折银起运额分为三个等级,低起运额(1级)458.92—918.16、中起运额(2级)918.16—1,950.12、高起运额(3级)1,950.12—3,294.22(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单位为两)。
利用上述方法再将秋粮米的实物起运定额及折银起运额分为三个等级,秋粮实物起运定额的等级为低起运额(1级)2,000—4,500、中起运额(2级)4,500—11,000、高起运额(3级)11,000—22,000三个区间(保留整数,单位为石);再将折银起运额分为三个等级,低起运额(1级)1,948.98—4,239.32、中起运额(2级)4,239.32—7,669.87、高起运额(3级)7,669.87—13,360.75(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单位为两。详见图1)。

图1 夏秋本色麦米田赋起运定额及折银起运额空间可视化展现图
笔者通过对兖州府的田赋数据进行空间可视化展现,发现部分区域出现了以下几个现象:
从夏税本色田赋改折白银前后的过程来看,起运田赋改征白银后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夏税麦实物起运定额较低的州县在改征白银之后出现了折银起运额升高的现象;二是田赋改征白银前后都保持了空间上的恒定(详见表3)。从秋粮田赋改折白银前后的过程来看,起运田赋改征白银后出现三种结果:一是秋粮米实物起运定额较低的州县在改征白银之后出现了折银起运额升高的现象;二是秋粮米实物起运定额较高的县在改征白银后出现了折银起运额降低的现象;三是部分州县的田赋在改征白银前后都保持了空间上的恒定(详见表4)。除上述五种现象外,部分州县其夏秋两税田赋在改折白银前后均保持了空间上的整体恒定(详见表5)。

表3 夏税本色田赋起运麦改折前后变化表

表4 秋粮本色田赋起运米改折前后变化表
 [49][50]
[49][50]
表5 夏秋两税本色田赋折银前后均保持恒定州县
(二)夏税秋粮附加税的可视化展现
需要指出的是,除秋粮中的马草外,农桑折绢与丝绵折绢本身数额并不多,同时也不具有起运属性,仅有实物定额及相对应的折银额。花绒在此时期还未改征白银,因此笔者在空间可视化操作中仅针对花绒的实物定额项进行空间可视化展现。在ArcGIS软件中将夏税丝绵折绢的实物起运定额及白银起运银纳额分别分为三个等级。因附加税数额较小,因此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实物定额以“匹”为单位并取整数,折银额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实物定额的等级为低定额(1级)29—153、中定额(2级)153—293、高定额(3级)293—502三个区间(保留整数,单位为匹)。再将折银额分为三个等级,低折银额(1级)20.51—107.46、中折银额(2级)107.46—205.74、高折银额(3级)205.74—352.00(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单位为两)。利用上述方法将农桑折绢的实物定额及折银额分为三个等级。实物定额的等级为低定额(1级)69—296、中定额(2级)296—916、高定额(3级)916—1927三个区间(保留整数,单位为匹)。再将折银额分为三个等级,低折银额(1级)48.32—207.56、中折银额(2级)207.56—641.46、高折银额(3级)641.46—1,349.29(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单位为两)。笔者将马草的实物起运定额及折银起运额分别分为三个等级。实物起运定额的等级为低起运额(1级)5,645—29,748、中起运额(2级)29,748—59,977、高起运额(3级)59,977—99,296三个区间(保留整数,单位为束)。折银起运额分为三个等级,低起运额(1级)302.17—737.10、中起运额(2级)737.10—1,398.03、高起运额(3级)1,398.03—3,517.47(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单位为两。详见图2、图3)。

图2 夏税田赋附加税起运定额及折银起运额空间可视化展现图

图3 秋粮田赋附加税起运定额及折银起运额空间可视化展现图
夏秋田赋附加税改征白银前后税额的空间可视化差异(横向解读)—从田赋附加税的定额及其折银额的可视化情况来看,夏税中的农桑折绢、丝绵折绢在进行改征白银后并未呈现出空间上从整体到局部的改变,整个兖州府内的27州县都保持了恒定。但秋粮中的马草在改征白银后则呈现出较大的空间差异,阳谷县、东阿县、东平州、汶上县、济宁州、滋阳县、曹州、曹县、单县、金乡县、鱼台县、滕县、郯城县、费县、峄县、宁阳县、邹县呈现出白银化程度升高的现象,其余10县则保持了恒定。
(三)关于田赋可视化结果的讨论
当田赋改折白银之后,各州县田赋折银额的形成基本上以其对应的实物定额为基准,而造册上报的实物定额则是田赋由实物到白银这一转换过程的重要痕迹。[51]然而在这个转换过程中,部分州县的田赋在田赋折银后却呈现出与实物定额阶段所不同的结果。以夏税及秋粮的本色项为例,部分州县的田赋改折白银后在恒定空间内部出现银纳额度上升的情况,部分则出现银纳额度下降的现象。但大部分的州县在恒定空间内部则呈现出折银前后所在税收区间的一致性。笔者在ArcGIS软件中利用了自然间断点(JenKs)的分类方法,将各州县的税额从高到低分为三个等级。自然间断点法是根据聚类分析的原理依据目标样本数据间的相似性进行分类截断,此种分类方法适用于在不清楚数据分布特征的情景下,在数据分布无特殊规律的情况下,使用此类方法最容易得到理想的结果。[52]图4A为“夏税本色田赋实物定额的自然间断点分类统计”,图4B为“夏税本色田赋折银额的自然间断点分类统计”。图4C为“秋粮本色田赋实物定额的自然间断点分类统计”,图4D为“秋粮本色田赋折银额的自然间断点分类统计”。纵轴代表“州县数量”,横轴为“不同州县间的征收额”。基于上述自然间断点法,即通过样本自身相似性分类的原理,在州县及田赋项目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将相同项目田赋在折银前后进行横向对比,从图4整体可得“夏税本色田赋”及“秋粮本色田赋”在征收白银前后的聚类特征都有以下共性:本色田赋在实物定额阶段主要集中在中、低起运税额区,本色田赋折银后,高、中、低起运税额区都有不同数量的州县分布在其中。以此可以发现,各州县折银后的田赋折银额相较于其对应折银前的实物定额,通过自然间断点法分类后,其在之前划分的高、中、低三个税额等级中的分布特征也更为平均。

图4 夏税秋粮本色田赋起运定额及折银起运额自然间断点分类图
夏税及秋粮的附加税的折银情况则较为恒定,夏税农桑折绢、丝绵折绢在恒定空间内部并未呈现出改折前后的差异。[53]需要注意的是,夏税农桑折绢、丝绵折绢作为田赋的附加税而言其征收额较少,而此处的农桑折绢、丝绵折绢与大量利用布帛、丝绵代征粮食中的折色田赋并无关系。[54]同时黄仁宇认为在除专业生产丝绢之外的地区,丝绢收入少到可以被忽略不计。但附属附加税中唯一对纳税人有很大影响的是马草,而马草的征收只局限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南北直隶。[55]从兖州府各州县间马草税额的自然间断点分类结果来看,马草经过改征白银后,大部分州县由实物定额阶段的低税额区升到中税额区,中税额区则升到高税额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改变,实则是因为在征收实物阶段,各州县马草的定额数量巨大,州县之间定额差距过大,因此所划分出的大部分州县都位于中低税额区。通过改征白银之后,各州县间的马草税额趋于平均。浮动变化可见图5,其中纵轴代表“州县数量”,横轴代表“不同州县间的征收额”,图5A为实物定额,图5B为白银征收额。针对田赋附加税在空间上出现的此类现象,笔者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也印证了上述观点。

图5 自然间断点分类中各州县马草折银前后变化浮动图
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以州县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改征白银之前,各州县田赋的实物定额影响因子得分为Z=1.94,此时随机产生聚类的概率小于10%,各州县之间的农桑折绢定额在空间上保持了较强的正相关性。当各州县的田赋改折白银后,州县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相较改折之前有所上升,影响因子Z=2.08,此时产生随机聚类的概率小于5%(详见图6)。而丝绵折绢与农桑折绢呈现出相同的空间特征结果(详见图7),改折前后各州县在空间上皆保持了一致性,这也印证了之前笔者的观点,田赋附加税在改折前后保持了空间上“恒定”的特征。

图6 兖州府农桑折绢定额(左图)及农桑折绢折银额(右图)空间自相关分析

图7 兖州府丝绵折绢定额(左图)及丝绵折绢折银额(右图)空间自相关分析
但根据秋粮马草的空间自相关的分析结果(图8)来看,马草一项经过改征白银之后,并未像农桑折绢、丝绵折绢一样保持空间上的整体恒定,而是在空间上呈现出随机性,改折前Z=1.85,改折后Z=1.01。这也意味着州县之间的相互影响力被削弱,马草改征白银之后,州县间马草项的折银额更为灵活。

图8 兖州府马草定额(左图)及起运马草折银额(右图)空间自相关分析

从兖州府田赋改折白银前后的空间可视化结果来看,阳谷县、东平州、济宁州在改折后呈现出夏秋本色麦米、附加税马草白银化程度整体上升的现象。费县、鱼台县、金乡县的秋粮本色田赋在改折白银后呈现出下降的现象。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本色田赋在改折白银后所呈现出的一系列变化实则就是折银率的变化,区域内折银率的高低也反映了该区域白银化程度的高低。从整个兖州府来看,兖州府内夏税本色田赋起运定额的平均折银率为0.39,秋粮本色田赋起运定额的平均折银率为0.85,夏税中附加税的平均折银率为0.7,而秋粮附加税马草的平均折银率为0.04(参见前表1、表2)。折银率的改变说明田赋中各项征收的具体内容在折银后出现了变化。原因为明政府更青睐本色麦米田赋,阳谷县、东平州、济宁州、汶上县的夏税及秋粮折银率均超过平均值。上述四州县其折纳的物品多为折银价较高的“麦”“粟米”;由于其总量大以及折银价高,田赋经过折银后整体的总量也会增高。而费县、鱼台县则以大量的折色田赋抵折实物的定额,费县通过将布帛运往德州常盈库抵折本色米的数额高达8350石,鱼台县高达4230石;[56]而折色田赋自身的折银价较低,因此最后的结果为两县的田赋折银后出现整体下降的情况。以沂州、曲阜县为代表,该二州县其改折前后的夏秋两税本色与折色田赋都保持了稳定的态势。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沂州的夏秋田赋都位于ArcGIS中的高起运额区间,曲阜县则为低起运额区间,同时并未出现大量折色抵折本色的现象。沂州本色实物定额都位居全府首位,因此各项实物田赋在经过折银之后的数量仍然庞大。曲阜县的实物田赋如粟米、麦折米的单项数额较小,因此田赋折银后并未造成大幅度的变化。该二州县的共性为州县内的夏秋两税田赋的征收数量过于庞大或是微小。明代折色田赋其作用便是折征本色,按其税项设计的初衷而言,其是为了缓解地方上因特殊情况导致本色征收不足的压力。“十七年,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于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57]可以明确的是,夏税田赋中的附加税农桑折绢、丝绵折绢其折价并未存在空间上的差异,皆为固定的七钱,但作为折色征收则会根据其最终的折色类型呈现折银价差异。[58]“大同屯地定为上、中、下分数,上等起征本色,中等折色七钱,三等三钱,山西、河南运粮量地之远近险易,以定本色、折色之例。”[59]之所以各州县的丝绵、农桑折绢折银后在空间上呈现出恒定的现象,是因为各类折色税赋自身折银价固定,折银后不会导致州县之间的税收比重发生改变。夏税本色麦与秋粮本色米会因起运仓场的差异而呈现出折银价格上的差异。同时夏秋两税的征收定额与银纳额从恒定空间中来看,无论是改折前还是改折后,夏秋两税本身也并非恒定。根据《万历会计录》中对夏秋两税的记载,秋粮在税收中的占比一直高于夏税,“夏税米麦共肆百陆拾万伍仟贰百肆拾贰石捌斗柒升伍合柒勺零(4,605,242.8757)……秋粮米共贰仟贰百叁万叁仟贰百壹拾柒石贰斗叁合叁勺零(22,033,217.2033)。”[60]秋粮在明代田赋中的重要性高于夏税。“均秋夏税粮,夫淮北之赋,秋粮为重,秋粮之中起运为急。至于夏税,起科既少,催征又缓。”[61]
(一)夏税本色田赋起运银纳额问题
夏税本色田赋的征收实物以“麦”为征收主体,但在改征白银期间也并非一直以“麦”作为直接的折纳主体,“麦”逐渐成为征收过程中的等量交换物。这也意味着在夏税的征收过程中,征收的主体无论是“米”还是“棉麻”等折色田赋,其改折都是通过“麦”作为换算标准,哪怕整个折征过程中都不曾出现过真实的“麦”。明初的实物税收模式之下,全国范围内全征本色实物不切实际,因地制宜就显得很重要。洪武时期,“帝曰:‘折收逋赋,盖欲苏民困也。’”[62]到了成化年间,章懋在《两浙盐法利弊》中曾谏言:“单丁老弱,家计贫难者,煎办不前,课入不敷,屡遭鞭挞之苦;而盐入于官,或被雨水销镕,又有追赔之患,此穷户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蒙轻其岁课,使纳折色,庶几宽民一分,使之稍可存活,是即生死骨肉之恩也。”[63]而到了嘉靖年间马卿在《攒运粮储疏》中上疏称:“本色加耗甚重,比之折色所费几倍。两年全征,东南之民力竭矣。运军往年粮有折色,则船有减存,得以休息。今两年全运,而军士之疲劳甚矣,乃复遇此数省全灾,军民困苦,若不量改折色,其何以堪?”[64]从明初到明中叶折色田赋的征收发展过程来看,折色项田赋一直是僵化的实物税收模式中最为灵活的部分。从明中叶来看,田赋征收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折色田赋抵兑本色的现象,“麦”已经成为夏税征收中的统一计量单位。在夏税的征收过程中,不同地区会出现“布折麦”或“米折麦”的现象,但“布”或“米”经过换算成“麦”之后的折银价格相对于直接征收的“麦”,前一个“麦”的价格会下降。以郯城县为例,郯城县夏税麦的起运情况如下:
故设官而无损于民,有益于事,存之可也。设官而无益于事,有害于民,去之可也,并省之可也。今观临清、广积二仓旧惟监督内臣一员,后增至二员。天顺等年亟罢,其后增至九员。正德五年,裁革三员,止存六员。正德六年,存留三员,近增一十五员。[90]
而从该仓所需官员数量及仓场规模改变的情况来看,这就意味着临清广积二仓在现实中不得不扩大规模建制以缓解仓场的压力。“明初京卫有军储仓,洪武三年(1370)增置至二十所,且建临濠、临清二仓以供转运。各行省……”[91]而到了宣德年间,临清仓规模再次扩大,“宣德中,增造临清仓,容三百万石”。[92]到了万历二年(1574)“增建原八十一廒,改一廒于常盈仓”[93],再加上明代对漕运的依赖性远超前代,需通过仓场对田赋进行转运。[94]成化八年(1472),临清仓转运共计“二十四万一千八百石,后临清广积二仓每年会派山东河南夏税秋粮共一十一万四千四百石”。[95]因此仓场的规模增加直接反映了整个国家财税的收入增加。从各州县起运到仓场的折价来看,各州县的田赋与仓场之间的“度”都较为平均,此现象可以理解为明政府在既定的“折银”方案中折价分配都较为平均。
(二)夏税麦折银额的Gephi可视化结果
图10为各州县夏税田赋折银后与仓场分配关系的可视化图,结合图9可以发现“临清广积二仓”的“度”权重最高,而“光禄寺”的“度”虽保持不变,但“边”的权重则相较于“白银折价阶段”有所下降。从图10中来看,田赋改折白银之后,“临清广积二仓”的度保持了与折价相同的结果,但“边”的权重上升,此现象说明“临清广积二仓”在田赋折银后,其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本色田赋权重上升。一些情况特殊的州县如“费县”“郯城县”“沂州”“滕县”将“钞”抵折为“夏税麦定额”的现象较为突出,其大部分实物税收都用“钞”进行抵折麦后再折银征收。部分县如汶上县、阳谷县、邹县“边”的权重上升,其通过用“布”抵折为“定额麦”后折银的情况也较为明显,折色田赋的权重上升。

图10 州县夏税本色麦折银后与仓场分配关系可视化图
(三)秋粮米实物定额及折银价的Gephi可视化结果
笔者通过对各州县夏税田赋起运及分配仓场的关系进行梳理之后,共计建立起182条分配关系。图11上为“秋粮米定额”与“征收仓场”之间的分配关系。其中可以看出“兑军攒运米”的“度”最高,整个兖州府内有多达24个州县需要承担“兑军攒运米”的派额。从“边”的权重来看,部分州县如“沂州”“滕县”“郯城县”“费县”利用“折色田赋”代征“本色田赋”的现象较为突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秋粮的起运情况中,兖州府内除沂州、费县、郯城县外,其余州县均有“兑军攒运米”的起运项。关于“兑军攒运米”的数据处理,并无具体的“每石折银价”及“总折银价”,笔者的处理方式为用各州县方志中所载的“实征银”减去除“兑军攒运米”项外的各项田赋折银数字总和。例如:曹县共计6条分配记录,“兑军攒运折色米157.60、张家口堡仓黑豆600.00、张家口堡仓粟米2,550.39、光禄寺白芝麻88.73、芝麻72.45、绿豆106.93”[96]。上述总和的数值为3,576.10,但曹县的起运实征银的数值为7,075.76[97],因此可算出“兑军攒运米”折银的数值为3,499.66。从各州县折银价与仓场分配关系图(图11)来看,明政府既定的折银计划中,仓场与州县之间“边”的权重都较为统一,这意味着各州县与仓场之间在田赋的分配折价上都较为平均。州县与仓场节点的“度”则因为各州县分配关系在改折前后并未发生增加或减少,因此无论在折银前或后及折价的可视化上,“度”都保持了一致。

图11 州县秋粮本色米定额(上)及白银折价(下)与仓场分配关系可视化图
(四)秋粮米折银额的Gephi可视化结果
图12为各州县的“秋粮田赋”折银后与“征收仓场”间分配关系的可视化图。结合图11可以发现,当“秋粮本色田赋”改折白银后,其结果基本与改折之前的结果相一致,并未出现州县与仓场之间“度”的变化。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则是受到自身原额数量的影响,折银之后的结果与征收实物阶段也保持了大致相同的结果。明代漕运通常遵循“不得蠲免,务运本色”[98]的原则,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缺少“兑军攒运米”征收项的州县“沂州”“郯城县”“费县”,利用折色田赋完成了州县的本色田赋定额指标。而丁亮通过对浙江正项田赋折银情况考察后提出部分仓场可以本折兼收,但此类情况大多在灾荒或本色无法完全征收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因此并非制度性的改变。[99]其余24州县在田赋折银之后,“兑军攒运米”的权重上升。

图12 州县秋粮本色米折银后与仓场分配关系可视化图

图13 州县马草定额(上)及白银折价(下)与仓场分配关系可视化图
(五)马草实物定额及白银折价的Gephi可视化结果
图13为“马草定额”与“征收仓场”间分配关系的可视化图,其中的太仓银库的度及权重最高,且沂州相对于太仓银库的度及权重最高。从图13中可以看出在明政府的既定折银计划中,“太仓银库”“御马仓”及“中府外场”是改折的核心枢纽。马草的折银价并不高,所有仓场的折价在9厘到7分之间浮动。其中“太仓银库”的折价为每束3分5厘,“中府外场”为每束6分,“御马仓”为每束7分。
(六)马草折银的Gephi可视化结果
图14为马草改折白银后各州县马草折银额与仓场的联系,从Gephi的可视化结果来看,其中太仓银库的度及权重最高,“太仓银库”在马草改折白银后,仍然和折银前一样作为明政府进行马草征收过程中最核心的枢纽。而当征收田赋马草折银后,其在Gephi的可视化结果中并未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变化,原因为各州县的实物定额不变,不同仓场之间的折银价虽有差异,但州县之间的实物定额差距过大,这导致了即使“太仓银库”的折银价为每束草“3分5厘”,但基于庞大的“实物定额”与定额征收阶段相同的“州县与仓场间的分配关系”,节点间的“度”并未改变。因此,即使在田赋折银之后,“太仓银库”仍然为征收马草数量最大、需征收州县数量最多的仓场。但几条实物定额较高的分配关系如沂州、滕县、郯城县、费县,其“边”权重发生了下降。从马草改折白银前后的分配情况进行对比,马草的折银情况似乎一直围绕着一个主旨——“趋向平均”。

图14 州县马草折银后与仓场分配关系可视化图

总体而言,笔者利用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万历兖州府的田赋改折情况的初步探析,将兖州府内的夏税、秋粮的本色、折色、附加税的定额及折银额的起征情况做了可视化分析处理后,结合学界主流观点及史料考据,提出以下四个观点:
其一,兖州府的田赋在改折白银的过程中,本色麦米田赋在改征白银之后出现空间赋税结构上的差异变化。田赋附加税中除去秋粮马草之外,各州县在改折白银前后从空间上来看均无改变的迹象,而是保持了恒定状态,其原因为折色农桑、丝绵折绢的折价皆为统一且固定的折银价,且自身原额较小,即便在改征白银之后,也会受制于其自身原额。田赋改折白银前后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夏税及秋粮中的麦、米及附加税马草三项。改折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这一时期的“京库地亩花绒”还并未进行改折,而是征收“本色”。其中马草的折银结果在实物定额阶段的各州县之间的定额分布差异过大;但马草在折银之后,各州县间的白银税额分布趋于平均。
其二,仓场在改折过程中尤为关键,各州县夏秋两税起运的仓场各有不同。在不同州县内,夏秋两税相同类型田赋的白银折价保持恒定,但各州县起运到各仓场的实物定额会存在差异,因而笔者推测明代政府在地方上将田赋改折白银的方式是通过调整州县田赋与仓场之间的分配关系进行银纳额调节。“不变”的是各州县夏秋两税“实物定额”仍然作为田赋改征白银的依据,折银后的田赋仍然需要完成“实物定额指标”;“改变”的是政府通过将不同州县的“本色起运定额”按照“赋税类型”及“征收数量”拆分之后,再分派到不同折价的仓场,进行银纳额调节。关于田赋的折银过程,笔者归纳了一个改折逻辑。一般情况下,本色田赋的折银过程为“A→C”,“C=A×Z”。[100]
其三,折色田赋在改折白银的过程中尤为重要,学界认为明代的田赋货币化改革历经了三个过程,即由征收实物到改折,由改折再到金花银的出现。而改折过程中出现大量折钞的情况,是赋税货币化的重要表现。在白银取得法定地位后,钞变为银。但在整个实物田赋走向货币化的过程中,实物原额一直存在,由实物到钞再到银,需要一定的比例进行转换。而无论是钞还是其他折色田赋都会被用来纳折并按照一定比例抵除实物麦米的额度。这个折银过程是在“折色田赋”按照一定的“比例”[101]完成“麦米额度”转换后进行的,即“A→B→C”,但其中“折色抵折本色田赋”的实征银额为“C=A×Z”[102]。在整个田赋改折白银的过程中,实物“麦米”定额成为折色田赋代征本色的抵折单位,这意味着实物定额(原额)从明初再到完成田赋白银货币化这一过程中是环环相扣,相互递进的。
其四,在学界之前的研究中,包括笔者在内的观点皆认为实物田赋的“额度数字”已成为一个定额和税收账册,笔者再度研究后认为,田赋折银这一过程会受到“自身原额”的影响,而如果“征收定额”或“实际征收额”的数量越大,受到“原额”的影响就越深。以“秋粮马草”“夏税钞折麦”“秋粮布折米”为例,这几项田赋在折银前后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基于庞大的“定额”之下,如不改变州县与仓场间的“分配关系”与庞大的“实际征收量”,或是过度抬高或压低折银价,这几项田赋在折银前后的结果都会保持一致。从夏秋两税的灵活性来看,夏税征收的灵活性要大于秋粮;夏税中本色改折色再征银的情况远多过秋粮,秋粮的征收则较为保守。另外,夏税与秋粮在改折白银之后,各州县与“临清广积二仓”及“兑军攒运米”的权重进一步提高,这意味着“起运到重要仓场的田赋”“通过漕运起运到中央的税收”在进行改征白银后,相较于“实物定额”阶段的税收结构,其重要性进一步提高。
A Study of Yanzhou County Tax Folding Silver 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Based on Spatial Visualization and Relational Network Analysis
Xu HaoMing, Liang Chen, Shang Ping
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it was difficult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operation of national finance. Since the 16th century, the Ming government initiated a series of fiscal and tax reforms that progressed from the local level to the national level and from the colle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the monetization of silver.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reform was to transform physical finance into a silver-based monetary finance,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In recent yea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 amount of tax in kind and the silver equivalent after tax deduction has been discuss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owever, the tax reform in the northern region of the Ming Dynasty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in detail. Yet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data preservation of Yanzhou Prefecture in Shandong Province are relatively complete.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e author employs 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HGIS) to visualize the collection quotas for physical goods such as summer tax wheat, autumn grain rice, and their additional taxes in 27 counties recorded in the Wanli Chronicles of Yanzhou Prefecture, as well as the figures converted to silver after the tax reform. The Gephi relationship network analysis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and sort out the allocation of land taxes assigned to different warehouses in each state and county, so as to deduce the relevant issues of “change” and “unchanged aspects” and “how to change” in the process of land tax reform in Shando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Ultimatel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tax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monetization of land taxes from a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 by analyzing the elasticity of the new and old tax systems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Keywords: Land Tax; Ben Se Tax; Zhe Se Tax; Silver Conversion; YanzhouFu
编辑 | 许可
[1]李园:《明代财政史研究中三种分析理论的构建与争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3期。
[2]“洪武型财政”的提出者为美籍学者黄仁宇,学界对此概念持续沿用并引发讨论。参见高寿仙:《为了变革而认识—黄仁宇对“洪武型财政”的病理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
[3]赵思渊、申斌:《明清经济史中的“地方财政”》,《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4]郭永钦:《明清钱粮考成定额化制度的形成与嬗变》,《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5]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8年,第86页。
[6]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18页。
[7]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5页。
[8]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81《食货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974页。
[9]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78《食货二》,第1894页。
[10]阎镇珩辑:《六典通考》卷66,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岳山房刻本,第8页b。
[11]万斯同撰:《明史》卷98,《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史部别史类,第325册,第615页上栏。引按:此段见于《续修四库全书》别史类中的《明史》,中华书局版《明史》并未收录。
[12]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78《食货二》,第1894—1895页。
[13]赵志浩:《明代田赋“折征”到“征银”的转变》,《北方论丛》2013年第1期。
[14]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71页。
[15]李义琼:《折上折:明代隆万间的赋役折银与中央财政再分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6]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09页。
[17]陈世昭:《明代一条鞭法问题研究》,《江汉论坛》1987年第7期。
[18]梁方仲:《明代银矿考》,《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9年第1期。
[19]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20]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第171页。
[21]万明、侯官响:《财政视角下的明代田赋折银征收—以〈万历会计录〉山西田赋资料为中心》,《文史哲》2013年第1期。
[22]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3]丁亮:《明代浙直地方财政结构变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24]春杨、汪思薇:《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25]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改革和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
[26]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241页。
[27]黄仁宇:《明代的漕运》,第101页。
[28]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26,江苏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478页。
[29]胡文彦:《十六世纪山东赋役的银纳化与再分配—基于〈山东经会录〉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史系,2021年,第14—18页。
[30]申斌:《明中叶米银双元核算下省级粮料再分派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2期。
[31]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付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65页。
[32]徐浩铭:《明代财政地理初探—以〈万历会计录〉中的起运、存留问题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23年,第71页。
[33]侯官响:《万历时期苏州田赋折银考—以〈万历会计录〉苏州资料为中心》,《明史研究》2017年第15辑。
[34]马铭遥、丁亮:《明代山东东昌府均徭役应役实态分析—以〈山东经会录〉为中心》,《兰台内外》2020年第24期。
[35]周振鹤主编,郭红、靳润成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53页。
[36]明山东布政司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编:《山东经会录》卷1,济南:齐鲁书社,2018年,第9—56页。
[37]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4《田赋》。(现存于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
[38]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14《田赋志》。
[39]明山东布政司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编:《山东经会录》卷1,第57—95页。
[40]万历二十五年《汶上县志》中秋粮米起运项折银7,525两,万历元年《兖州府志》中秋粮米起运项折银13,360.7两。
[41]指隆庆五年《山东经会录》、万历元年《兖州府志》、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
[42]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4下《田赋》,第3页a;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14《田赋志》,第28页a。
[43]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第6页。
[44]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14《田赋志》,第5页a。
[45]刘师少编著:《计算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46]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4上《田赋》,第17页b。
[4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7册,第50—51页。
[48]周振鹤主编,郭红、靳润成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第53—56页。
[49]峄县夏税、秋粮起运田赋改折白银前后都未发生空间上的变化,其夏税田赋改折白银前后均位于低起运税额区间,秋粮田赋在改折白银前后均位于中起运税额区间。
[50]滕县夏税、秋粮起运田赋改折白银前后都未发生空间上的变化,其夏税田赋改折白银前后均位于中起运税额区间,秋粮田赋在改折白银前后均位于高起运税额区间。
[51]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册,第54—55页。
[52]李乃强、徐贵阳:《基于自然间断点分级法的土地利用数据网格化分析》,《测绘通报》2020年第4期。
[53]夏税农桑折绢、丝绵折绢都有其固定且统一的折价——每匹7钱(0.7两),因此其实物定额折银乘以相同折价后,并不会使田赋附加税项的税收结构发生改变。
[54]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第172页。
[55]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第173页。
[56]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14《田赋志》,第58页b、第22页b。
[57]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78《食货二》,第1894—1895页。
[58]笔者通过对兖州府内所有附加税项统计发现,农桑、丝绵作为正项赋税中的附加税征收时,折银价皆为固定7钱(0.7两),但若作为折色折银则其折银价不恒定。
[59]谭希思撰:《明大政纂要》卷56,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南思贤书局刻本,第42页a。
[60]张学颜等撰:《万历会计录》卷1,《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史部政书类,第831册,第366页下栏—第368页上栏。
[61]隆庆《海州志》卷3《户赋》,第8页a—b。
[62]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78《食货二》,第1895页。
[63]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95,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1册,第835页上栏—下栏。
[64]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170,第2册,第1741页上栏—下栏。
[65]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14《田赋志》,第55页b。
[66]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江苏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91—92页。
[67]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第101页。
[68]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14《田赋志》,第41页a。
[69]申斌:《明代中叶以降赋役核算技术的演变》,《明清论丛》2018年第2期。
[70]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4上《田赋》,第14页a。
[71]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14《田赋志》,第6页a。
[72]详见下表7,兖州府境内仅有“登州府丰广二库”征收“钞”。
[73]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8年,第93页。
[74]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100,第2册,第886页上栏。
[75]光禄寺夏税征收“麦”,折银价为每石1两,秋粮征收“细粟”,折银价为每石1两。镇边城新城仓夏税征收“绵布”,折银价为每匹0.3两(3钱),秋粮征收“粟米”,折银价为每石0.9两(9钱)。
[76]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14《田赋志》,第32页a。
[77]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14《田赋志》,第46页a。
[78]姚广孝等修:《明太祖实录》卷56,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3册,第1089页。
[79]姚广孝等修:《明太祖实录》卷85,第4册,第1507页。
[80]姚广孝等修:《明太祖实录》卷88,第4册,第1569页。
[81]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14《田赋志》,第36页b。
[82]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185《列传第七十三·李敏》,第4894页。
[83]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14《田赋志》,第21页b。
[84]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4上《田赋》,第53页a。
[85]嘉靖《山东通志》卷8《田赋》,第10页b。
[86]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14《田赋志》,第53页b。
[87]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14《田赋志》,第53页b。
[88]张懋等修:《明宪宗实录》卷259,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6册,第4371页。
[89]姚广孝等修:《明太祖实录》卷88,第4册,第1568—1569页。
[90]张瀚纂辑:《皇明疏议辑略》卷8,嘉靖三十年(1551)大名府刻本,第24页a—b。
[91]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79《食货三》,第1924页。
[92]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79《食货三》,第1924页。
[93]刘斯洁撰:《太仓考》卷2,万历刻本,第31页b。
[94]黄仁宇:《明代的漕运》,第16—17页。
[95]刘斯洁撰:《太仓考》卷8,第12页b。
[96]其中数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前的单位为“两”,后为“钱”“分”。
[97]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14《田赋志》,第30页a。
[98]鲍彦邦:《明代漕粮折征的数额、用途及影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99]丁亮:《明代浙江正项田赋的银纳化考察》,《中国明史学会第十六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建文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377页。
[100]A为本色田赋实际的征收量,C为折银额,Z为本色田赋实际对应的折银价。
[101]前文提到,夏税中,折色田赋抵折“本色麦”的比例不恒定,该比例在0.1—1.2之间浮动。秋粮中,折色田赋抵折“本色米”的比例则为恒定的1:1。
[102]A为折色田赋中的绵布或钞、芝麻、豆的数量,B为各州县需起运到各仓场的本色麦米定额,C为折银额,Z为折色田赋实际对应的折银价。
基于空间可视化与关系网络分析下的明中叶兖州府田赋折银研究.pdf
如需购买《数字人文》期刊,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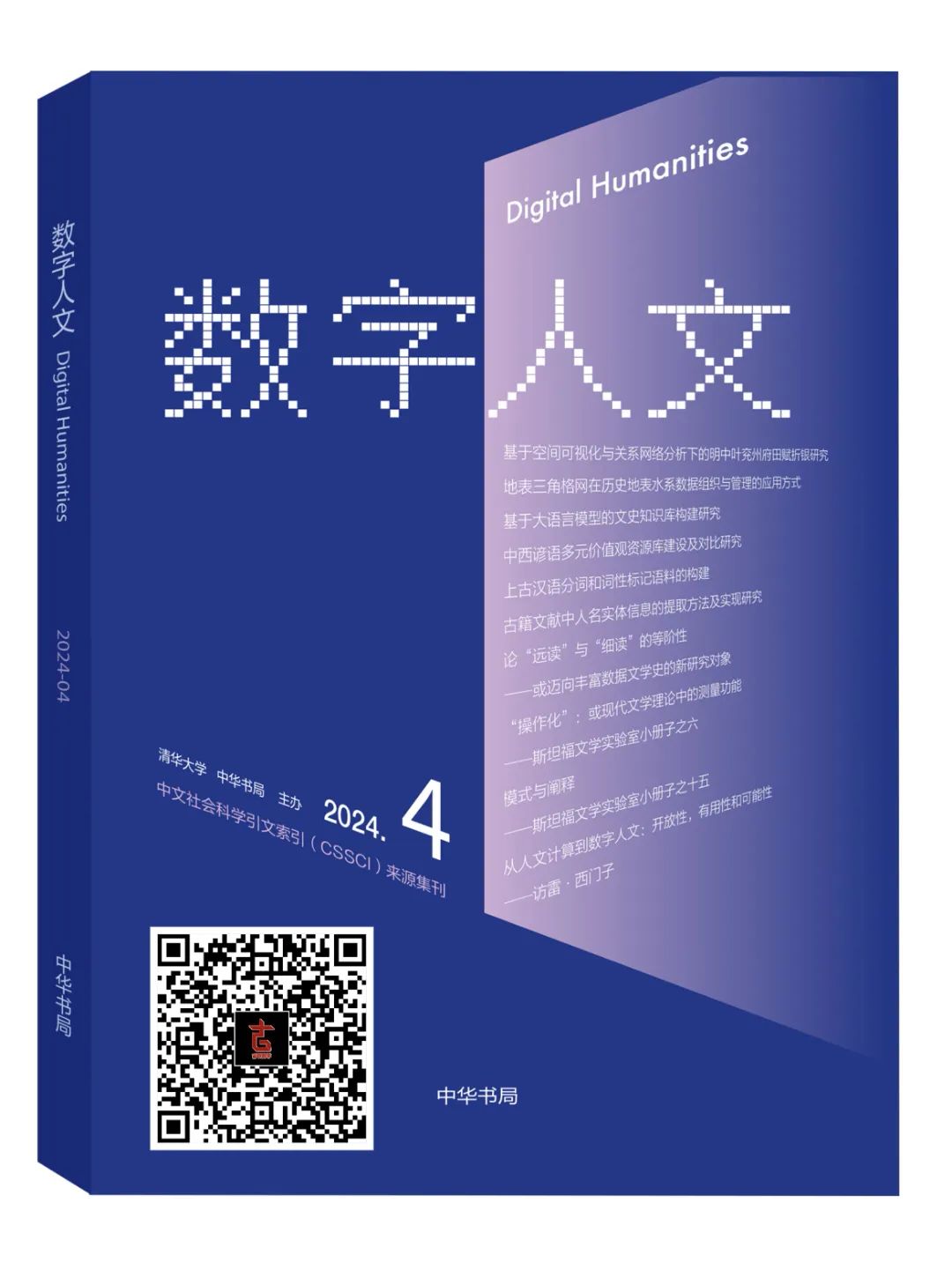
校对 | 肖爽
美编 | 王秀梅
往期回顾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DH数字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