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明时期,重型火绳枪通过欧洲人东来和商业贸易逐渐传入中国。在此过程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发挥了主导作用,而澳门葡人更是多次将重型火绳枪直接带入中国内地。与传统鸟铳相比,重型火绳枪枪管更长,弹药量更大,因此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很快引起明朝军政人员的高度关注。随着重型火绳枪的不断传入,晚明朝野掀起仿制与列装的热潮,由此衍生出以鹰扬炮、九头鸟、大追风枪、鹰嘴铳、斑鸠铳、翼虎炮、搬钩铳为代表的诸多名称,并被广泛应用到从沿海到内地、从辽东到两广的多种作战环境中,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晚明军队的火力水平。重型火绳枪的传入、列装,不仅改变了明朝军队的装备体系,而且影响到晚明时期的军事变革,是明清中国因中西交流而互动变革的实例之一。
关键词:重型火绳枪;斑鸠铳;大追风枪;晚明;葡萄牙
重型火绳枪是16世纪前期欧洲兴起的单兵火器。与此前流行的轻型火绳枪相比,重型火绳枪的枪管更长、口径更大,装填弹药更多,因而具有更大的杀伤威力。由于其枪体更重,士兵难以用手托举,因此发射时需要支架支撑。这种火器出现后,很快就被西方殖民者带到东方,并通过间接、直接两种方式传入中国。明朝方面也很快注意到了这种新型欧式火器,中央、地方乃至民间力量多有仿制,因此衍生出以鹰扬炮、九头鸟、大追风枪、鹰嘴铳、斑鸠铳、翼虎炮、搬钩铳为代表的诸多名称;装备区域则北至辽东,南达两广。重型火绳枪在多种作战环境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而成为推动晚明装备革新乃至军事变革的一种新因素。但学界以往对此问题关注极少。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重型火绳枪在晚明中国的传播、仿制与装备应用进行梳理,进而探寻其在中国军事史上的特殊意义。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教正。
一 欧洲重型火绳枪的东传与引进
重型火绳枪在欧洲出现后,很快就被装备到西欧国家的军队中,其在单兵装备中的占比逐渐提高。1567年起,在西班牙佛兰德斯驻军的一个tercio编制中,理论上2868名士兵装备重型火绳枪230支,占比只有8%。1636年后,每个连队189名士兵装备重型火绳枪30支,占比升至16%。1573年到1578年的尼德兰各连队,重型火绳枪占比在0到10%之间,平均不到4%。1587年到1601年,尼德兰的模范团,威廉·路易斯(William Louis)麾下的Frisian团,重型火绳枪占比已从13%提升到25%。1609年,尼德兰标准营级单位编有240名重型火绳枪手和250名长矛手,重型火绳枪手达到49%。重型火绳枪在西欧各国的大量装备为其向远东地区快速传播提供了必要前提。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在东来欧洲势力带动下,重型火绳枪相继亮相于中国周边,成为向中国传播的重要契机。
1586年,图谋侵略中国的吕宋西班牙人准备从美洲运来500支重型火绳枪。1598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恳请国王从西班牙输入400支重型火绳枪。1599年,他们再次请求国王调集500支重型火绳枪。1617年6月26日,一艘载有100支重型火绳枪的船只抵达甲米地。由此可见,重型火绳枪已成为西班牙驻菲律宾殖民军队的一种常见武器,其占比提升趋势与欧洲大陆基本一致。不唯如此,重型火绳枪的装备范围还从西班牙殖民者扩展到了菲律宾当地人。1603年,为了镇压吕宋华人的反抗运动,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心为邦板牙等地的菲律宾当地人装备大量轻重火绳枪。这些流入菲律宾的西班牙重型火绳枪有可能通过中菲贸易往来流向中国。
荷兰人是欧洲重型火绳枪东传的重要媒介,他们在殖民远东过程中大量使用了重型火绳枪。1622年6月,荷兰以重型火绳枪投入其与葡萄牙之间的澳门争夺战。同年11月,荷兰人在福建沿海以70名重型火绳枪手洗劫一个中国村庄。1626年,荷兰人以重型火绳枪介入台南麻豆社与新港社之间的内斗。1629年夏,荷兰台湾长官纳茨(Pieter Nuyts)派出60多名士兵,围剿麻豆社的中国海盗未果,返回时为方便渡河,荷兰士兵将手中的重型火绳枪交给当地麻豆社人保管,而麻豆社人旋即杀死了这些荷兰士兵。这次事件被荷兰人称为the Mattauw massacre(麻豆社大屠杀)。为了鼓励戎克船与自己合作,1625年3月2日,荷兰人曾将50磅火药、20磅子弹、7支重型火绳枪和3束火绳送给中国人。明末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称,荷兰人“每登陆,各执鸟铳一门,铅子每粒各重一两”,更番打放,实为劲敌。
重型火绳枪东传中国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最早来华的葡萄牙人,是他们最先让中国人见识到重型火绳枪的威力。1582年,一艘失事船只的葡萄牙船员向台湾西拉雅人展示了重型火绳枪,令他们大为惊诧。在澳门,重型火绳枪已较多装备于驻澳葡军中。当时澳门的葡萄牙连队由125名士兵组成,其中重型火绳枪手60名。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葡澳士兵误杀官军何若龙等,引起中葡交涉,延至当年九月,葡萄牙方面向广东当局交出凶犯6名,并“番哨船一只、大铳五门、鸠铳七门”,以及药弹、红旗等物。这进一步证实澳门葡萄牙人确实装备了重型火绳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驻澳葡萄牙人在崇祯年间才将更多重型火绳枪不断输往中国内地。
崇祯元年(1628),崇祯皇帝命两广总督李逢节向澳门葡人购置火炮,招募铳师。葡澳当局派公沙的西劳(Gonsales Texeira)、陆若汉(Joao Rodrigues)统领铳师、傔伴三十余人,携带“大铁铳七门,大铜铳三门,鹰嘴铳三十门”,于崇祯二年(1629)二月从广州出发,沿水路北上。其中的鹰嘴铳就是重型火绳枪。途经徐州时得到徐州知州韩云资助,公沙赠送火绳枪一支以作答谢。这批武器历经曲折,终于在崇祯三年正月初三(1630年2月14日)运抵北京。这是葡萄牙人第一次成批次地将欧洲重型火绳枪运往内地。
在这批重型火绳枪运抵北京不久,鉴于辽东形势再度严峻,公沙的西劳、陆若汉建议明朝再从澳门募兵,计划招募铳师、艺士200名,傔伴200名,“令彼自带堪用护铳、盔甲、枪刀、牌盾、火枪、火标诸色器械,星夜前来”;他们听说两广总督王尊德已从澳门借得大、小火器20门,“照样铸造大铁铳五十门、斑鸠铳三百门”。当时正在中国传教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也说:“现在,中国官员找葡萄牙人在澳门制造许多火器,Muskets开始进入中国。”因为重型火绳枪特受重视,公沙的西劳、陆若汉还特别提议,所募葡萄牙军士除自带前项军器外,还需在粤采买鹰铳200门、鸟嘴护铳1000门、西式藤牌5000面、刀1000口、长枪1000杆、短枪1000杆。这里的鹰铳当为鹰嘴铳的略写。崇祯皇帝准其所请,谕令广东方面备齐一切必要装备,星夜伴送来京。据曾德昭《大中国志》记载,这支军队从澳门抵达广州时,“很气派地进行检阅,用他们的Musquetrie致敬,使中国人惊奇”,看来还是自带了一些重型火绳枪。这支雇佣军从广州出发,最后到达南昌,嗣因朝中有人反对,不得不自南昌折返。
葡萄牙雇佣军的北上计划虽然夭折,但为配合这次行动采买的兵器还是运到了北方。据崇祯四年(1631)八月的一份档案记载,兵部在当月二十七日上了题为《兵部为闻风愤激直献刍荛再图报効事》的题行稿,是对此前陆若汉、公沙的西劳募兵建议的最后回应。题行稿称,广东管解西洋兵器官林铭、马宗舜,于崇祯三年十月内,“蒙巡按广东御史高批差,领揭一封,管解鹰铳二百门、鸟嘴护铳一千门,并各合用事件,藤牌五千面、刀一千口、长枪一千杆、短枪一千,红炉铜铁牌木各匠共二十五名,前赴兵部投交”。这批从广东起运的兵器名称、数量及前后顺序,与前述公沙的西劳、陆若汉奏疏完全一致,显为配合前项募兵计划而采买的广东兵器。林、马二人在运送途中接到将该批兵器转运登州的新指示。二人遂于崇祯四年六月十五日,将“班鸠铳二百门、鸟铳一千门……及放铳事件”,交由登莱巡抚孙元化查收。值得注意的是,该件题行稿前作“鹰铳”,后作“斑鸠铳”,再联系前文之“鹰嘴铳”,可见“鹰铳”或“鹰嘴铳”“斑鸠铳”,都是对同一种葡萄牙重型火绳枪的不同称呼。据此似可勾勒崇祯初年两批重型火绳枪由葡萄牙人传入中国内地的大致过程。
二 晚明所见中国重型火绳枪
欧洲重型火绳枪传入中国后,很快引起明朝军政人员的高度重视,他们从各个角度介绍重型火绳枪的技术特征和强大威力,或吁请仿制装备,或进行军事实践,因此在晚明朝野之官私文献中留下有关重型火绳枪的诸多图文记录。见于晚明文献的重型火绳枪主要有鹰扬炮、九头鸟、大追风枪、大鸟铳、鹰嘴铳、斑鸠铳、斑鸠脚铳、翼虎炮和搬钩铳等,其中以大追风枪和斑鸠铳最为典型。
赵士桢《神器谱》记载的鹰扬炮是最早著录于晚明文献的重型火绳枪。该炮吸收了佛郎机的后装特征,专为压制侵朝倭军之大鸟铳而设计。以日本大铁炮为代表的重型火绳枪一度威力巨大,其弹重甚至超过西班牙重型火绳枪,因此给中朝军队造成不小困扰。为了对付大鸟铳,赵士桢设计鹰扬炮式重型火绳枪,该炮将佛郎机和火绳枪的技术优势融为一体,“用长筒加厚,仍著照门、照星,纳子铳于筒后,不令敞口泄气”,射击速率比肩佛郎机,精准度媲美大鸟铳:“对垒之际,敌一举放,我已三四发弹,是以便胜之也。若置轻车之上,有车数两,陆续冲击,猛烈之势,足埒大将军,而离合纵横,进退俯仰,较大将军殊为轻便”,填补了轻型火炮与鸟铳之间的火力空白。鹰扬炮既可以在架上施放,也可以在藤牌、挨牌掩护下射击。架上施放时,一人负责装填子铳,一人负责瞄准射击,由此循环往复,保证了火力的连续性。以藤牌掩护时,鹰扬炮置于藤牌手肩上,射手以跪姿射击,另有一人装填子铳;如以挨牌掩护,则以立姿射击。其后茅元仪《石民四十集》所载“子母追风枪”之设计思路与此相近,只是它配备了九枚子铳,射击速率更高。
除鹰扬炮外,《神器谱》还记载一种名为“九头鸟”的重型火绳枪。赵士桢说,九头鸟就是重达二十余斤的“绝大鸟铳”,“用药一两二钱,大弹一个,小弹钱许者九个。遇敌冲我,人众则乱打,人少审定而放,尤宜夜战”。这种以一颗大弹配合多枚小弹的装弹方式,已和明军广泛装备的轻型火炮类似。据该书《放九头鸟图》所示,施放九头鸟时需二人配合,射手将铳置于副射手即“背铳兵”的肩上,采跪姿射击;施放完毕后“背铳兵”就用三眼铳射击,以掩护射手的二次装填。
大追风枪之著录稍晚于鹰扬炮和九头鸟,最早见于温编《利器解》。大追风枪“式长四尺四寸,重十八斤,除四尺四寸外,后长五寸入柄内,柄长一尺九寸”,下用“三足铁柱”支撑;发射时由两名士兵共同操作,“一名执枪照准则,一名执火绳”;由于枪管较长,所以“发而能远”;每出“用药六钱,铅子一枚重六钱五分”,平射射程二百余步,抛射射程十余里,被誉为“万胜难敌之长技”。大追风枪铅子重量超过三钱鸟铳一倍还多,而且枪管更长,这赋予了弹丸更大的动能,不仅射程更远,而且威力惊人。大追风枪在明代兵书中屡见不鲜,后出之《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三才图会》《武备志》《师律》等书,所记与《利器解》基本一致。而毕懋康《军器图说》记载的“追风枪”除体型略小外,其他情况亦基本一致。范景文《战守全书》记载了另一种与上述明显不同的大追风枪,此枪由辽将彭簪古制造,身长八尺,连柄一丈,射程可达数百步。该枪对枪机部分进行了简化,省去了复杂程序,所以“人人能放”,“比鸟铳甚便”。
何汝宾《兵录》记载了西洋大鸟铳,其身长四尺,铳管嵌于木柄之上,“用铁作半圜,下总一铁柱,绾在铳木柄中央,复用木直竖受铁柱,左右顾盼,照准施放”;铅弹重量在一两二钱至一两六钱之间,“弹作三分,用药止二分”,“如弹重一两二钱,作三分,用药二分,止该八钱。余仿此”“平放二百步,仰放一千步”。西洋大鸟铳弹重是普通鸟铳的四到五倍,装药量是其二至三倍,威力自不可同日而语。
但晚明最为典型的重型火绳枪还是多见于崇祯时期的斑鸠铳或斑鸠脚铳。明末档案《兵部行两广总督军门坐班承差廖宗文呈稿》,对崇祯八年(1635)两广总督熊文灿运至北京的100门斑鸠脚铳进行了细节描述:“每门连木靶重二十六七斤不等,除木靶重十五六斤不等”,“身长四尺二寸,连靶共长五尺五寸”,“用药一两三钱,空放一次复装药,用铅子一个重一两五六钱不等”。崇祯十年(1637),熊文灿再运斑鸠铳100门、大鸟铳100门;其大班鸠脚铳每门用药一两五钱,大鸟铳用药三钱,“俱各精好堪用”。这里的斑鸠脚铳即使与欧洲重型火绳枪相较,亦属大型。此外,其枪管前拿后丰,既可有效避免炸膛之虞,也减轻了整枪重量,是当时较为先进的设计。
翼虎炮是毕懋康《军器图说》记载的又一重型火绳枪。此炮“式长三尺,重六十斤。除三尺外,后一尺六寸入柄内。柄长二尺二寸”“其制有柄,有架,有铁嘴插入木架圜中,对敌举放,临时可游移上下,或平架放去,或稍昂其首,无不宜之”。据说翼虎炮最早出现在陕西榆林地区,曾与追风枪一道,作为震慑蒙古来使的军中利器。因其威力在诸炮之上,“故以翼虎名之”。每次演放,蒙古使者“为之啮指”。郑大郁《经国雄略》记载了明末最后一种名为“搬钩铳”的重型火绳枪。其名或为斑鸠铳的讹读。郑大郁说,搬钩铳为“鸟嘴之最大者”;“此铳用之舟战,极为利便。火药一发,杀人于百步之内外者,此铳得之矣”。与大追风枪、西洋大鸟铳和斑鸠脚铳一样,搬钩铳也有一个支撑铳体的支柱。所不同者,前者为铁柱,搬钩铳为木柱。
三 晚明重型火绳枪的仿制与应用
与轻型火绳枪相比,重型火绳枪枪管更长,弹重更重,用药量更大,因此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由于整枪重量显著增加,士兵单手托举已很困难,发射时往往需要支架或者架在另一战士的肩膀之上,使其射击更加稳定。重型火绳枪的这些技术特征受到明朝方面的高度重视,在一些军政人员的呼吁推动下,中央、地方乃至民间力量掀起仿制、列装的热潮,许多重型火绳枪开始应用到从沿海到内地、从两广到辽东的多种作战环境中,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晚明军队的火力水平。
如前所述,赵士桢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就已研制出鹰扬炮式重型火绳枪,并且介绍绝大鸟铳九头鸟,稍后之《利器解》中也已著录大追风枪,但其受到明朝军政人员的普遍重视,应该是在辽、沈失守以后。天启二年(1622)正月,协理京营戎政右佥都御史李宗延上言,辽东形势日益严峻,京师防御尤当加意,京城之外旧有九营,当为设置营车,“车中实土,上列水桶,中载追风、翼虎等炮,毒箭、弩弓等器,大约五层,可放十次”,“营有此而后可以无望尘奔溃之虞也”。天启三年(1623),兼理戎政兵部右侍郎余懋衡指出,火器乃中国长技,但京营装备之三眼枪等“筒短力薄,及远未能”,建议军兵“多习追风炮与佛郎机”。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一些人的响应。翰林院庶吉士蒋德璟在馆课《京军考》中写道,“车战则莫如佛郎机”“凌空则莫如追风炮”,呼吁“妙选名师,以一教十,转相仿授”。巡视京营给事中彭汝楠也强调,京营火器以三眼枪居多,“而力或不能及远”,“惟追风炮最强,宜加意明习,以备奋击”,天启皇帝令兵部讨论执行。
在辽东、贵州等京师以外的其他热点地区,推动仿制、装备重型火绳枪者亦不乏人。如天启二年八月出任辽东督师的孙承宗,十分看重追风枪在城池防守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追风枪“质小无震动之虞,而节长有远驭之势”,诚为守城利器,因此呼吁工部“取两厂不堪夹钯枪、五龙枪、快枪等项三万杆,运关改造追风枪”。在致户部尚书李宗延信中,孙承宗要求朝廷速将制造好的子母追风枪查验配发,以济关城急需。而天启四年(1624)就任贵州巡抚的蔡复一,也将翼虎炮、追风枪视为“制胜利器”,设法就地打造。
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使明朝面临更加严峻的内外形势。面对后金方面的咄咄攻势,徐光启呼吁多造大号鸟铳。在崇祯二年十一月的《计开目前至急事宜》疏中,徐光启指出,“凡守城,除城威大炮外,必再造中等神威炮及一号二号大鸟铳,方能及远命中”,而野战“尤须中铳及大号鸟铳”,目前“须造中炮五十位,大鸟铳二千门”,“若欲进剿,再须中炮百位,大鸟铳五千门”。十二月初九日,徐光启在《再陈一得以裨庙胜疏》中写道,破敌之法必须车营,“法当用二号西洋铳五六十位重千斤以下者,又须新造大鸟铳二三千门长四尺五寸以上者”,要在二十日内“鸠工攒造大号鸟铳”,并令广东、福建“速造长大鸟铳解用”。同月二十二日,徐光启又上《破虏之策甚近甚易疏》,疏中强调“战阵所急,无如鸟铳”,“宜纠工急造大号鸟铳,至少亦须千门”,“此为后来千百年之用,不但今日”。短短两个月里徐光启三次呼吁,足见其对装备重型火绳枪的高度重视。在崇祯四年规划的15个精锐车营中,徐光启计划每营装备“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此等鹰铳即鹰嘴铳。
崇祯七年(1634)由南京通政使陪推兵部右侍郎的毕懋康,凭着崇祯皇帝赏识获任新职,旋以争执边事告归。陛辞之日,毕懋康上《微臣去国积忱未撼》疏,朝廷命其“制造军器,并书进览”;八年,“所制军器及武刚车、神飞炮等成,并辑图说疏进。上御西苑观德殿临试,发部储用”。在所进《军器图说》序中,毕懋康指出,火器名色300余种,但军中实用者“不过数项”,其中“有打放极准,所击人马洞穿,而名为鸟铳、追风枪者,此小器之最利也”,“有打放极便捷,一人执之,可毙伯什人,用以冲锋破阵,而名为翼虎炮者,此中器之最狠也”。鉴于翼虎炮的强大威力,毕懋康建议每营都要装备:如将数十架置于阵前,“分作十数层,次第发之,再以数位分架两翼,或桥口,或田塍,或津渡,敌可往来之处,如法备御,贤于数万精兵矣,奚患冲突哉”!如果是在西北边塞,则当以万架计算,“旷野平原,动以百数为一层,次第举火,稍近即用各色火箭,接续不断,虏虽众悍,安能当此”!
但在晚明诸多名称的重型火绳枪中,仿制应用者多为追风枪、翼虎炮和斑鸠铳。追风枪的制造、应用当不晚于《利器解》成书时。据温编《利器解序》,武官朱腾擢与其长兄温纯好谈火器,已然构成《利器解》的知识来源。因为学有专长,朱腾擢曾被推荐到宣府巡抚王象乾麾下制造、试验火器火药;后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加衔守备,在辽东巡抚赵楫标下“专管打造、教练全镇火器事务”,惜未明言所制火器为何。万历三十六年(1608),延绥巡抚涂宗潜聘请朱腾擢改造本镇火器,“朱腾擢将贮库火器一一试验讲求”,“随营灭虏、涌珠等炮皆改轻便,百子铳、大追风、小神枪创新制造”。可见在朱腾擢的主持下,延绥镇已新造一批大追风枪。次年十二月,蒙古河套部落入犯,延绥总兵张承胤发兵掩击,“火器游击朱腾擢用新制循环、追风、神枪等炮,设伏在傍,连发打死贼众无算”,大追风枪威力初显。辽阳失守后,明军在辽东前线装备了更多大追风枪。如王在晋担任辽东经略期间,造有各式火器,其中包括追风铳、鸟铳等火绳枪制式武器。天启二年十二月,在蓟辽总督王象乾练成的一个密镇车营中,追风鸟铳居于各类单兵火器之首。孙承宗第一次就任辽东督师时,先后在军器局外置造大追锋枪173杆,并委托山西分造大追锋炮338门,此外还有江南地区新造追风枪1000杆。在天启六年(1626)正月的“宁远大捷”中,袁崇焕部“以红夷、将军、灭虏炮、鸟铳、追风、弓箭打死夷贼数万”,这是包括重型火绳枪在内的西洋火器实战发威的一个显例。
翼虎炮的制造、应用虽然无法媲美追风枪,但在多地仍有可观表现。如前述贵州巡抚蔡复一致郧阳巡抚毕懋康信中提到,自己已从荆州带来翼虎炮、追风枪工匠数名,但都技术平平,希望能从徽州、浙江物色良工,开炉鼓铸。据此,湖广荆州、贵州贵阳在天启时期都曾仿制过翼虎炮和追风枪,徽州、浙江一带的制造技术或许更加成熟。崇祯八年,张献忠农民军进攻滁州,南太仆寺卿周鼎捐资数百金,“差标员冯文正监制造翼虎炮、鸟铳,又车载大炮及硝黄等药至滁”,巩固了滁州城防。崇祯十一年前后,南京兵仗局奉命制造翼虎炮,仅应天一府额外例派之工价银就有二千七百两,可见规模不小。崇祯中出任歙县知县的傅岩,亦曾捐资制造“翼虎炮八门”。而在辽东前线,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到天启元年(1621),仅在工部发往辽东的武器清单中,就有翼虎炮110门。此后,还有更多工部、兵部制造的翼虎炮被运往辽东。如天启二年正月,工部主事沈棨将一批精制绵甲、翼虎炮等运至前线;十月,孙承宗恳请将战车厂和山西地区制造的翼虎炮尽数发往山海关外;天启四年五月,户部带运兵部接济皮岛毛文龙部翼虎炮100位。在天启初年的辽西西平堡战役中,翼虎炮曾“击毙虏贼无数”,立下赫赫战功。
除前述两款重型火绳枪外,明末仿制、列装最多的当属斑鸠铳。明朝第一次批量仿制斑鸠铳是在崇祯二年稍前。为剿灭海寇,时两广总督王尊德“仿澳彝式制造班鸠铁铳三百具”。崇祯三年,为配合在澳招募葡人雇佣兵的计划,明朝在广东地区一次采买粤制斑鸠铳200门(此事已见前文)。此后广东方面制造斑鸠铳的事例还有不少。如崇祯四年,两广总督王业浩在肇庆制造独弹斑鸠铳350门;崇祯五年(1632)十月,两广总督熊文灿差肇庆卫经历祝锡祯造斑鸠铳,“贮库待用”。崇祯九年(1636),广东海北兵巡参议张国经在廉州府“铸班鸠铳三拾肆口、大全身班鸠铳九个”。崇祯八到十年,兴宁知县刘熙祚制造班鸠、百子等铳大小25门。崇祯十五年(1642),郑芝龙拟造大、中水船各20只,装备大、中斑鸠铳640门,广东方面委托掌印都司马吉翔照数制造。崇祯十六年(1643),郑芝龙在福建打造多款火器,但“铁烦、扳鸠等铳,在粤制造”,且很快“可以解到”。
迟至南明初期,广东方面还在大规模制造斑鸠铳。据黎遂球《莲须阁集》记载,福王政权建立后,曾向广东征调火器。遂球闻之,率先捐资,“制斑鸠铳五百门”。而此次捐造者尚有不少。如某位广东官员之弟诸生某某,“随偕诸绅士先后,咸以义动,而黄君则又率诸生某等各蠲制如之”。据黎遂球之《上署县陆公》,此次广东方面仿造的斑鸠铳多达三千余门。
除广东地区外,其他地区亦多有仿制者。如因海寇猖獗,福建巡抚熊文灿于崇祯二年捐俸制造“福字号斑鸠铳数万”。崇祯三年,徐光启计划在京新造斑鸠铳200门,随后“造完大小三十门。其余铳筒已完,机床未备,通候讫工之日,进呈奏缴”。崇祯八年,耿廷箓就任南直庐江知县,所备班鸠铳“床管如噜密铳,而摧坚及远倍之”,令人印象深刻。崇祯十一年就任江西清江知县的秦镛,在任时造班鸠铳四门。崇祯十六年,山东莱阳知县关捷先造班鸠炮20位。而在南直隶嘉定县,启祯间所造军器多达23763件,到顺治十三年(1656)时,仍存磨盘红衣炮40位、佛狼机109位、班鸠鸟铳59门等不少西式火器。
斑鸠铳被较多装备于战船之上。以广东为例,崇祯十二(1639)、十三年(1640)担任广东岭西兵备佥事的冒起宗在其《莲头寨港图说》中记载:“海船火器,莫过班鸠铳”,但莲头寨现存斑鸠铳仅有14门,“尚不及海(朗)、双(鱼)二寨一船之器,计非增造五六十门不可”。这就表明,海朗、双鱼二寨水军当时装备了大量斑鸠铳。据载,两寨各有兵船12只,以每船至少14门计算,则两寨兵船至少装备了336门斑鸠铳。而身处福建,与荷兰人、葡萄牙人多有交集的郑芝龙,也很重视斑鸠铳的装备问题,前述郑军水船船与斑鸠铳的结合,应是一个成功范例。但不局限于战船水战,斑鸠铳在陆战中也能克敌制胜。如崇祯五年二月,广东琼崖参将李相会同福建、南赣方面围攻农民军首领钟凌秀,“贼抵班鸠铳不过,即溃散奔逃”。前述一些在北方、在内地制造的斑鸠铳,当主要应用于陆战之中。
四 互动变革中的晚明重型火绳枪
重型火绳枪的传入、仿制与装备应用,是明朝后期中西互动在军事装备领域的又一重要成果,体现了晚明军政人员对海外最新火绳枪技术的好奇敏感与借鉴利用。如前所述,赵士桢鹰扬炮式重型火绳枪兼具佛郎机与大鸟铳的技术特征,既有日本大铁炮的外在刺激,又有欧洲火器术的技术启迪,互动烙印明显。与赵士桢之鹰扬炮一样,温编大追风枪也有来自海外的技术传承。韩霖曾经指出,火器虽为小技,亦需兼通格物度数之学,“未有不由师传,顿臻神解者也”;他进一步明确,赵士桢最精鸟铳,所著《神器谱》,“授之者,游击将军陈寅、锦衣卫指挥朵思麻也”,“三原温恭毅有《利器解》,授之者,材官赵世登、朱腾擢也”。温恭毅即温纯,陕西三原人,温编长兄,卒谥恭毅。
而朱腾擢的火器知识似乎也是来自陈寅与朵思麻。清人钱曾《读书敏求记》著录《火器大全》一卷,“未知撰自何人,称李承勋、朱腾擢、赵士桢,皆负笈其门,随才授艺”。晚清经学名家孙诒让推测,若以《神器谱》考之,“彼书或出陈寅及朵思麻手也”。陈寅是万历时期热衷西洋番鸟铳的京营武官,朵思麻曾将土耳其噜密铳技术传给赵士桢。他们的火器知识都是来自西方,朱腾擢大追风枪的技术渊源也就不言自明了。
辽将彭簪古所制大追风枪则与澳门葡萄牙人有一定关系。民国《万载县志》引旧志云,彭簪古以文好武,喜谈兵法,“天启壬戌赴京,适兵部选将材,因就试,授京营把总,奉拨炼火器,教习先锋”。范景文《战守全书》载,天启中,澳门葡人将得自英国沉船上的二十四门西洋大炮运至京师,“时令袁州人彭簪古车营军五十人习之”。随炮而来的还有“深知火器铳师、通事、傔伴,共二十四名”,他们于天启三年四月抵京,“在京制造火药、铳车,教练选锋点放”。天主教徒韩云也说,来自澳门的西洋铳师负责“制造火器、铳车,教练选锋,点放鸟铳”“咸能弹雀中的”可见,在葡萄牙铳师的教导之下,彭簪古等接受了包括大炮、鸟铳制造、点放,以及火药配制方面的系统培训,并且取得不错成绩。因为技术过硬,督师孙承宗将彭簪古从京营调往山海关,后来再调宁远。在天启六年的宁远之战中,彭簪古以西洋火器击败努尔哈赤,因功加授都督职衔。彭簪古的这些经历,使其能够仿制“大于鹰嘴铳”的大追风枪。
得益于澳门葡萄牙人,崇祯初年广东方面第一次大规模打造斑鸠铳。崇祯二年,两广总督王尊德从澳门借得大小各式西洋火器,招募工匠,“照样铸造”,成功仿制“澳彝式”斑鸠铳300门。这次大规模的仿制行动,为广东方面培养、储备了一批火器工匠,此后广东地区能够不断仿制数量可观、质量过硬,并能驰援京师、协助邻省的重型火绳枪。南明福王时期广东方面又一次大规模制造斑鸠铳,亦可见到海外技术的影子。据载,负责此次造铳任务的是广州市舶提举姚生文。职使所关,这位市舶提举当与来华西商尤其是葡萄牙商人有着较多联系,所以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仿制重型火绳枪的必要技术。此人后来署理新会县事,再迁广州海防同知。由他打造的三千多门斑鸠铳,居然成为明末大规模仿制重型火绳枪的最后绝响。除此之外,福建处于对外交往的前沿要冲,在与西方殖民者的交流互动中,易于获得欧洲最新火器技术,以熊文灿、郑芝龙为代表的福建文武官员就能仿制一定数量的重型火绳枪。至于徐光启在京新造斑鸠铳,则完全是在葡萄牙铳师帮助下完成的。
重型火绳枪的装备应用,有效提升了晚明军队的火力水平。第一,穿甲威力显著提升。赵士桢称日本大鸟铳“似非牌甲可御”,兵部赞广东解京斑鸠铳“果可摧坚破锐”,说的也是这一点。面对“虏多明光重铠,而鸟铳之短小者未能洞贯”的火力困境,徐光启呼吁制造大号鸟铳,也是看中其“可以洞透铁甲”的火力优势。据此可知,重型火绳枪的列装为晚明军队提供了一种几乎可以对付所有盔甲的单兵火器,大大提高了明军应对敌方重装部队的能力。第二,增强了晚明城堡的防御能力。明军依托城墙可以有效避免重型火绳枪体重难举、机动性差的劣势,充分发挥其威力大、射程远的长处。彭簪古之大追风枪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该铳架于城垛之上,“比鸟铳甚便,守城宜用”。孙承宗也指出,追风枪“无震动之虞”,又有射程优势,确为“守城利器”。第三,追风枪与战车的全新配置,为晚明车营提供了一种布设更为灵活的重火器。协助孙承宗组建辽东车营的茅元仪说:“轻车之上,更得子母追风枪而捷。”在其规划的辽东车营中,每车装备1杆子母追风枪,一营共装256杆;轻车营每辆偏厢车装备2杆,一营共装336杆;海舟轻车营则每车装备3杆,一营共装384杆。车营追风枪与佛郎机高低搭配,部分取代了三眼铳的原有功能。在实战中,子母追风枪手“内以半司高丽牌,出则以半执追风架”,既可在战车内施放,也可前出架设,这是佛郎机无法做到的。由是观之,战车搭配重型火绳枪后,对一线步兵的火力支援更加直接有力。第四,提升了水师战船尤其是较小型战船的火力水平。前述郑大郁称搬钩铳“用之舟战,极为利便”,朝鲜人说大鸟铳“最关于舟师及守城之用”,以及广东海朗、双鱼二寨水师战船和郑芝龙水船船之大量配备斑鸠铳,可证中朝水师对于这种武器的高度青睐。在水船这类小型战船上,斑鸠铳的优势展露无遗。一艘水船船可以配备多达10—20门斑鸠铳,而同等体量的战舰往往只能装备数门佛郎机炮。凭借较明显的数量优势,且每放一次“用铅弹四枚”,其杀伤面积比佛郎机更大,因此成为更有效的水师近战武器。
重型火绳枪的装备应用,也是明代军事深度变革的一个缩影。随着重型火绳枪等欧式火器的引入列装,晚明军队的编制体制变得更加复杂,战略战术出现新调整,新军事观念不断涌现,从而刺激了晚明兵学的勃兴繁荣。同时冷热兵器更新迭代的步伐明显加快。据西班牙籍多明我会士帕莱福(Juan de Palafoxy Mendoza)记载,南明军队在与清军交战过程中,以重型火绳枪为代表的先进火器取代了传统弓矢,不少士兵成为技术娴熟的火枪手和炮手。而从世界范围看,14-17世纪欧洲军事强国的步兵单兵火器,大体经历了14-15世纪火门枪、15世纪末16世纪初火绳钩枪与火门枪混用、16世纪中后期轻重火绳枪混用、17世纪初统一为相对更轻的重型火绳枪,以及17世纪后半叶重型火绳枪与燧发枪(flintlock)混用并最终为燧发枪取代五个阶段。由于东西方军事传统与装备体系的诸多差异,我们不能将明清中国的军事实际与这五个阶段硬性对应,但晚明重型火绳枪的传入、仿制与装备应用,填补了中国传统火器体系在这一阶段的空白,使得中国在17世纪初期并不落后于世界先进潮流。
五 结语
重型火绳枪的传入、仿制与装备应用,是晚明中国在与西方世界互动中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新航路开辟后中西军事文化交流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没有他们间接或直接的接续传播,欧洲重型火绳枪东传中国的进程无疑会大大延后。而晚明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内外形势,尤其是来自北部沿边、东部沿海和西南内陆的安全压力,决定了晚明朝野对拥有显著技术优势的欧洲重型火绳枪有着较为迫切的现实需求,这是晚明军政人员在军事实践中的自觉选择。与明朝原有的轻型火炮相比,重型火绳枪重量更轻,后坐力更小,使用更加安全可靠;与其他单兵火器相比,其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可以更有效地毁伤敌人的强固目标,因此弥补了晚明装备中轻型野战炮与鸟铳等轻型单兵火器之间的火力空白,促成明军火器装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整体效能的进一步提升。伴随各式重型火绳枪的列装、应用,它们在支援步兵、把守城隘、海上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低估。在车营中,重型火绳枪既可像佛郎机一样作为战车之固定火力进行防御作战,又可随步兵小队前出突击,直接以火力支援执行防守反击或有限攻势任务的轻步兵;在城守中,重型火绳枪作为轻重火炮的有益补充,常被用于城门等要害之处,因而成为城守利器;在战船上,重型火绳枪则在远距离狙击敌人,以及近距离接舷、跳帮战斗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于此可见,重型火绳枪在晚明中国的装备使用,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当时的作战形态、影响到了战争进程,这是晚明时期基于中西互动而逐步展开的广泛军事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欧洲重型火绳枪在晚明中国的传播为切入点,重新审视新航路开辟后中国军事历史的发展演变,深入探讨明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在军事技术层面的交流互动,系统分析晚明时期军事变革的复杂动能,进而揭示晚明军事历史的诸多深层问题,对于更好认识晚明中国与时俱进的应变、转型与活力,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文献来源
《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2期。文中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
Museum
李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图为庞乃明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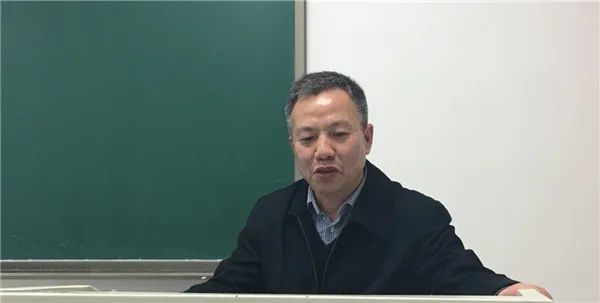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明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