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海洋史研究》23辑(大西洋史专辑)联合主编张烨凯博士
一
自二战以来,大西洋史在欧美学界已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专门研究领域。它兴起于二战后、壮大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趋势。领域的成熟与多元化也促使研究者对其展开一系列批判性反思。2002年,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大西洋史的三个概念》一文中从地理空间角度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此后,包括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艾莉森·盖姆斯(Alison Games)、威廉·奥莱利(William O’Reilly)、菲利普·D. 摩尔根(Philip D. Morgan)、杰克·P. 格林(Jack P. Greene)、等一批学者回顾了大西洋史的发展历程、优长与不足。在此基础上,包括施诚与魏涛在内的中国学者也梳理了此领域的发展脉络。
这些学术史反思中有几大要点值得留意。首先,“大西洋史”作为一个史学概念不仅意味着一个近似于布罗代尔式地中海的地理范畴、也不仅是大西洋周边国家与地区历史的综合,而是一系列强调大西洋世界中的联系与动态(Atlantic connections and dynamics)的历史诠释方法。其次,在地理空间上大西洋史需更重视两个方向的发展。一部分学者认为,大西洋史应当在全球语境下展开研究,探讨大西洋与包括印度洋在内的全球其他地区的联系。另一部分学者认为,20世纪的大西洋史过于侧重北大西洋,而新一代研究者应更强调将南大西洋的各种联系与动态纳入研究版图中。第三,一批受到后殖民史学思潮影响的学者则指出,传统的大西洋史研究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艾伦·卡拉斯(Alan Karras)指出,传统的大西洋史以欧洲为中心研究商贸交往、将美洲视为欧洲殖民与18世纪末革命时期国族形成的平台、并将非洲视为欧洲人掌控的美洲种植园的奴隶劳动力来源。保罗·科恩认为,“大西洋史”作为一种史学概念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和殖民主义倾向,学者们需要深刻地重新思考此概念使之能够有效地诠释美洲原住民的历史。为本专辑供稿的奥莱利便在早前的一篇英文学术综述中精辟归纳了这种后殖民批判思潮:“对于一些批评者而言,大西洋史不过是对若干‘其他细节’给予礼貌的关照,以新殖民的、政治正确的方式重新书写欧洲史。”在一定程度上,这股思潮也与对南大西洋的强调有所联系。

上述三种反思中,中国学人对前两者业已熟悉,但对第三股后殖民史学浪潮的了解仍不充分。应当承认,这股批判声音确有其中肯之处。大西洋史在二战后的欧美学界兴起的政治思想前奏是美国政论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倡导的“大西洋共同体(Atlantic community)”观念,而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北约的形成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在大西洋史早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雅克·戈德肖(Jacuqes Godechot)与R. R. 帕尔默(R. R. Palmer)强调以大西洋视角探讨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突出民主、自由等思想在大西洋世界的扩散;伯纳德·贝林关注北美新英格兰商人的大西洋贸易、欧洲人向北美的移民,又与戈登·伍德(Gordon Wood)、J. G. A. 波考克(J. G. A. Pocock)等学者一道在美国革命背景下探讨了共和主义与公民人文主义从欧洲向美洲的传播。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批学者,如约翰·艾略特爵士(Sir John H. Elliott)、拉尔夫·戴维斯(Ralph Davis)、约翰·J. 麦卡斯克(John J. McCusker)与拉塞尔·R. 梅纳德(Russell R. Menard)、理查德·邓恩(Richard Dunn)、杰克·格林等人,则从征服与殖民、大西洋经济体系、种植园经济、宪制体制构建等角度探索了近代早期列强在大西洋世界、尤其是北大西洋世界的殖民扩张与帝国形成。这些研究关注的历史行为主体是欧洲人、采取的研究视角也是欧洲本位视角,而这类研究的主导地位由令大西洋史好像是一部“近代早期西欧列强在北大西洋的殖民扩张、思想流传、帝国形成的历史”。因此,以“欧洲中心论”批判这种经典大西洋史学不无道理。不过,后殖民史学浪潮对当今欧美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的大西洋史研究已经产生深刻影响。任何一种史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批判欧洲中心论已成为大西洋史学史的一个话题时,就意味着史学实践上已有一大批作品对所谓“欧洲中心论的大西洋史”进行反拨。从史学实践的角度而言,这种后殖民批判体现在对“黑色大西洋”与“红色大西洋”的书写中。
“黑色大西洋”强调研究非洲人在大西洋史上的境遇及影响。尽管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大卫·埃尔蒂斯(David Eltis)、大卫·理查德森(David Richardson)等前代学者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统计在大西洋史研究中举足轻重,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更强调从社会史、文化史等维度,在相对微观的层面展开研究,聚焦于非洲人的具体境遇及主体性。“黑色大西洋”的概念最早由著名非裔学者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在1993年出版的《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一书中提出。他在书中探讨了奴隶贸易对非洲黑人的强迫迁徙产生的文化遗产,强调以大西洋作为一个更大的分析单元打破欧洲、美洲、非洲的边界,分析非裔身份、音乐文化、政治思想在跨大西洋大流散(diaspora)语境中的发展,呼吁以非洲为中心研究非裔文化。这样的观念深刻塑造了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研究。研究“中段航程(the Middle Passage)”的学者受吉尔罗伊的影响最深,强调从非洲到美洲的大流散过程对非洲人身份的再造。斯蒂芬妮·斯莫伍德(Stephanie Smallwood)的《咸水奴隶制:从非洲到美洲流散的“中段航程”》与詹姆斯·斯威特(James Sweet)的《多明戈斯·阿尔瓦雷斯:非洲疗愈与大西洋世界思想史》就是相关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一些学者强调大西洋奴隶贸易对北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时往往落脚于黑奴在种植园经济中的具体劳作境遇及此语境夏对奴隶制压迫的抵抗。在突出非洲人主体性与主观能动性方面,约翰·K. 桑顿(John K. Thornton)从文化与物质交流的角度强调了普通非洲人塑造大西洋世界中的联系的重要性。另一些学者,如大卫·理查德森、文森特·布朗(Vincent Brown)等人,则研究了黑奴在奴隶船以及美洲殖民地通过暴力起义反抗奴隶制的努力。强调非洲人在大西洋史上的境遇,乃至于突出非洲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面临史料的严峻限制。一方面,诸如奥拉达·艾奎亚诺(Olaudah Equiano)及索罗门·诺瑟普(Solomon Northup)自述等由非洲人留下的一手史料十分稀少,另一方面欧洲人留下的相关史料又往往带有自身偏见,因此詹姆斯·斯威特也专门探讨了如何挖掘、重审史料的问题。上述关于“黑色大西洋”研究,鲜明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大西洋史的欧洲中心论色彩的后殖民挑战。

《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
“红色大西洋”指的是以强调美洲原住民的主体性及视角书写大西洋史的实践。这一概念最初由马库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用以概述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各色属下阶层暴力反抗压迫的激进主义历史叙事。此概念后来被研究北美原住民史的学者杰斯·韦沃(Jace Weaver)借用,专指红肤色的北美原住民在大西洋世界的流散。韦沃在《红色大西洋:跨大洋的文化交流》一文中指出,以切诺基人为代表的北美原住民并不完全是以奴隶和受害者的身份被动卷入大西洋经济体系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自觉地自西向东进入大西洋世界,利用与欧洲人的物质、文化交流为本民族谋取生存空间。韦沃的研究引起了知名同行尼尔·索尔兹伯里(Neal Salisbury)的留意。索尔兹伯里以万帕诺亚格族(Wampanoags)人提斯宽图姆(Tisquantum)为例强调,部分原住民旅人虽对外部世界抱持着普世主义的开放心态主动融入大西洋世界的经济、文化网络,但这种主观能动性在面对欧洲帝国的殖民侵略时并不能完全赋予他们权力,更多地是反映一种艰难图存的境况。韦沃后来在专著《红色大西洋:美洲原住民与现代世界的形成,1000—1927》中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论点,在承认殖民压迫、跨民族交往的前提下强调原住民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主体性与主观能动性,而将欧洲视为客体参照系。这部作品也在北美原住民史研究者中引发了较大反响,《美洲研究学刊》甚至专门开辟圆桌讨论栏目对其进行评介。不论韦沃和索尔兹伯里的分歧如何,二人的论点都扎根于20世纪80年代以降北美学界原住民史研究的主流,不再以欧洲人为新世界带来文明开化的殖民叙事书写原住民与欧洲人互动的历史,而是正视原住民的主体视角:美洲在哥伦布到来前自有一段历史,对美洲原住民而言欧洲人是陌生的新来者与侵略者,双方的交往伴随着两种世界观的沟通、妥协乃至暴力碰撞。如果说大西洋史为原住民史带来了移民、物质文化交流等海洋史维度的新气象,“红色大西洋”的研究取径则以原住民本位,同“黑色大西洋”一道对大西洋史中传统的欧洲帝国扩张与思想流传的欧洲中心研究取径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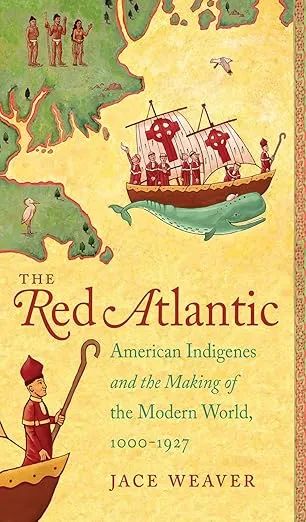
《红色大西洋:美洲原住民与现代世界的形成,1000—1927》
后殖民思潮影响下的“黑色大西洋”与“红色大西洋”研究无疑丰富了欧美学界的大西洋史研究。这并不是说大西洋史百花齐放的局面只由这种后殖民史学浪潮推进。新一代学者对帝国史的推陈出新,环境史对大西洋史研究的介入,以及采取“从下往上看历史”的视角研究大西洋世界中的欧洲人及欧洲文化,都对大西洋史研究的拓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研究与后殖民史学浪潮在近代早期西欧列强在北大西洋的殖民扩张、思想流传、帝国形成的脉络之外书写大西洋史都有共通之处。而就对欧洲中心论的质疑、对视角转换的强调以及对史料的重新思考而言,“黑色大西洋”与“红色大西洋”研究无疑是观点最鲜明、冲击力最强的潮流。
二
有鉴于此,本专辑所收录的论文与学术述评主要侧重于在介绍重要的概念与研究框架基础上突出以“黑色大西洋”、“红色大西洋”为主调的后殖民史学新成果,同时兼及环境史以及采取“从下往上看历史”视角对欧洲人的大西洋史进行研究。我们一方面强调对后殖民史学新成果、尤其是史料分析方法的吸收,另一方面不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大西洋世界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历史,而是指出后殖民史学相关方法与其他研究方向的互通性 ,并以“在大西洋内部发现大西洋史”理解这种互通性。
专题论文的第一组5篇文章集中展现了当代欧美学界大西洋史研究的若干重要概念与当代史学史和史学方法发展。大卫·阿米蒂奇的姊妹篇归纳了大西洋史研究的六种有用视角。《大西洋史的三个概念》一文最初发表于2002年。阿米蒂奇在总结二战后至21世纪初的诸多大西洋史研究时提出了三个基于地理范畴的概念:环绕大西洋水域发生的、超越国家乃至帝国疆界的环大西洋史(circum-Atlantic history)、强调历史比较与国家形成(state building)、帝国形成(empire building)的跨大西洋史(trans-Atlantic history)与研究大西洋世界内部具有独特性的地方及其与更更广阔地域相互联系的大西洋内史(cis-Atlantic history)。大西洋史在此后十数年的发展中日新月异,阿米蒂奇又提出三种新的分类:大西洋内部史(infra-Atlantic history)、大西洋水下史(sub-Atlantic history)和大西洋外部史(extra-Atlantic history)。相较于大西洋内部史,亚大西洋史更强调特定地域尤其是海陆边陲地区自身的界限、独特性以及人类活动及历史视角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西洋世界中不同政治经济势力相互竞争、被剥削族群抵抗欧洲帝国体系的历史现实及相关研究进展。大西洋下史将大西洋这样一个自然实体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显然受到晚近兴起的环境史、科学史、动物史等领域的影响。超大西洋史则反映了大西洋史研究者对全球史的追求,强调探索大西洋与外部世界,如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联系。威廉·奥莱利在《大西洋世界与德国:德国对大西洋史兴趣的起源及发展》一文中从以往较少涉及的德国史学界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大西洋史的发展。一战后德国国内不同政治潮流的折冲刺激了学界对“大西洋世界”这一观念的构想,并深刻影响了不同学术潮流的价值取向。二战后德国历史学者对欧洲与美洲联系的反思则催生了一大批大西洋史研究,在更广阔的海洋史语境中理解德国和德国人的历史。

大卫·阿米蒂奇
针对以往侧重北大西洋与欧洲帝国的大西洋史书写,路易斯·菲利普·德阿伦卡斯特罗与詹姆斯·斯威特的两篇经典文章则分别从史学史与研究方法方面给出了有力的补充。德阿伦卡斯特罗强调,传统的大西洋史只是以西北欧帝国扩张为主线的北大西洋史颇有以局部替代全局之嫌。史称“埃塞俄比亚洋”的南大西洋既有其独特性,近代以来的历史记载与研究也十分丰硕。以南大西洋为主的葡属大西洋世界、巴西在南大西洋的影响、非洲殖民与奴隶贸易以及非裔巴西人等研究视角无不说明南大西洋史也是大西洋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斯威特通过卷入奴隶制的非洲遗民的身份入手探究了大西洋史中海外非裔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因强迫迁徙跨越大西洋而流散于美洲的非洲人具有多重且模糊的的身份,无法简单地用“族裔”、“克里奥尔化”或非洲文化的“留存”概括。他们在非洲故土的独特身份有别于同在非洲的其他地方人群,但在横跨大西洋的过程中又因他人视角和自身对具体境遇的因应获得了多种身份标签,包括抹杀其地方独特性的“非洲人”身份。因此,研究者需要在具体语境中审视不同身份是如何人为构造与再造的,要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揭示其多重身份的往复与折冲,这样才能对非洲及非裔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作用有更全面的考量。

第二组5篇专题论文为我们在帝国形成、大西洋革命等传统视域外研究大西洋史提供了若干地域及话题概览。它们侧重于“从下往上书写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展现传统大西洋史书写所忽略的族群的历史。艾伦·弗雷斯特在《长18世纪中的法国与大西洋世界》一文中梳理了法兰西的大西洋帝国之兴衰。法属大西洋世界因殖民地贸易与奴隶贸易兴起,在受到18世纪中后期的一系列战争及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后瓦解。相比于美法“姊妹革命”的视角,作者特别强调奴隶贸易在法属大西洋兴衰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作者也在文末为中国读者提供了法属大西洋相关一手史料的宝贵信息。埃丝特·迈尔斯的论文梳理了17世纪苏格兰人在尼德兰大西洋帝国中的活动。以往对英伦三岛与尼德兰共和国关系的研究往往专注于英格兰一国,但迈尔斯的研究说明,即便苏格兰人并未像英格兰人那样建立起一个有形的大西洋帝国,他们仍能凭借与尼德兰共和国长期以来的商贸与宗教联系在尼德兰大西洋世界中开创一片天地。威姆·克娄斯特全景式地展现了尼德兰水手在尼德兰大西洋帝国中的命运,尤其是他们在巴西殖民地得失中扮演的角色。胡佳竹和马克·汉纳的两篇论文探究了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英格兰海盗问题的延续与嬗变。尽管海盗是大西洋史和西方流行文化中经久不衰的话题,汉纳仍在其论文中提出了新的洞见。他在梳理前代研究者的海盗研究后指出,活跃于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的英格兰海盗并不尽然是脱离主流社会的海上浪人。海盗与陆上社区的关系往往是紧密而暧昧的。这不仅在于近代早期国家权力对私掠(privateering)的授权以及私掠与海盗行为(priracy)的模糊界限,更在于海盗依赖陆上社区谋生存、也十分看重自身在陆上社区中的形象。海盗与陆上社区的这种紧密而暧昧的关系并非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的新生产物,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胡佳竹的论文表明,中世纪晚期西北大西洋东岸的海盗、海商与国家海洋军事力量之间存在相互纠缠、相互转换的复杂关系,王权对海盗行为的态度是灵活嬗变的。因此,尽管英格兰海盗在近代早期的活动范围大为扩张,成为一种环大西洋的历史现象,但海盗与陆上社区的关系仍与中世纪传统密不可分。上述5篇地域及话题概览论文从一些重要侧面反映了近年来大西洋史研究的新趋势:转向奴隶、美洲原住民、水手等以往被忽视的属下阶层、主要殖民列强以外的民族,探索人口流散等新的社会史议题,并从海陆关系等新视角重新理解、诠释大西洋史中的经典话题。

艾伦·弗雷斯特
第三组5篇专题论文以更具体的实证研究呈现了跨大西洋的联系、邂逅与不平等。弗吉尼亚·德约翰·安德森的《菲利普国王的牧群》是将北美殖民史与动物史相结合的先驱之作。尽管安德森在文中并未明确言及“大西洋史”的框架,但其探究的历史现象无疑是英格兰人在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殖民活动的产物。从英格兰引入马萨诸塞湾地区的牲畜在英格兰殖民者与当地原住民之间造成了日益频繁的摩擦,而这些摩擦背后的根源则是二者间牵涉自然、动物、土地、公正等问题的底层观念冲突,可谓是两个世界的碰撞。欧文·斯坦伍德考察了近代早期大西洋史中一个特殊的属下阶层群体——流亡北美的法国胡格诺派难民。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废止南特敕令后迫使许多胡格诺派(法国新教徒)流亡海外。他们利用自身的网络在欧洲再造法国新教教会的尝试失败后转向大西洋对岸,在北美成为早期大英帝国和尼德兰帝国的臣民。他们虽怀揣信仰,却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成为丝绸的制作者、葡萄酒的生产者与充实帝国边陲的边民。此文不仅展现了人际网络与帝国权力之间的张力,也通过水手、黑奴、原住民之外的群体展现了大西洋世界中属下阶层诸般历史经验的多元与统一。这第二点洞见在林福德·菲舍尔的论文《新英格兰与牙买加殖民地的不自由劳动谱系》中有进一步展现。菲舍尔认为,尽管新英格兰与牙买加奴隶制规模不同,但两地却因不自由劳动的谱系而存在历史比较意义上的相似性。白人、印第安人、自由黑人都可能因各种不利境遇卷入不自由的契约劳动。契约仆与奴隶在政治话语、法律地位、强迫劳动、人身自由等方面形成了一道连续的谱系,以奴隶制最为不自由。安娜·露西娅·阿劳若的两篇文章探讨了晚期大西洋奴隶贸易与达荷美(今贝宁)政治的关系以及相关历史记忆在后世的流传与嬗变。阿劳若为我们思考奴隶制及其影响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即非洲政治精英与奴隶群体对奴隶制变迁的因应以及其中所体现的主观能动性。达荷美王国的统治者极度依赖对维达海岸奴隶贸易的垄断以维持其奢侈品消费与政治权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达荷美王国的政治动荡与王权更迭不仅源于阿丹多赞国王一人之暴政,也有深刻的大西洋奴隶贸易背景。法国大革命时期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衰落在阿丹多赞倒台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官方信函表明,作为政治斗争失败者的阿丹多赞与胜利者的新王盖佐都勉力与欧洲列强修好,以图在大西洋奴隶贸易衰落的历史背景下维持对维达奴隶贸易的垄断,以图维持自身权势。作为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符号象征,巴西奴隶商人弗朗西斯科·费利什·德索萨的形象在家族记忆中因现实政治需求被不断形塑、美化,形成了一个身份杂糅、横跨非洲—葡萄牙—巴西社群的个人神话。

圣巴托罗缪之夜
学术述评包含7篇书评与1篇研究综论。7篇书评所涉书目皆是大西洋史领域的经典或前沿作品。卿倩文评述了一本重要论文集《大西洋史:批判性评论》,并结合该论文集在欧美学界的反响、我国学者对大西洋史研究的若干进展提出了对大西洋史内涵与外延的再思考。此后3篇书评集中关注以环境史、生态史视角研究大西洋史的作品。宁广要通过评介查尔斯·C. 曼恩的姊妹著作《历史的碰撞:1491》与《历史的碰撞:1493》,分析了生态环境史介入大西洋史研究并批判欧洲中心观的重要成果。刘晓卉批判地评述了山姆·怀特的专著《欧洲与美国在小冰期的冷面相迎》。她指出,以气候、环境为着眼点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欧洲殖民者与北美原住民的摩擦,而且跨大西洋殖民邂逅对环境本身的影响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谢瀚霆评介的《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一书则进一步说明以环境史与性别史、知识史等研究手段相结合的研究潜力。覃思、刘超评述了英国史学家约翰·艾略特爵士的名著《大西洋世界的帝国》。他们肯定了作者在全球史视野下动态掌握近代早期不列颠、西班牙大西洋帝国异同、整合历史碎片的能力,同时也指出未能充分关照原住民、非洲人视角以实现其所谓展现欧洲人与非欧洲人持续互动塑造殖民地历史的研究目的。对非洲视角的关照则在美国学界近年来两部热门作品中有所体现。张咪对《咸水奴隶制:从非洲到美洲流散的“中段航程”》的评述指出了这部作品的社会文化史贡献:它揭示了非洲黑人历经中段航程后被商品化过程中的“社会性死亡”与身份重塑,帮助我们在计量方法之外理解奴隶贸易对黑人的戕害。同时,张咪也结合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发展历程客观评价了该书在史料运用与视角上的局限。董鑫从全球微观史与传记研究的角度评析了《多明戈斯·阿尔瓦雷斯:非洲疗愈与大西洋世界思想史》的优长与缺陷,并指出该书在跨领域研究方法及海陆视角结合方面的特色。最后,马龙的学术综论《超越丝绸之路: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网络、全球货物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市场的一体化(1680—1840)》介绍了当前欧洲学界在近代早期大西洋、太平洋贸易联系方向的研究进展,体现了阿米蒂奇所谓“超大西洋史”的实践成果。
三
本专辑所收录的具体研究论文、评述的著作各有侧重,但就研究取径的共性而言,可概括为“在大西洋内部发现大西洋史”。以近代早期西欧列强在北大西洋的殖民扩张、思想流传、帝国形成为主线书写大西洋史,是一种胜利者的历史叙事,既忽视了德阿伦卡斯特罗强调的南大西洋空间,也忽视了非洲人、美洲原住民等其他族群所创造的历史,不免以偏概全。从研究方法上如何对此进行纠偏?斯威特的文章为研究者在超越传统大西洋史局限方面提出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研究手段,即落脚到大西洋世界中各种行为主体的多样经验、扎根于地方上的各个群体的物质与精神世界来理解大西洋史,通过地方特殊性再审大西洋史中形成的跨地域联系。这其中有两点值得留意。首先,研究者不应无条件地接受胜利者视角,不应认为殖民帝国执权柄者书写的大西洋史即大西洋史的全貌,而要尝试从失语者的角度审视大西洋世界的历史进程。其次,研究者还应意识到权力在历史叙事的更深层对史料的塑造作用:强势者与弱势者的权力博弈不仅影响了史料的产生与灭失,也影响了现存史料所隐含的文化意义、价值预设。弱势者之所以失语,不仅因为与之相关的史料更易灭失,更在于传世史料在产生过程中因权力博弈更易带上位居强势一方的殖民者的价值观念。因此,批判地审视史料中隐含的这些观念尤为重要。这样的研究方法在弗吉尼亚·安德森的专题论文以及宁广要、张咪和董鑫评述的著作中有鲜明体现。
从史学潮流兴起的角度说,斯威特的文章集中反映了过去三十年来去殖民化浪潮在大西洋史领域所带来的方法论启示。但笔者认为,以域外之身介入大西洋史研究的中国学人(包括笔者在内)却不必仅局限于“后殖民史学”的标签,而可以用“在大西洋内部发现大西洋史”的观念拓宽对这种研究浪潮的理解。着重于转换视角、扎根于地方、个体特殊性研究大西洋史的方法并不局限于探讨西北欧帝国扩张过程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迈尔斯、克娄斯特、汉纳与斯坦伍德的研究揭示了来自欧洲的属下阶层在走向大西洋世界过程中身为帝国边缘人的境遇。阿劳若的研究则更多地反映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地方社群内部的影响。这两组研究虽不直接强调欧洲殖民帝国在大西洋世界中对被殖民对象及其所处环境的压迫与剥削,但却与大西洋世界中发生的物质、文化联系息息相关,采取的研究方法也是与经典的后殖民史学作品相通的。
“在大西洋内部发现大西洋史”同时也意味着在地方语境下重新审视大西洋世界的物质文化交流对欧洲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影响,这是当前大西洋史研究潮流中着墨相对较少且有发掘潜力的方向。20世纪史学家对白银流入欧洲及“价格革命”的讨论虽是此方向的先驱,但相关研究着重于经济结构,与社会史、文化史、心态史等新兴研究方向关系并不密切。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山填补了这些方向的空白。一些学者对土豆、烟草、巧克力等消费品的研究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展现了大西洋世界的联系对欧洲社会变迁的影响。另一些学者则探讨了大西洋世界的奴隶制、殖民如何塑造了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社会文化、民族身份认同。
鉴于本专辑并未收录此方向的专题论文,笔者不妨试举一个与社会心态相关的个案作简单说明。英格兰的美洲殖民贸易至17世纪中叶已具相当规模,每年,伦敦、布里斯托等长途海上贸易重镇都有大量上传(以下简称“美洲殖民商船”)前往美洲殖民地采购糖、烟草等货物,到夏秋两季时经爱尔兰南部、英格兰西南部等面向大西洋的优良港口(包括金赛尔、布里斯托、普利茅斯等良港)返航。对于这一带沿海地区的人民而言,这种季节性的跨大西洋殖民商船往来已成为其日常生活的常态,商船在本地港口经停或沿岸航行皆举目可及。但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时期,美洲殖民商船归航时却往往在对此再熟悉不过的爱尔兰南部、英格兰西南部沿海居民间引发大规模的入侵恐慌。1666年夏,英政府情报首脑约瑟夫·威廉姆森(Joseph Williamson)在爱尔兰的一名通讯人所言:“不日前弗吉尼亚商船队出现,令芒斯特省毗邻金塞尔一带大为震恐。”翌年,当弗吉尼亚与巴巴多斯联合商船队悬挂英格兰旗帜出现在英格兰西南的法尔茅斯(Falmouth)毗邻水域时,岸上驻军最初“仍以之为荷人或法人”,城中士兵立即“披甲带器”严阵以待。已然成为常态的跨大西洋贸易航行在战时引发如此非常态的大众心态应激反馈,可以说是社会心理与人的观念中对跨大西洋日常经济联系的稳固认知被战时特殊环境所扭曲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美洲殖民商船的归航会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时期引发沿海民众的入侵恐慌?以往人们对跨大西洋日常经济联系的固定认知为何被扭曲?要回答这个问题,则必须回到“作为大西洋世界内部的一个地区”的英伦三岛展开分析。首先,美洲殖民商船归航引发的恐慌是英伦三岛各地民众惊惧于外敌入侵的缩影。1666年初法王路易十四向英格兰宣战后,白厅旋踵收到尼德兰与法国可能入侵英格兰、爱尔兰的军情密报,查理二世也因此命令英格兰滨海各郡加紧武备。在1666—1667年间,外敌入侵之可能一直是复辟王朝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心腹大患,对于爱尔兰王国而言尤甚。由于岸上人民往往不易识别自海上抵近的舰队与船只的身份,战争期间尼德兰及法国的战舰或私掠船又常悬挂英格兰旗帜作为伪装近岸袭扰,我们因此也不难理解临海百姓在恐惧外敌入侵时为何会将将己方商船队误作敌方舰队。复辟王朝从中央到地方财政困顿以至于海防废弛、使沿海地区人民无力自保,是大众心理中入侵恐慌的根源。战费之捉襟见肘初显于1665年秋冬、恶化于1666年、延续至1667年直到查理二世于当年夏屈辱议和,从海军主官到地方百姓皆饱受其苦,一些地方仅存的零星岸防火器也因资金紧缺得不到修缮。爱尔兰有过之无不及,该王国财政历来不能自足而必须依靠英格兰输血,战争期间更为恶化。爱尔兰国库空虚不仅导致士兵因欠饷而军纪废弛,也使地方海防问题丛生。雪上加霜的是,1666年夏,王家海军在四日会战(Four Days’ Battle)中惨败于尼德兰海军,不论是沿岸巡逻抑或战略威慑皆实力大损。正如爱尔兰总督奥蒙德公爵(Duke of Ormond)所言,会战后英舰队“元气大损”而法舰队“毫发未伤”,若爱尔兰此时不慎防法国入侵,则无异于“行疯癫之事”。海防废弛令沿海地区面临外敌入侵之威胁时可谓门户大开,也无怪乎手无寸铁的百姓时时恐慌,以至于在美洲殖民商船归航时也做出应激反应。
相比于把大西洋世界作为一个客体纳入欧洲列强的殖民帝国体系,这样的研究取径则在欧洲的地方语境下探讨大西洋作为一个异域如何介入并影响欧洲的历史进程。如此重新思考大西洋世界与欧洲的关系,同样需要对欧洲殖民帝国扩张的传统历史叙事祛魅,挖掘史料的内涵,尤其是大西洋世界相对于传统欧洲社会的异质性、跨大西洋联系的不确定性,。
因此,这种扎根于地方语境和个体独特视角的研究思路虽发轫于后殖民史学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却对理解大西洋世界中不同行为主体、不同地区的特有的历史、继而重审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的联系以及大西洋世界一体化螺旋式上升的曲折历程。到头来,近代早期的大西洋世界并不是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或其他北约的政治鼓吹手所想象的大西洋世界。相反,它是多个族群相互邂逅、竞合与交融的场域。乔纳森·米兰(Jonathan Miran)在反思《美国历史评论》“历史中的海洋”(Oceans of History)专题论坛时评论道:“绝大多数海洋空间本质上都是割裂、破碎且不稳定的竞技场。”不论大西洋海盆中存在多少联系,也不论史学家如何苦心孤诣地尝试发掘它们,这一切联系首先来源于“一系列不同的空间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竞争的不同视角。”本辑所刊的论文充分表明,不同历史行为主体对这些复杂历史进程的经历与体验,是深受各自政治、社会与文化背景所影响的。假如我们借用阿米蒂奇提出的概念,环大西洋史、跨大西洋史、乃至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大西洋史,都必须通过各种大西洋内史与大西洋内部史进行理解。
四
之所以要“从大西洋内部发现大西洋史”,有三大原因。诚然,并非所有的大西洋史都局限于大西洋海盆中的一个地区;书写跨大西洋的联系、甚至类似于哥伦布大交换这样遍及整个大西洋世界的复杂联系网络自然是了不起的学术壮举。然而,研究的常态是,大历史与宏大叙事要能站住脚,必须扎根于对小历史的坚实掌握。如果不能理解新英格兰地区的北美原住民的世界观,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为何牲畜可以成为菲利普王之战(King Philip’s War)的导火索之一。如果不能在新英格兰和牙买加各自的语境中理解契约劳役与奴隶制的形态,我们就不可能像林福德·菲舍尔一样书写关于不自由劳动的环大西洋史。此乃其一。

菲利普王之战中原住民袭击殖民者
其二,断代问题。英语学界一些学者以哥伦布发现美洲为上限、法国革命战争引发的美洲被殖民区域革命(如海地革命)动摇西欧帝国体系为下限对大西洋史做出断代,不可谓不专断。只有“从大西洋内部发现大西洋史”,后来的研究者才能有效地挑战这种专断的断代。如果我们对比阅读马克·汉纳与胡佳竹在本辑中的论文,可以发现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中海盗行为——一种真正的“跨大西洋历史现象”——的某些特征,具有深刻的中世纪根源,但在中世纪时,海盗与私掠绝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大西洋内史”或“大西洋内部史”。这种历史连续性也在上节事例中有所体现。由此我们得以拷问传统断代上限的合理性。同时,我们也能从安娜·露西娅·阿劳若的论文中了解到,达荷美与巴西的奴隶贸易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中叶。换言之,这种跨大西洋的联系并不因18、19世纪之交的大西洋世界革命而瓦解。所以,我们也应当质疑传统断代下限的合理性。因此,我们或许能对大西洋史的年代框架作出更精确的描述:近代早期(1500—1800年左右)的确是西半球历史上深刻的转型时代,许多跨大西洋和环大西洋的联系正是在这一时代大规模产生,但这些联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前时代的特定地区,而一个日益整体化的大西洋世界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乃至今日。法国革命战争并没有真正让大西洋世界解体——旧的奴隶贸易联系或许逐渐终结,但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于垄断资本主义、1976年《牙买加协定》以及新的产业革命之上的新联系。
其三,至少从英语学界的研究动向看,“从大西洋内部发现大西洋史”是挑战大西洋史研究中曾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的有力工具。本辑中詹姆斯·斯威特及阿劳若的论文,以及董鑫、张咪评述专著都是如此挖掘大西洋世界中被殖民对象的复杂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从大西洋内部发现大西洋史,我们才能既关照在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拥有技术和强权而占据主导的欧洲人、也关照被欧洲人奴役的各个族群。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基层理解大西洋史的丰富性,并对大西洋世界中的历史联系建构出更复杂、更精密的历史诠释。
本辑所编选的论文在内容导向上固然有所侧重于后殖民史学,但此举意在忠实地呈现编者在美国各个学术场合所接触到的潮流的面貌,而非作为观察者对其表达某种或全然肯定或全然否定的态度。与其刻意引领本辑读者的道德判断,不如把判断的权利与权力交还给读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毫无价值判断。编者最根本、最坚定的价值判断是:我们对大西洋史的研究,必须扎根于史料、扎根于区域和地方、扎根于细节;这样的研究才具有长久生命力。因此,本辑所收论文的核心价值,在于说明如何实现此目标,而不仅是为了介绍理论框架、研究动向。大西洋史的当代后殖民史学之所以在历史技艺的层面绽放光彩,在于它在面对研究对象史料大规模湮灭与二十世纪中叶主流史学盲点的严峻制约时,能够试图重现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中失语者的悲欢离合。这在本辑相关论文(及印度洋史等姊妹领域)中有充分体现。
编者必须特别强调,“从大西洋内部发现大西洋史”并不是英语学界后殖民史学的专属。强调基层在地研究,既反映英语学界大西洋史学从欧洲中心视角转向后殖民多元视角的特殊性,也是数字时代全球史、跨国史、大区域史等研究能够真正出彩的必然要求。本辑中威姆·克娄斯特、埃丝特·迈尔斯的论文各自牵涉属下阶层(水手)与大国背影中的少数群体(近代早期尼德兰帝国中的苏格兰人),其围绕欧洲人所展示的广阔历史图景都扎根于反映基层境况的史料及对区域、地方的细节研究。读者们不难通过脚注发现,在上节的个案分析中,编者强调从相对较小区域的语境中解剖跨大西洋联系的历史意义;这种史料分析方式与许多关于大西洋世界中失语的被殖民对象的研究并无本质差异,尽管此个案丝毫不涉及北美原住民或非洲黑奴。编者正是希望通过这个不起眼的案例说明,扎根于史料、区域和地方、细节的取径对于从任何视角开展的大西洋史研究——不论是牵涉欧洲列强还是被殖民对象、抑或是环境、动物等晚近蓬勃发展的研究话题——都是必须且能够实现的。
“从大西洋内部发现大西洋史”不仅对研究大西洋海盆中发生的历史至关重要,也对研究大西洋世界与外部的联系——即阿米蒂奇所谓“大西洋外部史”——不可或缺。比如,本卷“学术述评”栏目中所收马龙《超越丝绸之路: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网络、全球货物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市场一体化,1680—1840》一文即指出,近代早期大西洋、太平洋的制度外贸易联系往往依托于转运港展开。换言之,全球化早期的大西洋—太平洋贸易网络是两大洋内部具体的地方或小区域形成的联系,而非宽泛的两个大洋、两个世界体系的联系。正因为联系的地方性、具体性,微观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在马龙所总结的研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若干年前,刘津瑜教授在评介罗马与中国比较研究的著作时曾有如此论断:“如果中国学者只是在西方罗马研究的成果上进行比较研究,其实是放弃了在罗马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如此论断迁移至大西洋史也十分恰当。如果中国学者只是批判欧美学界经典大西洋史的欧洲中心论色彩、或呼唤研究东西海洋世界的联系却忽视下沉局部与基层,其实是放弃了大西洋史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尤其是基础研究和史料诠释的话语权。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学界已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随着有志于此的中国学人共同努力,中国学界也将为大西洋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本文刊于李庆新、张烨凯主编:《海洋史研究》第23辑(大西洋史专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作者简介:张烨凯,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博士
备注:作者对正文有细微修订;引用文献参见刊印版。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海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