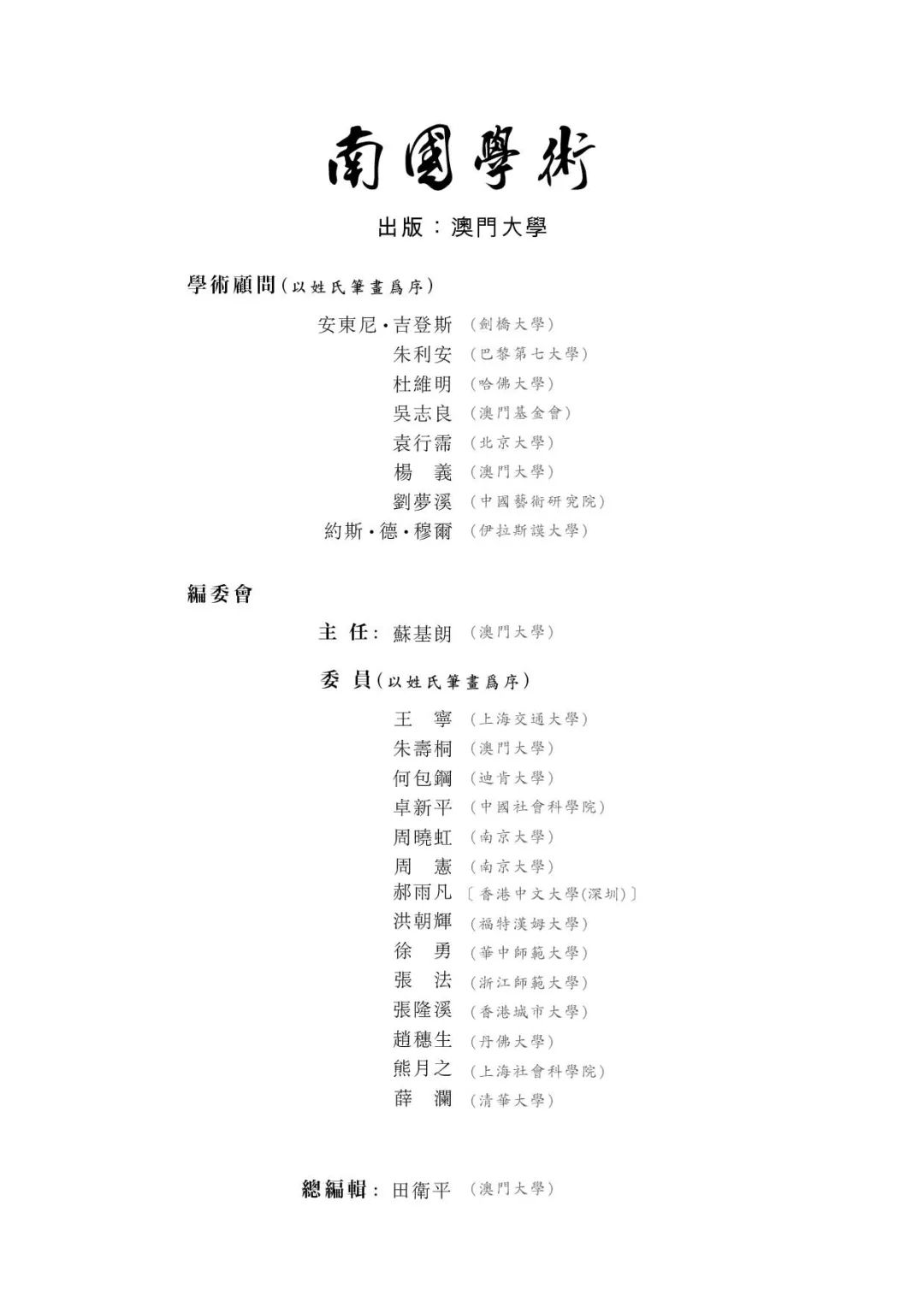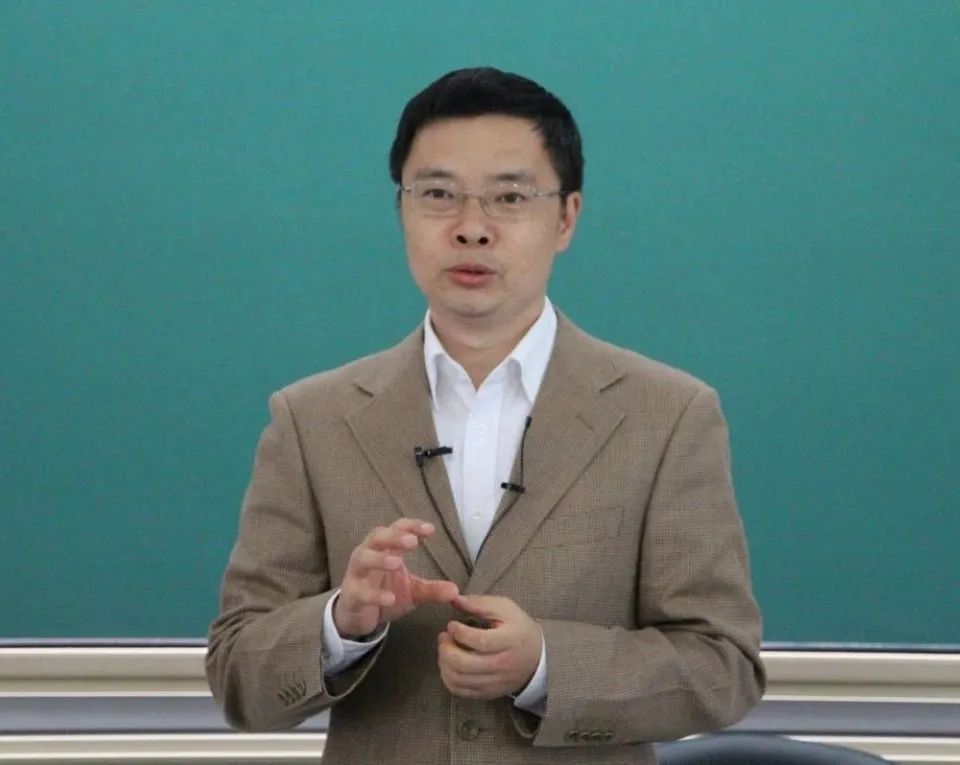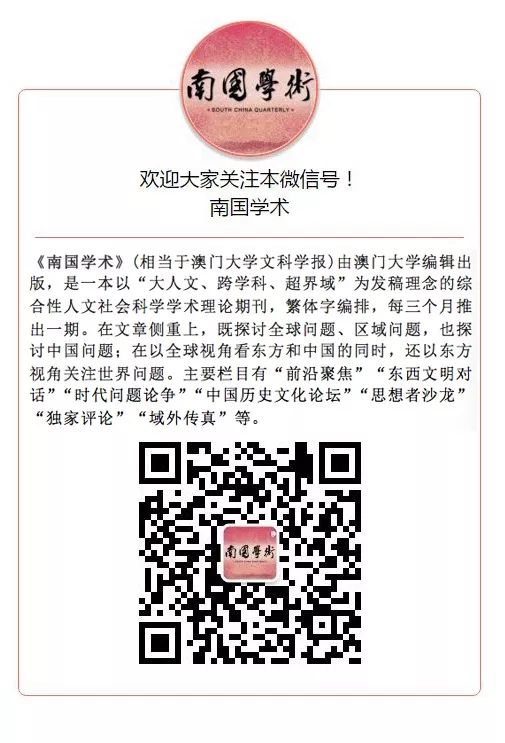[作者简介]倪玉平,2003年在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被教育部遴选为“青年长江学者”,先后任职任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代表性中文著作有《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博弈与均衡:清代两淮盐政改革》《清朝嘉道关税研究》《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英文著作有《清代关税:1644—1911年》等。
区域经济的形成,既是经济不平衡性的表现,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关中平原和华北地区在很长时间里曾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但唐代以后特别是北宋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经济中心逐步向南方移动。如果说,唐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经济重心第一次移动的话,那么,到了清代,中国经济重心又开始了第二次移动,即由内地向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而这新一轮的移动,在数据指标上有着充分展现。明清以来,以江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发达,农业则由粮食主产区和主要供给地变为主要输入地。到晚清时期,清代沿海地区人口数量虽然略少于内地省份,但人口密度远高于后者,且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也更高。清代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商品交易的活跃程度上。除个别时段因受到太平军的占领等特殊原因外,沿海地区的厘金征收数量都要高于内地,沿海地区百姓的厘金负担也高于内地省份。沿海地区的关税征收量,不论是针对国内贸易征收的常关税,还是针对国际贸易的洋税,都远远高于内地,有时甚至超过了四倍的水平。由于晚清时期也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时期,中国经济被进一步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使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一种整体式发展,而非仅限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局部发展。与第一次经济重心向南转移相比,这第二次由内地向沿海地区的向东转移有了新的重要变化。它除了在型构上呈现一种“V”字型外,在特征上也不再是以人口的多少而是以经济的活力、商品流通程度为标志。由此显示出,清代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靠人力投入的农业型社会,而向工商业方向迈进。在人口数量和可耕地面积小于内地省份的情况下,沿海地区走出了一条商业化的发展道路,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内地省份,尤其是在人均水平方面更是如此。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的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经济重心在沿海地区这一格局已完全确立,而其源头则来自清代开始的变化。
经济重心的变动是社会经济长期不平衡发展的结果。隋唐以前,中国经济的重心在北方,但从南北朝开始,经济重心已逐渐向南方转移。中唐至五代时期,南方社会相对稳定,没有北方那样频繁的战乱,经济获得较大程度的发展。两宋时期,南方经济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日益重要,地位超过北方。这一时期的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极大地塑造了此后的历史发展轨迹。不过,经过元明时期的调整,到了清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又一次发生移动,即由内陆向沿海的东向转移。这次经济重心的东移,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经济重心转移,并且格局大致保留至今,影响深远。本文拟就此做一分析,以求正于方家。一
区域经济的形成,既是经济不平衡性的表现,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在清代前中期,由于政局相对稳定,较少发生战争和动荡,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昭槤在《啸亭续录》中称:“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繁荣的基础上,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形成了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与此相伴随,以江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代表的沿海经济也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粮食产区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指标。明朝丘浚在《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四写道:“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谚有之曰:‘苏松熟,天下足。’”这说明,苏松地区在明代还是全国粮食的主产区和主要供给地。但到了清朝,这种粮食主产区的地位已经被湖广地区所取代,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即以今天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平原已经取代苏常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相反,江南地区成为粮食输入的主要目的地,粮食交易的枢纽地位得到确立,长江三角洲地区粮食业市镇的规模相当大,其中尤以苏州的枫桥市、吴江县的平望镇为有名。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指出,尽管清代前、中期的粮食流通,绝大部分仍然以地方小市场上的互相调剂和在区域市场内供应城镇人口的需要为主体,但长距离的运销已有长足发展。该书估计,当时安徽、江西米经长江运江浙的,年运量在500万石左右;湖南、四川米经长江运江苏的,年运量至少在1000万石以上。除此之外,还有奉天豆麦经海运到上海,年运量在1000万石以上。这说明,江南地区已经成为主要的粮食输入地。邓亦兵也对清朝乾隆时期的粮食流通数量做过研究。邓氏统计的粮食流通品种包括稻米、小麦、粟米、豆类、高粱等,她还将豆饼计算在内;邓氏讨论的范围,仅限于民间粮食运输,不涉漕粮、军粮及官方采买;在估算方法上,邓氏主要是利用关税资料来估算粮食的过关量,也考虑到并非所有运道都设有关卡征税,故而又依据过往船只的数量进行辅助估计。按照邓氏的研究,清代前期分布于内陆的江河水系,能够通船载粮的主要有长江、西江、闽江、淮河、黄河、海河、滦河、运河等水系。其中,长江水系的粮食运输量,乾隆年间的高峰时期由四川的300万石、湖南的800万石、湖北的200万石、江西的450万石、安徽的100万石组成(均指各该省的粮食外运量),总量在1850万石以上,主要供沿海地区之用。邓氏的研究同样说明,江浙沿海地区已经由原来的粮食净流出地变成粮食净流入地了。清代江南地区虽然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区,但依然有着明显的农业生产技术升级换代及替代转移优势,由以前的外销主力变成采购主力。通过李伯重等人的研究可以发现,江南地区的农业耕作技术遥遥领先全国。清代提高复种指数,发展多熟制的耕种方式,是在开垦土地外解决耕地不足的又一重要途径。在江南地区,水稻两熟是最为普遍的耕作技术,双季稻的种植既是选种技术的进步,也使稻麦多熟制得到进一步发展。类似的模式还有稻豆两熟、稻油两熟、稻与烟草等经济作物两熟等等。这里尤其注重施肥,采取多种方法积肥,普遍使用苗粪、草粪、火粪,根据土质类别,施以不同的粪肥,以提高地力和产量。江南地区发达起来的农业耕作技术,又迅速推广到内陆地区,形成稳定的技术传导路线。清代最发达的棉纺织业在沿海地区。广大农村除农业生产外,养蚕植棉、缫丝织布是最重要的家庭劳动。江苏的“松江布”闻名天下,其发展也受到清代鼓励政策的影响。棉纺织业的生产形式主要是农村家庭副业式的小商品生产,规模较小,更加分散。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下,农村中的妇女在家中织布,然后拿到市场上交换,以维持生计并进行再生产,是棉纺织业存在的普遍模式。据光绪《平湖县志》卷二、卷八记载,当地农村“比户勤纺织,妇女燃脂夜作,成纱线,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或拈绵线以织绸,积有羡余,挟纩赖此,糊口亦赖此”,“邑中妇女以此为业”。在家庭副业式生产的基础上,棉纺织业出现了一定的专业化趋势。在一些市镇中,有了专门纺织棉布的作坊和劳动者“机工”,也逐步划分出轧花、纺纱、织布、印染、踹压等工种,每个工种都有各自独立的作坊,如印染业、踹布业等,表明专业化的生产模式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与江南发达的棉纺织业相适应,这里还出现了一批专业的棉布业市镇,如嘉定县南翔镇和镇洋县鹤王市,棉花市场规模都极大。丝绸是奢侈品,也是技术含量极高的手工业产品,清代的丝纺织业仍然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清廷专门设立官营机构进行管理和生产,包括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专为皇室提供丝绸。三处织造局由清廷专派官员管理,规模庞大,至乾隆时每处织造局织机均已达到600张以上,工匠超过2000人。民间丝织业虽在规模上不比官营,但发展速度也很快,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丝绸业市镇。苏州地区的丝织生产集中于城东,“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工匠各有专能,或素或花”。杭州的丝织业生产同样发达,厉鹗的《东城杂记》卷下说:“杭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以至有“吴丝衣天下”的美誉。吴江县盛泽镇在明朝嘉靖时还是个只有百户人家的丝织小镇,到清朝乾隆年间,已经发展为有居民万户、远近闻名的丝绸大镇,“镇之丰歉,固视乎田之荒熟,尤视乎商客之盛衰。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客商。而开张店肆者即胥仰食于此焉”。湖州府双林镇也是如此,“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可见商品经济之发达。珠江三角洲是仅次于江南地区的经济发达地区。广东省的农村市场不称市镇而叫墟市,人们到市场交易称为“趁墟”。不论是手工业型市镇,还是商业型市镇,或中转运输型市镇,珠江三角洲地区市镇的密集度都远高于广东的其他地方。珠江三角洲地区墟市的绝对数量也最多,据雍正《广东通志》记载,这里的墟市已占全省总数的40%以上。广、肇、潮、惠等府的农产品商业化程度极高。番禺的花市、合浦的珠市、罗浮的药市和东莞的香市,合称广东“四市”。广州是清代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而茶叶和丝绸始终是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故种茶、栽桑殖蚕在当地农村非常普遍。桑树的栽种采取了与养鱼相结合的办法,即在鱼塘周围的堤岸土基上,栽种桑树,鱼塘浊泥可以肥树,蚕粪则可以喂鱼,“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龙眼多树宅旁,亦树于基。基下为池以蓄鱼,岁暮涸之,至春以播稻秧,大者至数十亩。其筑海为池者,辄以顷计,九江乡以养鱼苗”,农业生产商品化趋势进一步增强。由于当地商品经济繁荣,商品蔬菜的需求量逐日增加,在城镇附近的一些农村,逐渐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蔬菜生产基地,为城市居民和工商人口服务。如广州西郊,自浮丘以至西场,是很大的蔬菜供应地。花卉和香料也是城镇市场中经常见到的商品,销售量大。山东、直隶的经济在清代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根据许檀的研究,相较于明代华北地区商业城镇的稀疏,“清代华北商业城镇的数量和规模都有大幅度增长,其空间分布也比明代广泛得多”。山东、直隶由于是漕运孔道,在大运河的支撑之下获得大发展。清代前期河运兴盛之时,每年承运漕粮的运船有六七千艘。按规定,凡漕船出运,除装载正耗粮米外,还可附带一定数量的免税“土宜”(土产货物)。如果每年出运漕船以6000艘计,每船平均携带“土宜”150石,则嘉道年间漕船每年所带的免税商货有90万石之多。再加上旗丁水手携带的走私物品,数量更加可观。这对于清代运河经济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物资的交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以山东临清为例,据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关榷·税额》载,南漕“悉由此河输至京师”,每届漕运便“帆樯如林,百货山积”。因为当地人口众多,粮食消费量巨大,地产谷不敷用,只能取资于商贩,“秫、粱则自天津溯流而至;其有从汶河来者,济宁一带粮米也”。乾隆时期的临清城内共有粮食市场六七处,经营粮食的店铺多达百余家,每年粮食交易量在五六百万石至一千万石之间,“是当时山东,恐怕也是华北最大的粮食市场”。二
自唐宋以来,沿海经济尤其是海外贸易便得到长足发展。清初,为对抗以郑成功为首的东南沿海抗清集团,于顺治十八年(1661)颁布迁海令,命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居民向内地迁移30~50里,禁止任何船只出海,这严重影响了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清朝统一台湾后,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对外贸易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都承接对外贸易,其中粤海关是主体。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地位,使得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对清代的社会经济有着重大影响。根据马士(H.B.Morse,1855—1934)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记载,从1664—1753年的90年间,共有199艘来自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活动于中国,其中153艘在粤海关进行贸易,占所有船只的77%,可谓一枝独秀,遥遥领先。洪任辉事件后,清廷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只允许广州一口作为贸易口岸,粤海关成为唯一拥有国际贸易特权的税关,使其在对外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不仅是外国商品输入的港口,也是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交易场所。全国各地的出口商品,特别是华中、华南地区的商品,大都集中于广州,在这里进行交易和运出外洋,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才被取消。对外贸易获得发展的同时,清代沿海地区的国内贸易也得到极大发展。清初尚对民间造船业有诸多规定,以后逐步放宽。嘉庆二十三年(1818),清廷规定:“嗣后商民置造船只,梁头丈尺,照前听民自便,免立禁限。”民间造船业最为发达的江浙等地,获得进一步发展空间。清代的国内沿海贸易分为南线和北线。南洋航线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北线则自江苏吴淞口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这也是京杭大运河之外南北物资流通的重要通道。南线商船以福建的乌船和广东的洋船为主。这一时期的闽广海船数量较多,广东商人也全力追逐海洋之利。清中叶,每年往返南洋航线的闽广海船不少于700只,如果一年两次或多次往返,运货总吨数超过百万吨。据学者估计,“清中叶以后每年沿海贸易的南北海船约计有4000只左右,总吨位50万~70万吨,年总载货量约170余万吨”。因海路通畅而大大加强的南北经济交流,促使沿海地区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不仅东北的大豆、杂粮等物质源源不断运往南方沿海各省,台湾的稻米、蔗糖也成为与大陆贸易的主要物资。乾隆年间,两岸每年的贸易额已达“率数百万元”。北线以上海为最重要的出发点。“海船畏浅不畏深,畏礁不畏风”,上海等地很早就发明了沙船,“以其船底平阔,沙面可行可泊,稍搁无碍”,大者载3000余石,小者1000余石,专为沿海沙滩较多的特点定制。沙船舱底有甲板,船旁有水槽,其下有承孔,“水从槽入,即从孔出,舱中从无潮湿”,是理想的近海运输船只。另外,此时沙船已有诸多改进:在结构方面,将沙船的风篷改得短而宽,以降低风压中心来抵抗海风;在用料方面,将杉木改为“以松接杉”,将篾篷改为布篷,以增强抗击能力;在动力方面,改帆橹并用为完全利用风力,以提高效率。同时,当时已经有商船使用先进的“水托”法来判断航海方位。嘉道时,沙船按经营区域分为崇明、宝山等11帮,每帮有船数百只,分属若干船主。沙船以由北而南为正载,贩运东北的豆麦等物。由南而北装载茶布之类,每不满载,谓之“放空”。为求航行稳妥,通常要在吴淞口取泥压舱。上海经济很早就与沿海贸易联系在一起。曾国荃在《〈松江府志〉序》中写道:“松江枕海带浦,南控闽粤,北达辽左,冠盖之所临,帆樯之所集,中外富商大贾之所交通,蔚然为东南一大都会。”因地理上的关系,上海居民操航业者甚多。上海高桥中学内有一块明永乐年间的石碑,记载当时居民人工堆筑方圆百丈、高三十多丈土山的情况,土山上设烽堠,日夜燃烧,作为当时船商进入黄浦河道的航标,人们称之曰“宝山”。在清代,宝山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成为今日“宝山”地名的由来。在海运带动下,上海的经济日益繁荣,“浦滨舳舻衔接,帆樯如栉”。当时,由南载往花布之类曰“南货”,由北载来豆饼之类曰“北货”。乾隆、嘉庆间的上海沙船,有“朱、王、沈、郁”四大家。朱居首位,“家资敌国”,人称“朱半天”。王氏兄弟拥有沙船上百只,并占有上海南市的王家码头。郁家拥有沙船70余只,雇工2000多人,人称“郁半天”。道光时,上海已有私营专业船厂出现,如顾明海在浦东开设船“厂”,从修旧船开始发家,逐步发展到制造驳船、帆船,一应俱全。上海巨商张元隆立意要造船百只,以百家姓为号,头号赵元发、二号钱两仪、三号孙三益、四号李四美、五号周五华之类,“则其意要洋船百只之说,不虚矣”。当时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可见张元隆资金之雄厚。据李伯重研究,江南地区每年造沙船所需的专业工匠多达5000人,需工150万个,沙船业非常发达。上海船商主要从事豆饼运输。豆饼由沙船运诸辽左山东,江南百姓倚为生活,磨之为油,压之为饼,屑之为菽乳,“用宏而利溥,率取给于上海”。从事豆饼运输的商人自豪地指出,上海以从关东、山东所运之豆饼为大宗生意,“分销各省,营业为全市冠,以故上海用银两曰九八豆规元”。因流通量大而能成为通用货币,可见地位之重要。漕粮海运之后,每年有数百万石漕粮由沪至津,“均以沙船承其乏”。同时,清廷为招徕沙船,又规定船主可以同河运漕粮一样,免税携带土宜。政策上的扶持使得上海获得了发展的绝好时机,沙船在此段时间空前的发展,船只数量大为增加。在对漕运“独专其利”的同时,还促进了南北商品交流,致使“一时生涯鼎盛”。富户由漕运起家者也以上海“为独多”。随着沙船贸易的进行,上海钱庄事业也得到了巨大发展,据萧国亮的研究可知,当时双方存在着相互间的渗透,既有大钱庄对沙船主进行放贷,又有沙船主从事于钱庄事业。咸丰六年(1856),因上海银价飞涨,沙船主王永盛甚至仿西班牙银元之式,自制银饼,正面标有“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王永盛足纹银饼”,背面标有“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壹两银匠万全造”字样。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上海的江海洋关是依据这个条约第一个被开放的关口,并在1843年底开始征收国际贸易税。1850年,上海的洋货进口值为390.8万元,到1860年增长为3667.9万元,增加了8倍多。1855年,在小刀会起义期间,起义者控制上海,所有的征税活动停止。英、美、法三国决定接管江海关,自行征税,清政府不得不同意这一接管。通过这种方式,江海洋关成为第一个被西方列强控制的税关。从1861年起,所有洋关的管理权都步江海洋关后尘,全部交给西方列强管理。太平天国时期,大江以南几无完土,惟恃上海征兵筹饷。因为位于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江海关在关税收入上很快超过了粤海关,并迅速成为全国和远东地区最大的国际贸易口岸。除上海外,晚清时期沿海地区的城市也都得到巨大发展。北至天津,南至广州,此外还有烟台、宁波、厦门等,无不成为国内贸易的中转和对外贸易的枢纽。以天津为例,天津原名直沽,本为“海滨荒地”。元代定都北京,因运漕以海运为主,而海运均起泊于天津,所以,直沽作为海运码头的地位在元代已经形成。每届春秋两运,它们都会在直沽设立主政机关,人员繁多,“舟车攸会,聚落始繁,有宫观,有接运厅,有临清万户府,皆在大直沽”。为方便储粮,元代又在直沽广设卸粮和屯粮场所。至元二十五年(1288),增立直沽海运米仓。清时期,天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亲自查看天津至通州河道;次年,在天津建北仓48座,每座5间,共240间,“为屯粮之所,有大史官驻守”;八年(1730),清廷又将原属武清之西沽、北仓和原属沧州的葛沽划归天津,升府设县,地位更加重要。晚清时期,天津成为通商口岸,经济得到迅猛发展,1865年的进口洋货总值为7724571两,5年后即增长到11935176两,增长幅度高达50%以上。 “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天津便脱颖而出,由一个近畿的府属县城发展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港口城市,在北方首屈一指。”天津正式成为全国乃至远东地区的重要核心城市。三
由于气候、地理、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差异,数千年来,中国一直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关中平原和华北地区在很长时间内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但唐代以后特别是北宋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经济中心逐步向南方移动。到了清代,经济重心开始了新一轮的移动,即由内地向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呈现出一种“V”字型的变化。作为一种经济重心转移的现象,在数据指标上也得到了呈现。清代行政区划变化频繁,但边疆地区的数据缺失严重,加之本身的经济比重不大,这里以十八直省的情况为例来说明经济重心转移的情况。在十八直省之中,沿海地区省份为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山东、直隶,共计7个;内地省份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四川、山西、甘肃、云南,贵州,共计11个。按今天的省区行政面积来算,沿海地区为114万平方千米,内地省份为281万平方千米,沿海省份的区域面积远远小于内地省份,只有后者的40.57%。也就是说,不管是从省份数量上还是从管辖面积上来看,沿海地区都远小于内地省份。根据曹树基关于清代人口的研究,可以获得沿海省份与内地省份1776年、1820年、1851年、1880年、1910年这五个基准年份的人口统计数据:表1 清代沿海人口比重(单位:万)
省区 | 1776年 | 1820年 | 1851年 | 1880年 | 1910年 |
沿海 | 14038.8 | 16958.9 | 19086.3 | 16929.1 | 19152.1 |
内地 | 16560.8 | 20579.4 | 23502 | 18162.1 | 21936.3 |
总计 | 30599.6 | 37538.3 | 42588.3 | 35091.2 | 41088.4 |
沿海占比 | 45.9% | 45.2% | 44.8% | 48.2% | 46.6% |
通过表1可以看出,清代沿海地区人口数量略少于内地省份,考虑到沿海省份的面积不到内地省份的一半,其人口密度显然远高于后者。清代主体上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作为最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的可耕地面积,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参见表2)。表2 清朝直省耕地数(单位:万亩)
省区 | 雍正二年 | 乾隆十八年 | 嘉庆十七年 | 道光三十年 |
直隶 | 7017.1 | 6586.2 | 7414.3 | 14587.6 |
山东 | 9925.9 | 9934.7 | 9863.5 | 15096.8 |
江苏 | 6933.2 | 7019 | 7208.9 | 9167.5 |
福建 | 1330.7 | 1362.1 | 1451.7 | 2825.7 |
浙江 | 4588.5 | 4618.3 | 4656 | 5795.1 |
广东 | 3175.7 | 3342.6 | 3203.5 | 5279.9 |
广西 | 815.8 | 895.3 | 900.3 | 3404.3 |
沿海耕地 | 33786.9 | 33758.2 | 34698.2 | 56156.9 |
安徽 | 3420 | 3502 | 4143.7 | 8794.8 |
江西 | 4855.3 | 4857.1 | 4727.4 | 5167.8 |
湖北 | 5540.4 | 5874.5 | 6051.9 | 5807.8 |
湖南 | 3125.6 | 3201 | 3158.2 | 6334 |
陕西 | 3065.5 | 2916.6 | 3067.8 | 8114.8 |
甘肃 | 2179.1 | 2853.5 | 2479.8 | 5015.2 |
四川 | 2150.3 | 4593 | 4654.7 | 8106.2 |
云南 | 721.8 | 754.3 | 931.5 | 3016.9 |
贵州 | 145.5 | 257.4 | 276.6 | 2359.5 |
山西 | 4924.3 | 3398.6 | 5526.7 | 7189 |
河南 | 6590.5 | 7302.8 | 7211.5 | 12675.5 |
内地耕地 | 36718.3 | 39510.8 | 42229.8 | 72581.5 |
沿海占比 | 47.92% | 46.07% | 45.10% | 43.62% |
从表2不难发现,沿海省份的可耕地面积略少于内地省份,在总面积远不及后者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就,只能说明沿海地区的土地得到了更大程度的精细开发,达到了“生齿日繁,地无遗利”的局面。与人口和耕地面积直接相关联的是田赋。清代田赋统计方面存在大量的数据缺失。这里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藏的汤象龙等人整理的抄档《清代各省钱粮征收表》中道光时期各省地丁钱粮奏销册为例,来说明在清代中期社会经济较为稳定的情况下,沿海省份与内地省份地丁正项钱粮征收方面的对比关系。
图1 沿海、内地地丁钱粮占全国份额示意图
通过图1可以看出,道光时期沿海地区所交纳的地丁钱粮数,占全部地丁钱粮征收数的比例保持在42%~49%范围,其中超过45%是常态,这个比例与它的人口数与可耕地面积的比例是比较一致的。从人头税的角度来看,沿海地区的地丁钱粮负担的比例与内地省份并不存在着大的差异。但如果考虑到双方的总辖区面积,则可以说沿海地区的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显然更高。与此同时,地丁钱粮的数据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在清代,清廷延续明朝的政策,除了在各直省征收地丁钱粮外,还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八个省份征收实物税的漕粮,以供京畿之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抄档《清代黄册·户部仓场类》第23~24册各省漕粮交付通州仓(不含白粮)的数据显示,道光时期,虽然沿海地区只有3个省份要交纳漕粮,数量上少于内地的5个省份,但沿海地区所承担的漕粮征缴任务却远高于内地省份,年均要比内地多征收近200万石。其中,最低差额为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129万石左右,最高差额为道光六年(1826)的235万石左右。这显然与两者之间的人口数量形成鲜明对照。除此之外,江浙两省每年还需要额外为京师提供白粮,以供祭祀等重要场合之用,正米耗米合计为每年18万石左右。如果考虑到漕粮负担,则沿海地区的粮食赋税是超过了内地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沿海省份在清代是粮食净流入地。四
清代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商品交易的活跃程度上。在这其中,厘金和关税这两种商税具有标志性意义。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为解决财政危机,发明了厘金,即对过往商品征税。作为商税的一种,厘金征收制度较为复杂,既有征收于日用百货的普通厘金,也有专门征收于盐、茶、洋药、土药(鸦片)的特种厘金。按征收地点来区分,则可分为出产地厘金、通过地厘金、销售地厘金。征收的方式则分为官征和商人包缴两种。按照罗玉东的研究可知,厘金在开征之初,征收的比例大致为1%上下,所征税率并不算高,但此后这一比例被逐步提高。在这其中,沿海地区省份的征收率税是:福建10%,广东7.5%,浙江5.5%~10%,江苏是5%,广西和山东均为2%,直隶1.25%;内地省份则是:江西10%,湖南6%,云南5%,四川和陕西均为4%,安徽和湖北均为2%,河南1.625%,山西1.5%,甘肃为1%至2%,贵州不详。总体上看,两者的征收税率差别不大。然而,根据周育民《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再估计》一文所提供的数据,从咸丰三年到宣统元年(1853—1909),除个别时段因太平军的占领等特殊原因外,沿海地区的厘金征收数量都明显高于内地。考虑到人口因素,应该说,沿海地区百姓的厘金负担是远重于内地省份的。再来看关税的征收情况。关税基本是按货物的价值按比重抽税。岸本美绪分析康熙年间江南苏州附近地区米价表,最低米价为每石七钱,此时的最高米税率为3.7%;雍正六年(1728)修改米豆税,每石纳银四分,最高税率为6.7%。又据邓亦兵的研究,大约在雍正七年以前进行税则改革,即从量船计征改为计石征收,其中夔关的粮食税率最高,“各关的粮食税率一般不会超过夔关6.7%的水平”。至于其他的商品,如棉花、白蜡、丝、烟、烧酒的税率,则各有变化。由此可见,关税大致按2%~5%作为征税税率。这里仍然按十八直省的方式做区分,纳入沿海税关的为:直隶(含京师)的山海关、张家口、潘桃口、古北口、崇文门、左翼、右翼、坐粮厅、天津关、天津海关;广西的梧厂、浔厂;山东临清的户关、工关,以及晚清时期成立的山东东海关;江苏的江海关、淮安关、浒墅关、扬州关、龙江西新关;浙江的浙海关、南新关、北新关;广东的粤海关、太平关;福建的闽海关。纳入内地税关的为:山西的杀虎口、武元城;四川的打箭炉、夔关、渝关;湖南辰关;安徽的芜湖户关、工关,凤阳关;江西的九江关、赣关;湖北的武昌关、荆州关及晚清时期的湖北新关。常关税的征收对象是国内的商品流通情况。图2是沿海地区省份与内地省份的常关税征收情况:
图2 清代沿海、内地常税征收示意图
从图2来看,沿海省份的常税收入显然远高于内地省份,而且常常超过了一倍的水平。这说明,沿海地区的商品交易活跃程度是远高于内地省份的。关税征收量的波动,正好可以反映出商品流通的活跃程度。从这一点来看,沿海地区的商品流通活跃程度是远高于内地的。晚清时期,对外贸易获得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自然也会影响到洋税的征收。与常关税一样,沿海地区省份的洋税征收量远高于内地省份,同样反映出晚清时期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活跃程度远高于内地省份。如果把常税与洋税合并,则可以从总体关税的情况看出商品流通的活跃程度情况。
图3 清代沿海、内地关税征收示意图
图3的趋势显示,沿海地区的关税征收量,不论是针对国内贸易征收的常关税,还是针对国际贸易的洋税,沿海地区的征收量都是远远高于内地,有时甚至超过了四倍的水平。考虑到人口两者之间的对比,无疑更凸显沿海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商品交流的繁荣程度。五
唐宋之际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最重要的标志是人口重心移动,南方人口的比重一度曾达到北方人口的两倍,其内在的驱动因素是由于北方战乱的影响。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大混战和唐代的安史之乱,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有的随黄巢起义军南下留居各地,有的因避军阀混战逃向南方。契丹兴起后,不断侵扰中原,也迫使大量汉人南迁,迁徙的地区以江浙、闽、粤、蜀、楚为主,尤以闽、粤所获劳动力最多。不过直至北宋,由于与辽、金、西夏的长期对峙和战争,人口进一步流向南方,才导致人口重心彻底转移至南方。隋唐之前,关中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宋代开始,南方经济超过北方。到了清代,经济重心发生东向的移动。如果说清前期的田赋征收尚可以看到双方的势均力敌,随着厘金和关税为代表的商税快速增长,沿海地区的区域优势更加明显。晚清时期也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时期,中国经济进一步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沿海地区由于地缘优势而获得快速发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清代经济重心由内地向沿海地区的东向转移,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转移。与第一次相比,这次转移有了新的重要变化,即不再是以人口的多少为标志,而是以经济的活力及商品流通程度为度量衡。清代的人口重心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但经济活跃程度却有了彻底改观。这显示出,清代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在逐步超越传统的靠人力投入的农业型社会形态,而向工商业社会方向迈进。在人口数量和可耕地面积小于内地省份的情况下,沿海地区走出了一条商业化的发展道路,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内地,尤其是在人均水平方面更是如此,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沿海的7个省份之中,如果做进一步的区分,以直隶、山东作为北部沿海地区,江苏、浙江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广西作为南部沿海地区,则三个区域人口数据的比例,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的三个基础年份(1776年、1820年、1851年),分别为33:39:28,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的两个基准年份(1880年和1910年)则为42:27:31。这显示,经过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而北部沿海地区的人口比重则极大提升。可耕地面积方面,北部沿海地区所占的比重在48%~59%之间,比例较高;东部沿海地区则在34%左右浮动,恰为三分之一的比重;南部沿海地区的比重最低,为16%~20%之间,比重明显较低。如果以地丁钱粮计算,则道光时期北部沿海地区所交的钱粮比重占33%~45%左右,东部沿海地区占30%~40%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占22%左右。从这个角度来说,清代东部沿海地区的“赋重”,主要是体现在漕粮的征收上,而不是来自地丁钱粮。从厘金和关税的角度来看,则会呈现另外一种面貌。由于数据的缺失,大致而言,如果仅考虑百货厘金,则北部沿海地区的厘金征收最多只占不到5%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东部沿海是厘金征收的主体,尤其是前期占据了70%的比例,后期比例下降,也在50%以上;南部沿海地区则由最初的比重20%左右,持续上升到40%。即使是将各种厘金汇总,这种趋势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常关税的角度来看,北部沿海地区的关税征收有较大幅度的变化,从雍正乾隆时期的占比不到20%,逐步扩大至占比50%;东部沿海地区的关税征收由雍正乾隆时期的接近60%,下降至清末的不到18%,跌幅惊人;南部沿海地区的关税征收则经历了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雍正乾隆时期占比不到20%,嘉道时期一度增至50%,清末又退回至30%左右。洋税方面,北部沿海地区从1861年开始的2%占比,逐步提升至清末的15%,有较大的增幅;东部沿海地区的情况比较稳定地保持在50%左右的占比;南部沿海的洋税征收虽然绝对数量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但其占比却由最初的50%逐步下滑至30%左右,下滑的占比由北部沿海地区的增长所承接,这显示以天津为代表北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迅速崛起。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才可以说,清代是沿海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不是仅限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局部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的经济进一步得到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沿海地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1992年,占比为56.55%,1995年增加到58.33%,1999年则上升到58.72%。中国经济重心在沿海地区的这一格局,已经完全清晰。应该说,这一格局的确立,其源头正是来自清代开始的变化。
[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
编者注:此文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商税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644—1911)”(16ZDA129)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南国学术》2022年第3期第477—487页,第3期页码接续第2期。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或查看《南国学术》以往文章,请到“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网站点击“学术期刊-南国学术”,可以下载文章的PDF版,网址是:https://ias.um.edu.mo/2022-contents/。
主办:澳门大学
◇ 王一川
万物互联:一种新的哲学范式(353~362)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教授
妇女/性别研究的学术架构(363~375)
◇ 畅引婷
·东西文明对话·
◇ 张隆溪
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 讲座教授
◇ 江 怡
内忧外患与文化竞争
——嘉道年间朝野对基督教的认识与反应(395~409)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 教授
“休闲”中的文化记忆
——以日本的“花见”为例(410~420)
◇ 王晓葵
理论旅行的两种模态(421~430)
——从德勒兹《差异与重复》来观察(431~444)◇ 尚 杰
郑州大学 哲学学院 特聘教授
中国社科院大学 哲学学院 特聘教授
◇ 卢小合
·中国历史文化论坛·
◇ 程妮娜
吉林大学 匡亚明特聘教授
吉林大学 文学院 中国史系 教授十六国北朝僧俗往来书笺及其文学史意义(466~476)
◇ 倪玉平
·澳门学研究·
东西方交流中的澳门通事与长崎通词(488~494)◇ 娄胜华
编辑、校对、排版、设计:田卫平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平眼观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