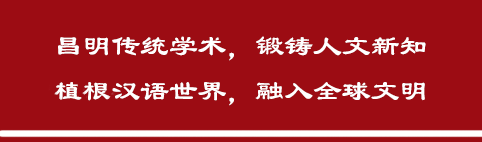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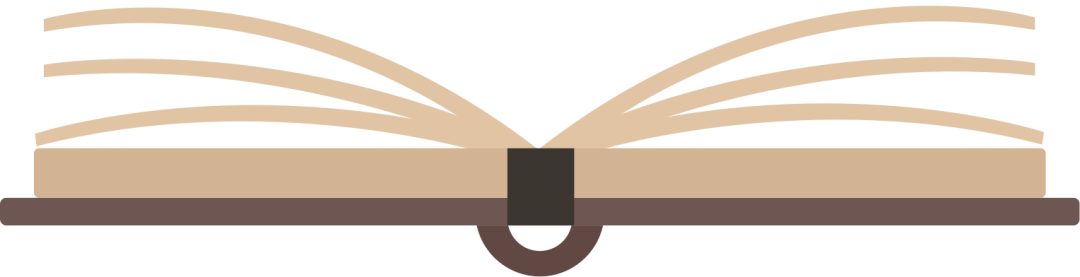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多面相的近世中国”,乍看来难免给人一种感觉:关于五代辽宋夏金元明清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被涵括,拼在一起就是近世中国。大约也是在这块场地,五年前《文史哲》曾组织过一次定位接近而时段不同的会议,名曰“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则明显有着相对集中的路径指向与前景追求。这样的差异当然并非编辑部有意造成,而或多或少能反映出两个时段历史研究的不同现状。
具体到我关注稍多的10至13世纪史,严守断代、政权边界的精耕细作与跨越时空畛域的贯通思考,在实践层面长期存在不小的张力,前者日趋纷繁乃至过密,后者则屡经号召而响应寥寥。纯以学理度之,多数治史者大概都不会否认后者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不过对于具体的实现路径及其可行性,或许有着见仁见智的理解与考量,从而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呈现。就个人闻见而言,前辈学者论及突破断代藩篱,常常会强调“整体视野”,诚属卓识,惟今看来,关于此种视野的内涵与外延,似乎还有进一步申说的余地。兹从跨越断代的格局、看待文献的眼光以及个案意义的定位三重维度稍事展开。
一、断代史背后的整体格局
说到这一时段历史研究的整体视野,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大宋史”的理念。1982年邓广铭先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提出:“我们的学会虽是以宋史研究会为名的,而实际上,不论北宋或南宋,都只是当时中国大陆上先后或同时并立的几个割据政权之一。既不应把宋朝作为正统王朝看待,更不能把它与那时的中国等同起来。宋史研究会的会员同志们所要致力的是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而决不能局限于北宋或南宋的统治区域。”类似倡议大概就是“大宋史”理念的由来。该理念曾引起过一些争议,不过正如学者近年所正确指出,所谓“大宋史”指的是宋史学者在讨论宋史问题时,应注意与当时前后并存的辽、西夏、金各王朝之间的联系与影响,而不是局限于赵宋王朝。也就是说,“大宋史”并非意在以“宋”作为那个时代中国的代称,而是呼吁研究宋史者不局限于“小”的宋政权,而应张大视野,胸怀全局。同理,治辽、夏、金史者如果能对整个时代加以全盘把握,自然亦可以“大辽史”“大西夏史”“大金史”名之。在这样的脉络下,各政权内部的历史被放置在整体时代格局之下,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视域得以打开。近来在中原、草原两大脉络交汇中观察契汉双轨修史体制、在中古郡望制度南北分途流变视野下讨论漆水郡望的特性等诸多尝试,重要基点即是对辽史研究由“小”而“大”的关切。
约与“大宋史”说同时,辽金史研究者曾提出过“第二个南北朝”说。此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取得太大反响,直至元史学者李治安发表《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一文,方才真正引起整个学界的重视。随着21世纪以来辽金史研究的持续深入,“第二个南北朝”不仅逐渐获得了较大范围的认可,更具备了从本位、名分之争转化为整体分析视角的可能,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就前贤所论稍加推衍,“两个南北朝”的观察视域大概可以用“两个七百年”来概括。第一个南北朝时期很多历史问题的实际入口在东汉,而其收束则往往晚至唐前期,因此不少优秀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会将公元1世纪前期至8世纪前期这七百年当作一个整体来思考,兼治南北,瞻前顾后,因而呈现出一派通达的气象。第二个南北朝的历史入口则可以上溯至安史之乱,此后南北的冲突、对立、碰撞、融合逐渐成为最大的问题,历经五代辽宋夏金之分立,并未以元朝的统一而自然终结,直到明朝前中期方才基本实现了政治制度、文化观念以及社会经济各层面的真正交汇。如此说来,第二个南北朝的研究者亦不妨考虑将8世纪中叶至15世纪中叶这七百年看作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单元加以通盘关照。
就具体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关于第二个南北朝的讨论仍处于筚路蓝缕的阶段,其间呈现出一些值得斟酌反思的问题。
其一,“南北朝”作为一种分析视角,除了强调汉与胡、农耕与游牧(渔猎)的异同外,还应看到它的本质在于理解分与合、多与一的关系。南与北的区分是相对的,多与一的转化则是绝对的;南、北内部皆可再作区分,南中可能有北,北中抑或有南,彼此杂糅的状态才是彼时的日常。以北方制度而论,辽制之渊源包含诸如草原旧俗(又可细为突厥、回鹘及契丹等多种)、晚唐之制、经后唐后晋改造过的中原之制以及汉唐经典所记理想制度等,这些因素在政治体发育、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不同时间节点被吸纳进来,加以混融。其中所涉显然并非简单的胡汉、农牧之别,而可能指向空间上的不同主体(契丹、沙陀、华夏等)以及时间上的不同层次(汉、唐、五代等),多元的制度来源在易代以后则往往被打包视作单一的辽制而为后来者所继承。如此由多到一的演进,又可能在金、元、明的制度流变中一再重演,后朝之一源在前朝皆不排除出自多源;理想状态下的史学研究正是将一元的既成事实还原为多种可能性的制度渊源,同时呈现其被整合、消化的制度过程。由此看来,南、北朝的分野不应成为遮蔽其他具体问题的笼统话语,而可将研究旨趣定位为从一元线性的历史叙述中观察到、释放出多元复杂的历史演变脉络。
其二,“南北朝”问题的研究路径未必局限于由后溯前。既往关于第二个南北朝的探索,多立足于元明时代既成的历史事实,逆流而上,寻找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渊源,连缀成必然的发展线索。这样的单向溯源,有可能因为后见之明而过度强调既成的“一”,而忽略原本的“多”,难免会给人以倒放电影的观感。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事实上更多是基于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的敏锐观察和深刻理解,验之以隋唐时代的衍化实迹,方才实现内在而邃密的贯通。同理,探讨元明时代的相应问题,离不开五代辽宋夏金史研究者的深度参与,依循历史演进的实际顺序,仔细剖析多元脉络、不同可能性的嬗变逻辑及其被统合、被遮蔽的过程,从而呈现更为斑驳丰富的图景。
其三,“南北朝”主要是汉文语境中突显的问题,有其适用的范围及限度。在汉语外交场合及日常称谓中使用的“南朝”“北朝”字样,默认的一个前提是南北双方处于同一套天下秩序与政治话语之中,是具有相对平等地位的两朝;从第一个南北朝到第二个南北朝,“北”的指涉范围由所谓的“渗透王朝”扩展至“征服王朝”,本身的确反映出前后期历史的演变,第二个南北朝的视角也的确有助于走出早先单一汉化论的叙述模式。不过,如果考虑到这套话语在契丹、女真、蒙古文中并不常见,恐怕仍不能以此覆盖当时历史的全景,从北方王朝自身的角度出发,会对世界秩序与族群格局更多样的理解与表述,这是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可以考虑增加的向度。
二、从碎片的史料到整体的文本
以上所述集中于断代史背后的整体格局,也是既往论及“整体视野”最为常见的方面。除此之外,所谓整体视野还可以包含另一重维度,那就是看待文献的眼光。近年来,我曾尝试从具体实践出发,反思史源学的研究路径,提出过其间的新旧之别,倘以一言蔽之,正在于碎片与整体的区分,从专注碎片的史料转向关照整体的文本。
中文语境下的史源学,一般认为创自陈垣的“史源学实习”课程。事实上,陈氏所用“史源”并非汉语成词,乃是由姚从吾自德文译介而来,其源头是伯伦汉所著《史学方法论》中“Quellen kunde”一词,意为相对原始之史料,而该词在通行的中译本中一般直接翻译为“史料”。换句话说,这个脉络下的“史源学”与“史料学”同出一源(直到今天,很多中国大陆以外的古代史研究者所理解的史源学仍然等同于史料学)。史料取向的史源学研究,最初是一条条地给清人挑错,后来发展为一条条地对史料加以碎片式溯源。此法的核心关切是对材料的真伪、正误、价值高下作出非此即彼的明确判断(如通常所说一手或二手材料等),落脚点仍然在于价值评判,在于如何利用。
如果说旧有史源学重在“源流有别”,那么我们现在所尝试的文本取向的史源学则重在“从流到源”,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整体”的理解和把握。
首先,根基在于整体的文献学感觉。所谓“文本”首先是以文献为本体,若将之看作有机的生命体,则其背景、来源、纂修、结构、抄刻、流传、被接受、被改造等各个环节都可以作为剖析的对象,每一个文献环节背后都牵涉到实际的历史情境,包括整体的文献环境、具体的人书互动关系乃至宏观的书籍社会史图景,连贯起来就是文献的生命历程。换言之,文献源流本身在学术意义上是独立的、自足的,并不依附于使用者的价值评判,亦未必需要舍流而从源。再者,所谓“文献熟是一种整体的感觉”,是希望研究者对文献的本质或者说文献本体有一个贯通的把握,理解其生成、衍化的机制和通例,特别是文献内在的复杂性、丰富性及约束性。如果对材料所在文献母体缺乏关照,孤立、零散地利用就会成为常态,这种漂萍式的碎片感可能会令研究者忽视文献源流本身所具有的规定性,增加文本解释的随意度和自由度。
其次,路径在于关注整体的文献源流。区别于既往从条到条的溯源研究,我们希望理清从书到书的过程,即从条与条的比较乃至比附转为还原书与书的实际关联。在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中,文献里绝大部分的有效内容并非“天外飞仙”式的信息碎片,可以不受现实条件制约直接飘落在作者笔下,而是通过具体的书籍流衍与编纂,从前一本书传递到下一本中。因此,来源文献的流传过程与最终文献的编纂过程,从纵、横两个维度构成了史源学分析的坐标系,也是研究结论可供验证、检核的切实依凭。而只有实现了“从书到书”,才有可能真正“透书见人”。书籍生成的每一个实际节点都在于人的参与,书—人—书的结构决定了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具体的人书互动关系,也就是什么人看到了什么资料,受到了何种影响,采取了怎样的编纂手段,最终在所成之书中留下了哪些痕迹。这些都是真切的历史场景,也留给后人考证钩沉的实在空间。
最后,落脚点在于化一为多,拆解既有叙述的整体框架,呈现前所未知的历史图景。既往个人所作尝试中,对于“一”的拆解以《辽史》的探源工作较为典型,即从文本缝隙切入,区分文本层次与单元,关注文本创作者究竟是如何将不同来源、不同性质、不同立场的资料编纂拼合在一起,加以逐层剥离,从而实现整体的框架性突破。而对于“多”的呈现,则以目前正在整理的《三朝北盟会编》更为突出。该书征引宏富,所收文献十佚其九,其中部分标举出处,另一部分则未注明,前者多为史家所零星引用,而后者在既往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倘对其来源加以逐一考索,以所得与各书已知文字合观,有望恢复许多佚籍的大致面貌,从而实现整体性“打捞”。文献层面化一为多的背后,其实是历史叙述由一元到多元的逆向过程,而所谓“透书见人”的实质正在于还原更多叙述主体所处的历史情境。
以上方法层面的探索得以开展,其实与10至13世纪文献遗存的特点密切相关。大体而言,这一时段留存的文献总量不多不少,通盘把握文献源流既是必要的更是可能的;基础核心史书仍居于统摄地位,对其加以批判性分析,具有足够的牵动性与影响力;留存文献的内在面相较为丰富,涉及不同时代、不同政权、不同层级,广泛存在着各种源头文献、同源文本及质证材料,客观上提供了呈现多元性的可能。可以说,这是史源学绝佳的实验场域,也是其最能发挥效力的历史空间。由此产生的彻底的源流意识和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读书法,构成了看待其他各种文献的整体眼光。
三、透过个案去关心整体
在长时段整体格局下呈现历史演进的多元图景,在整体文献源流中将历史叙述化一为多,二者存在内在的契合,这种契合促使我们思考10至13世纪在整体史中的典型意义。所谓整体史,并不限于中国史的范畴,而可能指向人类历史中的共通问题,即将10至13世纪的中国历史看作观察人类整体史的个案——这可以视作“整体视野”的第三重维度。
之所以会提及这一维度,从根本上讲,缘于对为何要关心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追问。在我看来,作为本位的研究对象与作为个案的研究对象,所折射出的或许会是完全不同的光谱,究竟要在怎样的视野下定位其价值,也应该取决于问题本身的延展范围。理想的人文学术,本质在于不断推展全人类认知的边界,而未必服务于什么;研究对象核心意义的检视标准,也可能并非研究者自身所设定或受制于的种种框架,而要看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关系到、照亮了整体历史。
近来一直勉力尝试从以上视角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例如关于契丹早期历史,我们观察到契丹自4世纪即见记载,阿保机家族则是晚至8世纪中叶方才加入的外来者,该家族的逐步崛起、跃升汗族直至10世纪初建立王朝,对于契丹集团而言不啻天翻地覆的变革,这在既往的历史叙述中完全湮没无闻。该个案的落脚点在于揭出统治家族史与族群集团史普遍存在的区别与断裂,由此可以进一步反思“民族”的本质以及权力与记忆的关系:从来没有哪个家族天生就是民族集团的统治者,但他们获得统治权力后总热衷于将自己家族的历史打扮成整个民族史的模样,通过重塑认同与记忆将现实的政治关系合理化,原本复杂多元的历史图景被简单化约为单一线性的家族史叙述。
又如关于契丹开国年代及阿保机即位方式,中原文献与辽朝文献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其实是历经文化转型后的辽朝史官系统性改写的结果;这种改写留下了种种难以弥缝的破绽,像阿保机奉遥辇末代可汗遗命即位,属于委国异姓的顾命,在汉文历史叙述中未见先例,显得不伦不类,其背后却隐含着草原政治中所谓同号易主的共通传统:同一国号下改换统治家族的情况在草原上并不罕见,这应该是与中原国号随家族改更并行不悖的另一种政治文化传统。相关历史叙述的张力集中呈现出草原传统被强行纳入华夏历史叙述所面临的困境,其实质是不同文化在交界面上的激荡冲突,可以视作文化转型的史学代价。
再如关于四时捺钵的研究,我们所熟知的经典叙述其实是元末史官将三种不同时代、不同主体、不同性质的文献拼凑而成的产物,根本不能反映有辽一代捺钵的实态。这一叙述之所以在数百年来一直被封为圭臬,是因为从最初的记录者到后来的修史者,再到后世的研究者,其实都是透过定居文明的滤镜观察契丹的:以春夏秋冬作为草原政治体的迁徙节律,很多时候只是定居人群基于他者认知而生成的一种镜像,与游牧活动之本相、北族原初之观念并不相涉。异文化的历史记录构成了今人观察古代草原社会的主要媒介,其中可能隐含的思维定式以及由此带来的扭曲、误解,亟待展开深入反思。
上述不同个案具体立意自然多有分别,但其处理方式与最终落脚却有所叠合,如对于“多”与“一”关系的关注与呈现,正与前两节所论时代格局与文献留存的实际状况密不可分,足见整体时代的典型性特征可能会在潜移默化间影响具体个案的研究旨趣。同时,这些个案中隐含着共同的思维路径,也是我目前对于如何透过个案去关心整体史的理解:在个案的实证层面呈现前所未知、遭到遮蔽的历史图景,在人类整体生存境遇的视野下思考其典型意义,在具有共通性、普遍性、牵动性的议题上提出差异化、多元化的可能解释——如此疏空之论,很大程度上只是学有不逮而心向往之的愿景,更多的实践与检验还要留待将来。

往期精选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文史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