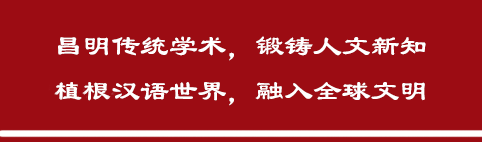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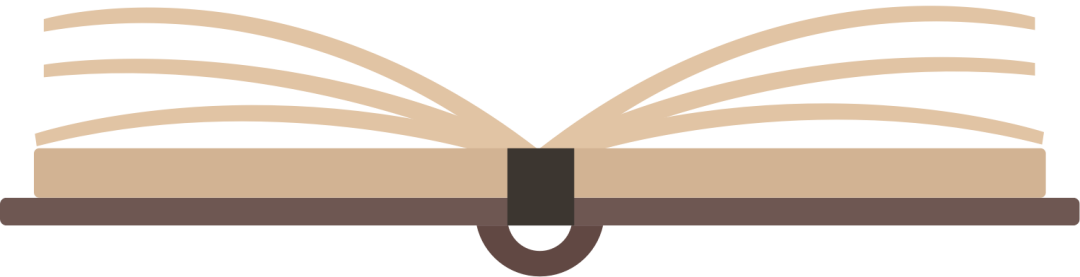
元史研究的世界性,在史学界是公认的。如果从何秋涛(1824-1862)与巴拉第(P.I.Kafarov Palladius, 1817-1878)的交往算起,超过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外学术交流不绝如缕。这在中国史研究中独领风骚,学术遗产丰厚。洪钧首开引介域外文献之功,屠寄有志于超越元史而编纂世界性的《蒙兀儿史记》。王国维的元史研究以文献学(西方称为语文学、历史语言学)贯通中西史学,使世界范围的学者得以顺畅对话。伯希和(Paul Pelliot)常称引的多桑、伯劳舍、屠寄、巴托尔德,代表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前半的成就,至今仍然不可绕过。在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之后,姚从吾、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等留学欧美归国,以融汇中西学术为导向。哈佛大学柯立夫(Frances W. Cleaves)留学中国,奠定根基,从而成为美国蒙古学奠基人和汉学大家。20世纪中后期,柯立夫培养出傅礼初(Joseph Fletcher)、萧启庆、刘元珠、洪金富等中西学者。改革开放以后,中外学术交流恢复畅通。四十余年来,元史研究从业者少,中外学界有一些壁垒,以及公共领域有某些偏见,导致学术国际化也许未达到前辈学者期待的水准。国外学术的营养在国内还未得到充分吸收,而一些领先于世界的中文著作也还没有对外传播。
世界性,造就了元史研究的基本特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史料、语言和理论是史学的三种功夫。以我个人体会,对于当今元史学者,史料和语言钻之弥坚,理论仰之弥高,三者缺一不可。本文从这三方面梳理和展望元史的方法、范式和理论。一孔之见,就教于方家。
首先是史料。元史学由乾嘉史学、晚清西北史地学发展而来,以文献校勘为史学根基。校注古书、释录金石,可以说是钱大昕、沈曾植、王国维、陈垣到蔡美彪的日课。陈垣发凡起例的校勘学,是校《元典章》的经验总结。陈垣的史源学,是将研读中国史料的经验,结合姚从吾带回的兰克史学而提出的。1976年点校本《元史》,体现出元史学界精湛的文献功底和历史语言“审音勘同”(韩儒林语)研究积累。1980年,在中国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翁独健号召系统性整理史料。但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相比,元史的基本史料迄今仍未整理完备。学者们集中力量优先解决繁难的蒙古语文和蒙汉双语混合的“硬译公牍文体”(亦邻真语),到21世纪才整理出版《元典章》《元朝秘史(校勘本)》《圣武亲征录》《经世大典》等书,而周清澍、杨讷等对文集资料的编目和刊布,以及出土文献、海外藏典籍的整理等工作,为下一层次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当代西方学界对中国史料的渴求,体现在美国柏清韵(Bettine Birge)英译《元典章·户部·户婚》,艾骛德(Christopher P. Atwood)英译《元史·太祖本纪》《圣武亲征录》及五种汉文史料,邓如萍(Ruth W. Dunnell)等英译《长春真人西游记》,以色列彭晓燕(Michal Biran)主持的多语种传记数据库等项目中。这些译注项目中皆有中国学者的身影。若无陈高华等对《元典章·户部》的校释研究,英译本是不可能出现的。日本学界从20世纪末兴起“石刻热”,积累了在中国各地访碑的宝贵资料。松田孝一、森田宪司、村冈伦等在京都召集元代石刻读书班,编辑期刊《13、14世紀東アジア史料通信》,尤其发掘石刻对于政治和宗教史的补证作用。中青年学者也注重开拓石刻对于社会史的价值。饭山知保的英文专著以“先茔碑”为主线,贯通金元明清长时段的历史。王锦萍将华南历史人类学方法引入金元之际的华北。李治安、王晓欣担任总主编的多卷本《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正在陆续出版。随着元史史料学基础日益坚实,史学与文献学紧密结合的史源学、史料批判和历史书写等研究,方兴未艾。而多语种文献为这些研究增加了挑战,也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其次是语言。元史文献语种多。陈寅恪阐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有“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之义。其现代学术意义,在于突破单一语种史料带来的单线叙事、单一视角。一切研究,必从二重证据起步,故而元史研究中史料与语言相得益彰。民族语文,以蔡美彪的八思巴字、亦邻真的蒙古语文研究为典范。而域外文献,按翁独健的建议,分两步译介,先借助现代西文译本转译,再从原文直译。波斯文与汉文并列为元代史料之大宗。波斯文《史集》汉译全本(1985),领先英文全译本(Thackston, 1999)十余年,而且余大钧增注的波斯原文转写提高了汉译本的学术价值。当今学者正直接翻译波斯文献,已出版时光译《伊利汗中国珍宝书》,待出版王一丹等译《五世系》(《五族谱》)、陈春晓译《迹象与生命》、邱轶皓译《完者都史》等。欧洲文献以中世纪拉丁语和俗语写成,以往学界只能借助现代欧洲译本。《马可·波罗行纪》在1936年有冯承钧、张星烺两种中译本,但后来杨志玖、蔡美彪、黄时鉴、陈得芝的杰出成就皆基于1938年慕阿德、伯希和的英译百衲本(Moule-Pelliot)。如今荣新江、党宝海主持中译了英译百衲本,历时十余年终于完稿。随着我们与意大利文献学者的合作,未来读者有望见到从原本直译的本子。元中期来华的《和德理行程记》(旧译《鄂多立克东游录》)已由求芝蓉从拉丁文直译,即将出版。
中外史料二重证据,为元史研究带来了广阔的视野。元史研究很自然地延伸到民族史、边疆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可谓“无中无西”,“无分畛域”。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领先于世界。西方学术界自20世纪末爱尔森(Thomas T. Allsen)以来推崇全球史、跨欧亚区域文明交流的视角,集中展现于新出的《蒙古世界》(2022)、《剑桥蒙古帝国史》(2023)等书中。其中也有中国学者的贡献。冲破单一国别、单一民族国家史的界限,跨越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分野,是元史研究的横向意义。
元史学界充分重视域外文献和历史语言(傅斯年所谓“虏学”)的方法。陈得芝《蒙元史研究导论》(2012)开创了多语种史料书目学。《剑桥蒙古帝国史·史料卷》集各国学者之力而成。对域外史料仅取便于使用的版本,是远远不够的。新获史料的价值,有可能被过度强调。如果多重证据相互之间出现矛盾,孰轻孰重,是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比如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著作中,常常有以波斯史料为准的倾向。域外史料,可能因获取和研读难度大而被赋予神秘的功效。只有对域内域外史料同等精通,才能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以马可·波罗研究为例,渡边宏1986年编纂的《马可·波罗书志》所收史料与研究已逾1500条。随着研究飞速发展,我在《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2018)中介绍的文献学成果又可迭代更新。2024年纪念马可·波罗逝世七百周年之际,意大利又发现了新抄本,而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正在做马可·波罗书目数据库。这些国际前沿资料,让我们的研究可以进入新的层次。总之,建立域外文献史料学,势在必行。
最后是理论。这包含宏观理论和中观范式,关乎历史阐释和历史叙事问题。钱大昕、伯希和、王国维皆以考证见长,伯希和甚至以宏大叙事为耻。这塑造了国内元史学者百余年来的实证学术传统——重史实,轻阐释,较少套用新理论。实际上,元史研究不能回避历史叙事的问题。在现代史学中,元史的叙事框架,基本定型于20世纪中期。代表性的著作是三种《元朝史》(分别为韩儒林主编,陈得芝主编,周良霄、顾菊英著)及《剑桥辽夏金元史》(尽管英文标题冠以“征服王朝”)。伊朗、中亚各国、俄罗斯的现代民族国家史叙事,也都习惯赋予蒙古统治野蛮、落后的负面评价。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转而阐释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对于沟通世界文明的积极意义。1990年代以后,杉山正明出版一系列著作,将游牧民族的能动性置于世界历史的中心,而且将他的研究心得灌注到历史课本中,影响很大。金浩东(Kim Hodong)、陈得芝为此各自撰文讨论元朝的国号和性质。2013年以降,杉山的多部著作译为中文出版,引发了知识界对于元史的历史定位、多角度叙事及现代价值的关注。姚大力、刘迎胜各自为《重新讲述蒙元史》(2016)撰写的论文,是用实证方法回应世界性叙事的范例。我们想要理解元朝在当时世界上的横向定位,需思考元朝在中国历史中的纵向定位。
王国维的元史研究因其自沉而未竟,其著作从问题意识而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史料学相关问题,另一类是蒙古名物制度研究。后来元史学界的政治制度研究成果尤为丰硕,深入探究了蒙汉二元制度。王国维时代学者所谓制度,含义比政治制度广,迄今未发之覆尚多。如元朝礼俗研究即由王国维开启,吸引了世界范围多学科的兴趣,但后来推进较为缓慢。一方面,蒙古语史料过于零散;另一方面,必须付出相当大的精力读懂汉式礼制,才能从汉文史料中剥离出蒙古礼俗。这种困难是制度史整体上要面对和克服的。而如果用汉文史料只做汉式制度,则不免有陷入琐屑之虞。
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是在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痛切关怀现实的思潮中产生的,揭示外来族群融入中华文化的史实,立意高远。后来者将“华化”范式具体为少数民族家族或人物的案例研究。萧启庆提出“多族士人圈”理论,描述元代中后期蒙古人、色目人既接受士人文化也未放弃原有的身份认同的现象,学术概念更加明晰准确,而研究时段缩小为元代中后期,对象限定为精英阶层。
陈寅恪的研究,紧扣民族与文化。陈寅恪的首篇元史论文《元代汉人译名考》(1929),是与日本箭内亘《元代社会之三阶级》(1916)的局部商榷。箭内亘将蒙古、色目、汉人民族混淆为阶级。在此基础上,1930年代出现的“四等人制”一词,并非来自学者的严谨论著,却很快成为传播最广的元史概念之一,被写入历史课本。进入21世纪,经船田善之的反思性论述,日本的教科书删除了“四等人制”“四阶级”之说。中国学者也展开深入探讨。刘晓指出元代并不存在民族不平等的法律,证明“四等人制”之“等”“制”皆无依据。张帆用“圈层”与“模块”取代“四等人制”的金字塔式图形。刘迎胜、胡小鹏各自揭示族群他称和自称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总之,“四等人制”已不再是阐释元史的万能钥匙。换个思路,研究元代族群的认同和构建,有充足的史料土壤,可描绘丰富的历史图景。
前述三种范式对今日的研究而言,适用性都有一定限度。制度范式主要适于中央政治尤其是统治集团。华化范式主要适于少数民族精英。“四等人制”不是一个清晰的学术概念,几乎已被扬弃。陈寅恪关切的“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细分为民族、家族、阶层、地域等方面,同样适用于元史,但元史相对于中古史产生的研究范式较为有限。
我们可以发现,民族在现代元史研究起步时吸引了太多的目光,而更重要的问题似乎被低估了。元朝作为大统一王朝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政治统一所带来的区域差异的整合,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课题,仅用民族视角是远远不能涵盖的。20世纪末,萧启庆归纳20世纪元史研究的整体进展,以“统合”(或整合)来概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等方面共同体的形成。21世纪初,中古史学界回溯陈寅恪、唐长孺的学术遗产,热烈讨论隋唐王朝的“南朝化”抑或“北朝化”。李治安先生从元史出发,吸收中古史的研究经验,提出南北朝与五代以后南北政权对峙局面的可比性,关照隋唐与元两次统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变动。李治安先生以长时段的尺度,回应“唐宋变革”和“宋元明过渡”(Song-Yuan-Ming transition)假说,最终将问题深入到生产关系的制度层面,提出“编民耕战”与“士农工商”两种发展模式的博弈是中国自战国至清代的历史主线,并且将南北区域整合、民族融汇两条线索置于发展模式这一主线之下。官制、士人与文化等皆为上层建筑,而发展模式讨论的是经济基础,这一理论可谓高屋建瓴。其十余年来的研究历程,对元史青年学者尤有启示性和指导性:为考察南北区域差异整合的长期过程,将元和明前期作为一个历史单元,融通断代史;以元史为入口,逐步实证,最终贯通性地阐释长时段中国史。由此可见元史研究的纵向意义。
总之,百年来元史学者提出了一些方法、范式和理论,需要当今学者继承发展。校勘学、史源学、二重证据、历史语言“审音勘同”,是由史料和多语种史料直接催生的微观方法。制度、“华化”,为中观范式。“四等人制”之说看似宏观,但学术性不足,应予摒弃。发展模式、南北区域整合、民族融汇是宏观理论,不仅适于元史,更有通史意义。与中古史相比,元史范式和理论较少、较晚出,留给当今学者很大发挥空间。新生代学者可以继续开发会通中外、融通断代的潜力。某一断代史中的问题,也许在另一断代史中有答案;中国史中某一模糊的面相,也许在世界另一区域史中有镜鉴。

往期精选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文史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