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近年来帝国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以钱乘旦主编的8卷本《英帝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为代表的重要成果,但由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于西方来说仍然非常薄弱,要想在这一领域拥有自己的学术话语权,还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帝国史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对其学术趋势及“新帝国史”做一初步考察,并由此提出一点思考。
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帝国史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8卷本的《剑桥英帝国史》。这套丛书从1929年开始出版,直到1959年出齐,这30年间英国正经历了从英帝国向英联邦的转变。这套书前3卷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旧帝国、新帝国、英联邦的历史,后5卷则叙述了英国主要殖民地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历史。从历史书写视角及方法来看,这套丛书主要秉承了史学中的政治史传统,围绕宗主国及其对殖民地的统治来构建叙述框架,主要探讨了英国如何从一个欧洲小国兴起、发展成为世界性帝国,英国的扩张及帝国的建立对于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及其殖民地的意义。这种叙事显然是围绕着英帝国意识形态展开的。
以《剑桥英帝国史》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的帝国史著作,关于英帝国形成的叙事基本持以下看法:英国扩张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而且在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盛行之时,还出现了针对殖民地的“小英格兰人”及其“分离主义”思想,把移民殖民地看作“母国”的“负担”。因此,19世纪中叶前英帝国是在“心不在焉”中形成的,与19世纪末强调“有形帝国”不同。
针对这种观点,约翰·加拉格尔和罗纳德·罗宾逊于1953年发表了《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一文,以“非正式帝国”的概念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对19世纪英帝国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其正式版图,因为在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形式下,英帝国的正式版图只是帝国看得见的部分。要理解19世纪的英帝国,应该考察这个触角伸张到世界各地的“非正式帝国”,其中包括英帝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涉及的非洲、中东、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不同国家。因此,他们主张19世纪英帝国扩张的连续性,不赞同“分离主义”的说法,并强调对殖民地的研究。
这一主张从加拉格尔和罗宾逊二人1961年合著的《非洲与维多利亚时代》一书中体现出来。该书聚焦于非洲不同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史,从殖民地而不是宗主国的视角来解释。加拉格尔和罗宾逊的帝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一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再把帝国只看作一个领土实体,而是看作与当地合作者的一种经济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它转而关注帝国中心的特性、土著社会的结构以及边缘地区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从而为帝国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们坚称正式与非正式帝国统治之间的连续性,这不仅为解释19世纪的英帝国主义,也为解释20世纪的非殖民化,甚至为解释美帝国,提供了思路”。
20世纪50至70年代是帝国史研究衰微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殖民帝国的瓦解,帝国和帝国主义在这股大潮中都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人们通常把研究帝国史看成认同或同情帝国主义。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帝国史陆续从欧美大学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甚至研究机构中被删除,代之而起的是区域研究或第三世界研究,也有一些帝国史家转向原宗主国本土历史的研究。这样,作为整体的帝国史基本上被分解成两个领域,即原宗主国的历史和原殖民地新兴国家的历史,帝国史为民族国家史的潮流所淹没。当然,帝国史在西方尤其是英国史学界并没有完全消失,1972年创办的《帝国和英联邦史杂志》(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为帝国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展示成果的阵地。
在去殖民化的浪潮中,帝国史很容易地被分解成宗主国的历史和殖民地国家的历史,这也恰恰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之前帝国史研究的特点,即帝国史就是宗主国的扩张及其殖民地的历史。这种历史实际上是以宗主国为中心展开的,重点在于从宗主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来分析欧洲国家扩张的原因和动机,探讨欧洲殖民帝国建立的过程及其对殖民地的统治。
从20世纪80年代起,帝国史在欧美史学界开始复兴,“帝国”一词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中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相关学术著作和大众读物也越来越多。到今天,就西方学术界的帝国史研究而言,从古代大陆性帝国到近代海外殖民帝国,相关著作多得难以统计。其中,迈克尔·多伊尔的《帝国》是帝国史研究出现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随后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成为一本重要的历史畅销书。这种帝国史叙事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在尼尔·弗格森《帝国:不列颠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一书出版时达到了一个新高潮。P.J.该隐和A.G.霍普金斯合著的《英帝国主义》于1993年出版后不断被修订再版。约翰·达尔文的《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也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的《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出版后即获得了2011年度美国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如果说大多数帝国史都是以西欧几大帝国为对象,那么,多米尼克·列文的《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成为理解俄罗斯帝国的一本重要著作。
帝国史在复兴过程中不仅涌现出大量论著,在帝国史书写方面也开始摆脱传统帝国史的研究视角和书写方式,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帝国史”的主张。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凯思琳·威尔逊(Kathleen Wilson)、史蒂芬·豪(Stephen Howe)、托尼·巴兰坦(Tony Ballantyne)、安托瓦内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克莱尔·安德森(Clare Anderson)、菲利帕·莱文(Philippa Levine)、琳达·科莉(Linda Colley)等人的帝国史研究就体现了一种“新帝国史”的理念。
最早呼吁以新方法来研究帝国史的学者是大卫·菲尔德豪斯(David K.Fieldhouse),他在1984年撰文提出,有必要复兴“一种新形式”的帝国史,把“旧帝国史的碎片重新组织成新的范式”,以帝国体系各部分(尤其是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互动领域”(the area of interaction)作为“新的和重建的帝国史的主题”。菲尔德豪斯在该文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新帝国史”这一概念,但明确使用了“旧帝国史”(old imperial history)并提出要用一种新范式来取代它。1996年,克莱尔·米奇利(Clare Midgley)在评述安托瓦内特·伯顿的《历史的重担:1865—1915年英国女权主义者、印度妇女和帝国文化》(Burdens of History:British Feminists,Indian Women,and Imperial Culture,1865-1915)和劳拉·塔比利(LauraTabili)的《“我们要求不列颠的正义”:英帝国晚期的工人和种族差异》(“We Ask for British Justice”:Workers and Racial Difference in Late Imperial Britain)时,称这两部著作探讨英帝国中的性别和种族问题,是“正在兴起的‘新帝国史’的一部分”,因此该评论文章也直接被冠名为“新帝国史”。
然而,“新帝国史”的主张在20世纪末并未得到帝国史学者的广泛赞同,一些学者仍然秉持约翰·西利以来的帝国史传统,1998年至1999年出版的5卷本《牛津英帝国史》就是这种研究的代表。这套著作仍然从帝国宏大叙事的角度,以英国的扩张及其与各殖民地的关系为中心,聚焦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因此在出版后受到了一些持“新帝国史”理念学者的批评。例如,安托瓦内特·伯顿就批评《牛津英帝国史》忽视了性别、种族等问题,“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想象力上也相当保守”。
2004年,凯思琳·威尔逊主编出版了《新帝国史:1660—1840年不列颠及其帝国中的文化、认同和现代性》,这可能是西方史学界第一部以“新帝国史”命名的著作。威尔逊认为,历史学由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认识论模式所塑造,把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经验普遍化并推广至世界其他地方,并以此来衡量其他地方的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在此影响下,“‘帝国史’观念可能只是欧洲支配和宗主国视角下的人为产物(artifact),它将西方帝国的现代性所锻造的模式和定位假定为事实……这样一座大厦上建立一种‘新帝国史’,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只能是‘添加’既有叙事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取代或甚至是重新配置它们”。因此,要突破帝国史的旧有框架,引入新的观念和思想尤为重要。
正是在后殖民理论和跨学科研究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帝国史研究中让“庶民”(包括原住民、妇女以及所有被历史档案所掩盖或隐匿的人)“说话”,使一种克服以往帝国史缺陷的“新帝国史”成为可能。“在不列颠研究中,这一激动人心的新工作大部分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影响:对英国历史中帝国重要性的一种非凡的重新发现以及在解决帝国情境中的身份认同和差异问题时,对社会史、文化史方法和文化批评的兴趣。”因此,在威尔逊看来,“新帝国史”就是把后殖民理论、社会史、文化史、文化批评等理论和方法引入帝国史进行跨学科研究,帝国中的身份认同和差异问题是其重要内容。威尔逊进一步提出,“新帝国史”也可被称为“批判性帝国研究”,是由历史研究和批判实践构成的一种跨学科形式,采用女权主义、文学、后殖民和非西方的视角,并用帝国统治下的地方知识来重新评估权力与维持现代性观念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关注社会底层,也是对长期忽视下层及非西方群体的帝国史研究的学科规则和范式进行干预,以此重新思考帝国意味着什么,并通过这一途径来重构关于帝国的叙事。
2010年,斯蒂芬·豪将他认为代表了“新帝国史”的30篇文章编辑在一起,出版了《新帝国史读本》。他认为,“新帝国史”意味着“以文化和话语的观念为中心的帝国史研究,极为关注性别关系和种族想象,强调殖民主义文化对宗主国及被殖民者的影响,并倾向于进一步探讨正式殖民统治结束后的持续影响”。因此,这种历史要对“知识、身份认同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包括关于历史学家自身定位的一种高度明确的自我意识)提出问题或假设”。正是从这种理解出发,他把这些论文分为12个主题:促进和解释“新帝国史”;思想的竞争与交流;来自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作为全球网络的帝国文化;女权主义、性别研究和身体史;生态史;种族想象;殖民主义文化对宗主国的影响;殖民主义的后续影响(afterlives);非洲与加勒比地区;其他帝国与其他历史;新历史、新帝国以及“殖民当下”。
由上可见,“新帝国史”是在诸多新史学思潮影响下,“对旧帝国史的一种修正,关注点在于文化、性别和种族,而不是高端政治、经济或军事扩张”。因此,“新帝国史”就是要克服那种以宗主国为中心,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来书写的帝国史,不再把殖民地及其人民置于被动的、次要的和附属的角色,而是要看到他们的能动性,并从文化、性别、种族、身份认同、流动网络等视角来理解和研究帝国。
第一,随着后现代思潮在西方的盛行,尤其是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以后殖民文化批评为特色的后殖民理论发展起来,这种思想着眼于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对历史学界的帝国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盖娅特里·查克拉巴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ty 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从福柯、葛兰西、德里达等那里吸取思想的养分,试图从话语角度解构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采取的策略是对殖民者的语言进行批判性审视,解构有代表性的文本,揭露他们表面叙述背后的话语设计。”例如,萨义德的《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通过对帝国主义时代西方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批判了后者对“东方”的建构和文化霸权。他指出:“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因此,西方许多文学作品都认为,“世界上有意义的行动和生活的源头在西方。西方的代表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他们的幻想和仁慈强加到心灵已经死亡了的第三世界的头上。在这种观点看来,世界的这些边远地区没有生活、历史或文化可言;若没有西方,它们也没有独立和完整可展现”。
在萨义德等人的后殖民理论影响下,出现了一些从殖民话语分析来批判西方帝国主义的著作,例如,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大卫·斯珀尔《帝国的修辞:新闻、旅行写作和帝国管理中的殖民话语》、珍妮·夏普《帝国的寓言:殖民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蒂姆·扬斯《在非洲的旅行者:1850—1900年的英国游记》等等。这些作品通过对殖民者的历史记录进行话语分析,批评了他们对非欧洲社会的歪曲、简化和建构。这些后殖民理论视角下的帝国史研究虽然存在着忽视具体历史差异、将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描述公式化和同质化的倾向,但对历史学界的帝国史研究仍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提供了新的审视维度。
第二是新社会史和庶民研究影响下的帝国史。20世纪60年代以后,从英国兴起的新社会史主张“眼光向下”,书写普通民众的历史。这一倡导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庶民研究的理念相一致。以印度学者为主开展的庶民研究,反对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视角来书写印度历史,认为以往的印度历史研究由这两种视角的精英主义主导,其历史书写带有一种偏见,即把印度民族的形成与民族主义的发展归结为精英的成就,假定民族主义完全是精英行动的产物,在任何一个叙事中都没有庶民进行独立政治行动的位置。因此,他们主张转向“非精英”和“庶民”研究。印度历史学家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是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主编的连续出版物《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后殖民理论学者斯皮瓦克加盟这一研究之后,后殖民史学方法成为这一学派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印度在近现代历史上主要是英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在英国学术传统中,印度史也就是英帝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庶民研究对印度历史研究中精英主义的批评,倡导印度史研究中的文化和语言转向,书写庶民的生活和境遇,无疑也成为推动英帝国史走向“新帝国史”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学术影响下的“新帝国史”,例如克莱尔·安德森的《清晰可辨的身体:南亚的种族、犯罪和殖民主义》,通过考察19世纪印度殖民地罪犯身上的刑罚文身(godna),认为这种纹在囚犯、罪犯和惯犯(habitual offenders)前额上的罪名使得他们的身体文本化了,其身体变得清晰可辨,为帝国管理者在殖民地社会中构建种族化和性别化的“社区”提供了途径。安德森的另一著作《庶民生活:1790—1920年印度洋世界中的殖民主义传记》,通过考察罪犯、俘虏、水手、奴隶、契约劳工和土著居民这些“庶民”的生活,描绘了一幅19世纪印度洋世界殖民地生活的图景。
第三,在女权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史学界出现了社会性别视角的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社会性别”(gender)像种族、阶级一样成为历史分析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此影响下,帝国史中的主角不再是男性殖民者,被淹没的女性被发掘出来,女权主义、性别问题和妇女生活也成为帝国史叙事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安托瓦内特·伯顿的《历史的重担:1865—1915年英国女权主义者、印度妇女和帝国文化》,考察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女权主义者如何构建并利用“印度妇女”的刻板印象来促进她们自身的解放。因此,她对英国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印度妇女和帝国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旨在“重新定位英帝国情境中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并且质疑西方女权主义者与本土帝国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她认为,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中产阶级女权主义与英帝国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英帝国文化霸权的表现。因为“印度妇女”被塑造成无助的受害者形象,依赖于她们的英国女权主义姐妹来帮助其改善境况,这种“印度妇女”形象在意识形态上服务于英国的中产阶级自由女权主义。菲利帕·莱文的《卖淫、种族和政治:英帝国中的性病监管》考察了1918年之前英帝国关于卖淫和性病的殖民政策,尤其是关于旨在阻止性病在各殖民地传播的殖民地立法,并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了殖民主义、性别、种族与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促进不同历史分支学科学者之间的对话。另外,莱文主编的《性别与帝国》是一部从性别视角来探讨帝国史的文集,其中的作者都是这一领域颇有成就的学者,包括安托瓦内特·伯顿、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凯思琳·威尔逊、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等。她们主张把性别放在帝国史研究的中心而非边缘,认为从性别视角来分析帝国,并不仅意味着承认妇女的行动和存在,也不仅是承认男性统治的帝国中存在着基于性别的差异,而是要进一步主张,“在理解帝国时,除了这些的因素外,如果不采用性别视角,就无法理解帝国的观念以及帝国大厦本身”。丽莎·奇尔顿的《帝国代理人:1860年代至1930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英国女性移民》,主要从跨国史视角探讨了英帝国中上层妇女在支持女性移民中所扮演的角色。她认为,从19世纪中叶到1930年间,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中产阶级妇女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并改变了帝国的移民。她们通常隶属于少数几个英国女性移民团体,形成了一个女性移民促进者(emigrators)的帝国网络,以此支持和推动女性移民。因此,这些具有帝国意识的中上层妇女帮助英国妇女移民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在致力于帝国的发展。正是出于挑战帝国在本质上是男性事业的观点,奇尔顿不仅把女性移民促进者描述为帝国代理人,而且将她们看作“帝国女性化”(empire feminization)的推动者。
第四,历史书写中的“文化转向”也大大推动了“新帝国史”的兴起。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麦肯齐是从文化视角来书写帝国史的积极倡导者,他主编的“帝国主义研究”丛书从20世纪80年代起,由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114册。其中包括麦肯齐的著作《宣传与帝国:1880—1960年的英国舆论操纵》及其主编的文集《帝国主义与大众文化》。前者主要以大众帝国主义为关注点,考察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英帝国的戏剧、电影、教育、青少年文学、帝国展览、青年运动和各种帝国宣传机构。后者则探讨了英国的音乐、绘画、小说、报纸、学校教育、电影、BBC广播、帝国营销局(Empire Marketing Board)、童子军运动等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些研究表明,具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和宣传,有助于培养英国民众的优越感、帝国认同和民族认同。因此,帝国史文化转向带来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就是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
英国的扩张及英帝国对英国人的身份和民族认同有何影响,成为“新帝国史”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琳达·科莉的《不列颠人:1707—1837年的民族塑造》从对外战争的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她认为,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成为不列颠王国时,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并没有统一民族的观念,但在其后不列颠王国发展的一百多年里,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列颠民族,这一过程与英国的扩张及一系列对外战争有关。18世纪下半叶,英帝国经历了北美独立、与法国和与西班牙的战争,1792至1815年又进行了一场艰苦持久的反法战争。正是这些对外战争使不列颠王国中的不同社会群体团结一致,使广大民众逐渐形成一种民族团结感。与科莉不同,凯瑟琳·霍尔的《教化臣民:英国人想象中的宗主国和殖民地(1830—1867)》则主要以牙买加为例,从宗主国和殖民地相互建构的角度考察了英国民族性的形成。霍尔的基本假设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相互建构,宗主国决定了殖民地的发展,而对殖民地的想象从观念上塑造了“英国性”(Englishness)。因此,她一方面“把殖民地和宗主国放在一个分析框架内”,另一方面探讨了使二者联系在一起、“走在双行道上”的复杂辩证关系,尽管二者处在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英国人正是在“学会如何定义和管理他们所遇到的新世界”的过程中,“通过成为殖民者而实现了自我”。霍尔和桑娅·O.罗斯主编的《与帝国同在:宗主国文化与帝国世界》也是主要讨论帝国对英国本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另外,安托瓦内特·伯顿的著作也强调帝国和殖民地对英国本土的影响,其《历史的重担:1865—1915年英国女权主义者、印度妇女和帝国文化》即凸显了想象“印度妇女”对于英国女权主义的意义。她的《在帝国的中心:维多利亚晚期在不列颠的印度人和殖民相遇》一书,通过讲述三个印度人前往英国的经历,探讨了19世纪晚期印度人和英国人相遇所引发的身份认同问题。她试图说明前往帝国中心的殖民地臣民,其身份认同颇为复杂,它是在一种动态的互动中建构起来的,而帝国意识形态对此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全球史的兴起也对帝国史书写产生了较大影响。全球史研究的基本理念是从整体、关联和互动的视角来思考大范围的历史,而帝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具有地区性甚至世界性的特点,因此,一些学者借用全球史理论和方法来开展帝国史研究。例如,有学者把殖民帝国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情境中,注重从帝国与外界的互动来理解其兴衰。C.A.贝利的《帝国子午线:1780—1830年的英帝国与世界》在分析英帝国的扩张时,就将亚洲与英国作为一个相关的整体来看待,认为英帝国的建立正是以莫卧儿、萨法维、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为前提。约翰·达尔文的《未终结的帝国:不列颠的全球扩张》也把英帝国扩张放在全球情境中,将其看作英国与外界相遇、接触、占领和统治的过程。再如,一些学者以网络作为理解帝国史的重要概念和工具,从网络视角来分析帝国各地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托尼·巴兰坦的《东方主义与种族:英帝国中的雅利安主义》就从帝国网络视角,探讨了雅利安主义的出现及其在英帝国各地的传播,因为“英帝国就像一张蜘蛛网,依赖于殖民地间的交流”。艾伦·莱斯特在《帝国网络:在19世纪南非和英国建立身份认同》中,通过考察19世纪英国对南非东开普殖民地的统治,从帝国网络和殖民主义话语构建的角度,探讨了英国殖民者的身份认同。凯瑞·沃德的《帝国的网络: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强制移民》和盖里·麦基、安德鲁·汤普森主编的《帝国与全球化:不列颠世界中人员、商品和资本的网络(1850—1914)》等,也都以网络分析作为帝国史研究的重要工具。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全球史影响下,从关联和互动的视角将个人生活经历置于帝国框架中来书写,出现了全球史宏观视野与微观史个体书写相结合的帝国史研究。琳达·科莉的《俘虏:1600—1850年的不列颠、帝国和世界》和《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世界历史中的一位妇女》、艾玛·罗斯柴尔德的《帝国的内在生活:18世纪史》等,就是这种“新帝国史”的代表作。
“新帝国史”是多种学术思潮影响的结果,体现了帝国史研究的多元实践。在这种多元实践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帝国史学者借鉴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结出了丰富多彩的帝国史研究硕果。这些研究无论从性别、种族、文化的视角,还是从后殖民理论和全球史的视野,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反对西方帝国史书写中以宗主国和政治史为中心的叙事传统,让殖民地人民和社会底层“说话”,更多地从文化维度来理解帝国,并将帝国看作一个互动网络,由此达到去宗主国中心性并解构相关宏大叙事的目的。“新帝国史”的实践无疑极大地丰富了帝国史研究,使帝国史这个历史学分支学科焕发出生机,并成为当今历史学中一个日益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新帝国史”由英帝国史研究发展而来,其理念和方法虽然也由英帝国史研究扩散运用于近现代法国、西班牙、荷兰、德国等殖民帝国,但不可盲目将其运用于欧洲殖民帝国之外的历史研究。同时,西方学者对帝国史研究的反思及其史学实践,虽然对西方帝国史研究中的传统及其欧洲中心论进行了批评,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和解构西方的帝国史学术话语霸权。这一任务还有待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学者来完成。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9期,注释从略。
责编|刘莉
网编|陈家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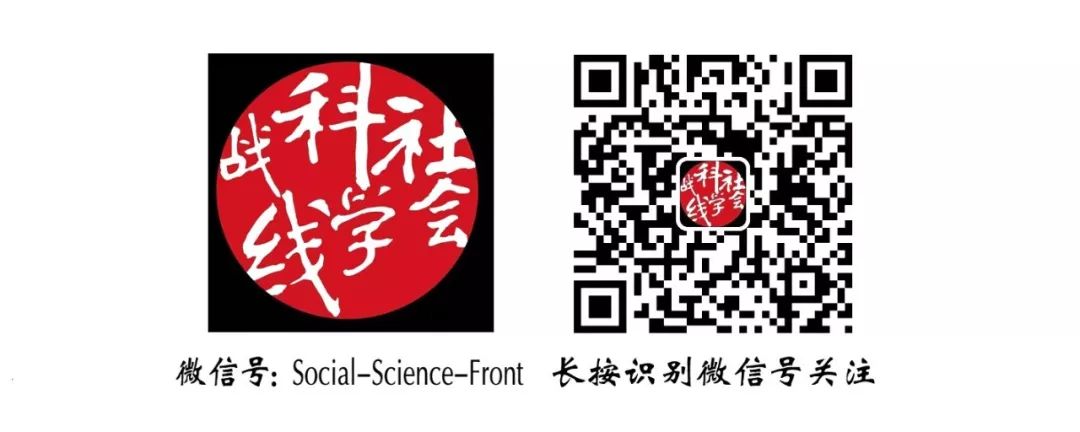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社会科学战线